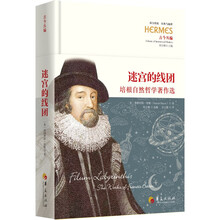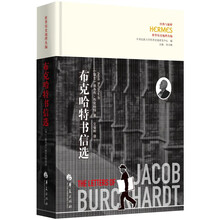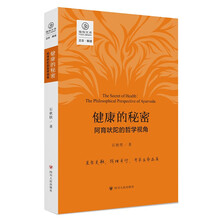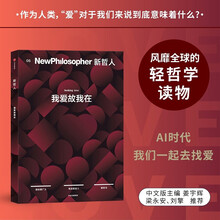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
他以一种费希特的方式认识到,外在世界是派生性的;它只是来自“我”自身的、来自“绝对之我”的下意识和无限意志的“非我”。为了认识并因此与这种被隐匿的意志结合,洛维尔必须颠覆把他设定为一种有限存在的传统惯例。这些限制看上去是由外在世界设立的,但在费希特看来外在世界只是“绝对之我”的意志的表现,而且我们通过我们的感觉在最为本原的层次上经验这种意志。这样,“经验之我”只需要通过它的感觉就能认识到它自身和世界,这些感觉表明它的局限性,而且因此显示“非我”和客观世界的形状。为了更深层次地理解作为“经验之我”和“非我”基础的“绝对之我”,有必要克服这些感觉和它们建立的限制。这意味着要克服“非我”和“经验之我”,与“绝对之我”结合,与作为所有事物基础的最为根本的创造性意志结合。洛维尔向残酷的肉欲主义不断重复而又深化的旅行,不是其他,最终就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悲剧式努力,努力成为绝对意志的一部分,努力获得无限性,努力获得绝对自由。他的生活就是尝试撕毁欧洲传统生活的庸俗面纱,揭示恶魔主观主义的全部真理性,揭示位于这种主观主义核心的肉欲和任性。他的例子证明,位于世界核心的本原意志,并非羔羊的意志,而是老虎的意志,或者至少只有老虎的意志才能穿透存在的真理,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种知识并没有带给洛维尔满足。自由不是幸福。他的努力使他反对所有的限制、所有的地平线,而在他跨越每一道地平线时,一道新的地平线又总是环绕着他。从费希特的视角看,他永远不可能幸福,因为他寻求的是自由和自治,但这样的自由永远不可能达到。于是,他总是不断受挫。无限性难以企及。当一张新的面纱被撕毁,他总又面临另一张面纱。他努力成为上帝,结果却成为怪兽,或者确切地说,成为怪兽般的上帝。
蒂克认识到洛维尔的行为黑暗而傲慢的一面,但是并没有诅咒这些行为。对蒂克来说,这种努力中有一种值得欣赏的本质性的东西。洛维尔的命运没有被打算当作一种针对傲慢的警告,而是作为一种感人的号召,呼唤人们去攻击天堂的城墙,即使它们最终没有被推翻。这样,即使洛维尔没有成为上帝,他也成了上帝的一个恶魔般的对手,并且因此成了某种超人般的东西。
对蒂克和其他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者来说,洛维尔的人生是高贵的和悲剧式的。它照亮了人的恶魔本质。他的“罪行”不是卑劣的行径,而是为换取高尚的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不道德成为自由和伟大的徽章。对耶可比和让·保罗来说,似乎是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把洛维尔诱骗进了虚无主义。耶可比指出这种黑暗的可能性:“我知道,迷信本身走得太远,以至于它会让它自己受到崇拜。除了虚无,它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它……只有它本身,它只看到它自己……作为命运的工具被决定;它不是意志,却发现自己是意志的代理人,这种意志想要把最可怕的东西带人光明,这些东西本来只是出现于黑暗的传说中。”
虽然蒂克也认识到一种绝对主观主义所包含的恐怖,但是他并不想谴责它,因为那些庸俗的替代品对他毫无吸引力。正如蒂克所描述的那样,后革命时代的人,要在过度文明的浅薄和恶魔般的深刻之间作出选择。
这种恶魔式的替代品的迷人之处不可低估。甚至是让·保罗,恶魔主义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也在他的小说《泰坦》(Titan)中描述了一个虚无主义英雄,罗凯洛尔。这部作品尽管是对浪漫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批判,但也能清楚地说明这种虚无主义对让·保罗所具有的魅力。这并不令人奇怪。就像他的导师耶可比一样,让·保罗相信存在一个人类无力理解或控制的上帝。他们的上帝非常接近唯名论的上帝,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上帝与藏在布莱克的老虎后面那种恶魔般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但是,费希特主义和浪漫主义尝试把这种力量置于“我”之中,这让他们非常厌恶。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