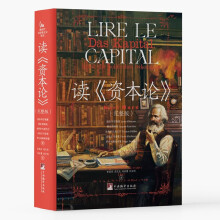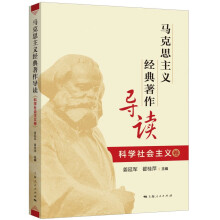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文化人类学研究》:
在作为群婚制的最高阶段的普那路亚家庭中,内婚制被终结,外婚制开始。所谓内婚制,就是氏族内部通婚,即夫妻之间具有血缘关系。对“内婚制”这一概念缺乏鲜明意识的学者,仅仅以为内婚现象是可能的,而没有认识到,在史前时代的某个阶段,内婚行为还是必要的,并因此成为一种制度。内婚制的存在性问题,在重要性上一点也不亚于群婚制的存在性问题。当然,内婚与外婚、群婚与个婚各是一对概念或制度,并可排列组合为四种具体婚制:内婚群婚制、外婚群婚制、内婚个婚制和外婚个婚制。从历史来说,从内婚制到外婚制的转变是在群婚制内实现的,然后群婚制在外婚制内转变为个婚制。但内婚个婚制(注意,这是一种制度,而非只是现象)并非不存在,而它正是文化人类学上能够带来重大发现的历史密钥。个婚的“先进性”与内婚的“落后性”所构成的错位性组合,集中代表了文化谱系中的家庭与亲属制度之间的错位规律的极端性,即它实际上乃是专偶制与血缘群婚制乃至性杂乱的错位。
内婚现象中的血缘关系有两种,即上下辈关系和平辈关系。血缘家庭的夫妻间禁忌了第一种血缘关系而保留了第二种血缘关系,而普那路亚家庭的夫妻间把第二种血缘关系也禁忌了,就走出了家庭本身的氏族限制。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变,其意义远不止优生学上的价值。这是因为,家庭本来只是氏族,而外婚制所带来的超氏族的家庭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其社会结构。社会转型问题第一次真正浮现出来。成功转型是很不容易的,而转型的成功就是从母权制及其公有制本质过渡到父权制及其私有制本质。
这里的关键词是三对概念:内婚制和外婚制、母权制和父权制、公有制和私有制。其中,内婚制必然是母权制,母权制也必然是公有制,且父权制必然是私有制;但外婚制可能是母权-公有制,也可能是父权-私有制。外婚-母权-公有制是从内婚-母权-公有制到外婚-父权-私有制的文化史中介。从内婚制到外婚制的母权-公有制的社会转型,是比较容易的;但从外婚制的这种形态向父权-私有制的社会转型非常难。这就好像书写载体的转换:从竹简、木简或布帛到纸张的转换是比较容易的,但从纸张到电子页面(即计算机界面)的转换很难。前一种转型或转换是质料的转换,其技术条件所要求的思维能力水平不高;后一种转型或转换是形式的转换,要求很高的逻辑素质。父权-私有制社会的运行基础就像计算机的运行基础,是复杂而严密的逻辑体系。法理与数理在逻辑形式上只有具体与抽象之别。事实上,数理化的逻辑科学及其技术(计算机程序)只可能诞生于讲究法理化程序的文化条件中。
一般说来,母权制和公有制是与内婚制相适应的,父权制和私有制是与外婚制相适应的。这样,既是母权制和公有制又是外婚制的社会,就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围绕这个矛盾的存在、认识以及解决办法所展开的,就是人类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其重要性,只有从自然动物到文化人的转变所在的那个文化人类学开端才堪相比。拿希伯来圣经故事来类比,如果说后者像上帝造人,那么前者就像人中有了亚伯拉罕,连摩西都在其次。
这里的具体问题分为两个:一是内婚制如何过渡到外婚制;二是在外婚制条件下,母权制如何过渡到父权制,而这就是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相对来说,第一个问题是简单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困难问题。但第二个问题之难,就在于第一个问题在精神本质上的遗留。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母权外婚制,是内婚制在外婚制中的精神性存在。而婚制中所谓的内外,作为血缘意义上的内外,在这种内外矛盾的斗争中,将隐示出在人格心理上关于自我认知的关键问题。在真正成熟了的灵魂中,血缘之内被颠倒为实际上是外部的东西,灵魂本身作为真正的内部之物由此才得以构建。这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社会心理学含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