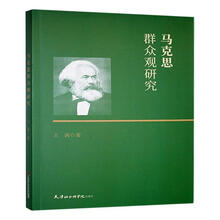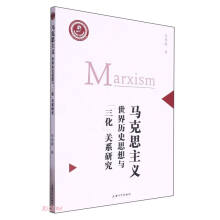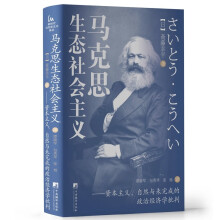《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由此可见,自然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获得了一种更为合理的和全面的意义,而人对自然的控制也具有了更加宽广的价值。也就是说,对自然的宰制,不仅具有作为劳动和生产力对象的经济层面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那里,一种伦理责任和正义担当也通过控制自然的行为被赋予在社会中活动的人。于是,当人类在寻求自身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和解放的时候,并且当这一任务被历史地实现的时刻到来的时候,自然也同时获得了作为劳动和技术的对象的最大限度的解放,它获得了与社会和人同等重要的意义,而不只是一种取之不竭的原料和资源的来源而已。正如莱易斯所言:“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理解,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
总而言之,从格伦德曼的观点看来,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概念的合理理解避免我们在实践中遭遇尴尬处境,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继承马克思的控制自然和支配自然的概念;另一方面,我们在生态实践上,约束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控制和支配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并不必然排斥在经济和伦理的维度上关注自然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格伦德曼坚持认为,只有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之上才能促进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格伦德曼的“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方案,就是要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以资本增殖和利润增殖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显然是以破坏自然为基本手段的,无法实现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是一种矛盾和冲突的关系,只要在资本的逻辑下,这种矛盾就无法化解。但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克服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实现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尽管从制度层面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但是苏联的社会发展仍然没有避免带来生态的灾难。格伦德曼认为,根源还在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对社会关系的改造,虽然从经济结构上消除了使资本增殖的驱动力,但是在冷战背景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社会模式的竞争性格局的对立性存在,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同样存在对生产增长的强烈冲动,而且对社会主义丰富的物质财富的追求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社会财富的盲目追求和崇拜,也给苏联的自然生态状况带来了片面的控制和剥夺。因此,按照生态的观点看来,社会制度并不必然决定社会经济是环境友好还是不友好的,问题在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采取的是何种控制自然的方式。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受控的“物质变换”循环采取何种方式、如何在消费和生产中控制人的非理性活动,将对“客体自然”的控制与对“主体自然”的控制结合起来,这才应当是人类“控制自然”的真实内容。
在反驳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反生态性指控方面,格伦德曼强调马克思的技术和劳动过程概念对于生态解放也具有启发性意义。马克思对现代性建制下的劳动的批判,指出了现代性劳动本质上的反生态性,因为现代性劳动的目的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人的欲望被无止境地激活,而为了满足无穷的欲望,现代性的生产劳动必须开足马力,不受限制地制造商品。资本的逻辑运动赋予人向自然无尽索取的价值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晚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劳动本质的反生态性功能获得进一步增强。显而易见,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本能,因此现代性架构中真实运动的资本逻辑的全部奥秘就是不断增殖的资本,以及为了生产的增长和利润的扩大而不知疲倦、永不休止地疯狂扩张,资本增殖的秘密就在于,“资本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获取利润,资本家投人大量的资本,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工人的物质生活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工人的劳动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实现自由。从本质上来说,现代工人劳动的异化本质并未消除,所不同的只是异化劳动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工人普遍贫困状态下的异化,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工人资产阶级化”的物质丰裕时期的相对贫困的劳动异化。工人的劳动除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还要为一种被消费社会所创造出来的虚假需要而劳动,如果说基本物质需要满足的是工人的生存需求的话,那么虚假需要满足的则是被激活的人类的无穷欲望。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