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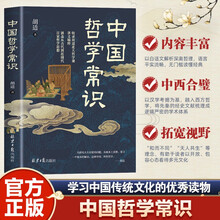


精彩句段
如今,随处可见一种痛苦恐惧症,一种普遍的对痛苦的恐惧。人们对痛苦的忍受度也在迅速下降。痛苦恐惧症导致一种长效麻醉。人们对所有痛苦状况避之不及,甚至连爱情的痛苦也渐渐变得可疑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症也蔓延至社会性事物。冲突和分歧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它们很可能导致令人痛苦的争论。痛苦恐惧症也席卷政治领域。一致之强制和共识之压力与日俱增。政治安守在一个妥协1区域,失去一切生机与活力。别无选择成为一剂政治止痛药。弥漫的中庸之气治标而不治本。人们不再争辩,不再奋力寻求更好的理据,而屈服于制度强制。一种后民主蔓延开来,这是一种妥协的民主。(P1-2)
妥协社会与功绩社会相伴而生。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苦难的被动性在“能”(Können)所支配的主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如今,痛苦被剥夺了所有表达的机会,它被判缄默。妥协社会不允许人们化痛苦为激情,诉痛苦于语言。(P3-4)
妥协社会也是一个点赞的社会。它沉溺于讨喜的妄想中。一切都被磨光、理平,直至称心如意。赞是表征,是针对当下的止痛药。它不仅掌控社交媒体,也席卷所有文化领域。任何事物都不该带来痛苦。不仅艺术,就连生活本身也要够得上在Instagram晒一晒的标准,去除可能引发痛苦的边缘和棱角、冲突与矛盾。人们忘记了,痛苦有清洁之能、净化之功。讨喜文化则缺少净化的可能。在讨喜文化的表面下积聚着肯定性之渣滓,人们在这些渣滓中窒息而死。(P4)
病毒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揭示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如今,人们将生存绝对化了,仿佛我们正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生命的所有力量都被用来延伸它的长度。妥协社会是一个生存社会。面对大流行病,为求生存的激烈斗争在病毒的刺激下逐步升级。病毒侵入妥协的舒适区,并将其变为隔离场所,生命(Leben)在这里完全僵化为生存(Überleben)。生命越像生存,人们就越畏死。“痛苦恐惧症”的尽头是“死亡恐惧症”。(P17)
为求生存的战斗必须用对美好生活的“操心”(Sorge)来对抗。被生存癔症控制的社会是一个僵尸社会。对于死来说我们太生机勃勃,而对于生来说我们又太死气沉沉。当我们的关注点仅为生存,那我们与病毒这种不死之物无异,同样只为繁衍;或说只为生存,不为生命。(P20)
我们可以把安徒生童话《豌豆公主》作为晚期现代人类超敏感性的一个隐喻。床垫下的豌豆给未来的公主造成如此多的痛苦,让她彻夜难眠。如今的人们可能就患有“豌豆公主综合征”。这种痛苦综合征的矛盾之处在于,痛因越来越少,而痛感越来越强。痛苦的程度无法客观确认,只能主观感受。“痛苦之无意义”伴随着日渐高涨的对医学的期待,让哪怕是很小的痛苦都显得难以忍受。我们不再拥有意义关联、叙事、更高的审查机构以及目的等有可能超越痛苦、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如果豌豆消失了,人们就会开始抱怨床垫太软,让人受罪。其实,真正让人痛苦的恰恰是漫长而无意义的生命本身。(P29)
如今我们不愿让自己遭受痛苦,然而痛苦却是为新生事物和全然他者接生的助产士。痛苦之否定性使同者中断。在妥协社会这座同质化的地狱中,痛苦之语言、痛苦之诗意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只能容纳“快乐的散文”,也就是“阳光下的写作”。(P45)
如今,像耐心与等待这样的精神状态也日渐消磨。强制追求全然的可用化使人们失去了真实性,而耐心与等待则能使这种真实性再度变得触手可及。在漫长与迟缓中的耐心等待,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意向性,一种向不可用之物靠拢的姿态。重要的不是等待什么(Warten-auf),而是在什么状态下等待(Warten-in),其特征在于一种恳切(In-Ständigkeit)1,它依偎在不可用之物身边。弃绝是无意向之等待的基本特征。弃绝本身也在给予,它使我们易于接受不可用之物,它与消费相对立。海德格尔曾说,“悲伤地承受着不得已的弃绝,做出牺牲”,亦是一种“接受”(Empfangen)。痛苦并非对缺少什么的主体性感受,而是一种接受,或说是“存在之接受”。痛苦即赠礼。(P62)
如今的我们完全失去了“灵魂赤裸”“揭蔽”,以及“对于他者的痛苦”。我们的灵魂仿佛长满老茧,使我们在面对他者时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数字化的气泡也越来越将他者屏蔽在外。围绕着他人的清晰的畏惧,完全让位于围绕着自己的散漫的畏惧。没有“对于他者的痛苦”,我们就无法触及“他者的痛苦”。(P67)
毫无痛苦、永久幸福的生命将不再是人类的生命。追踪并消除自身否定性的生命,自身也将不复存在。死亡与痛苦难分彼此,在痛苦中人们可以预见死亡。想克服一切痛苦的人,也必将抹除死亡。然而,没有死亡和痛苦的生命便不是人类的生命,而是僵尸的生命。人类为了生存而将自己消灭。他或许能获得永生,可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P75)
生 存
Überleben
病毒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揭示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如今,人们将生存绝对化了,仿佛我们正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生命的所有力量都被用来延伸它的长度。妥协社会是一个生存社会。面对大流行病,为求生存的激烈斗争在病毒的刺激下逐步升级。病毒侵入妥协的舒适区,并将其变为隔离场所,生命(Leben)在这里完全僵化为生存(Überleben)。生命越像生存,人们就越畏死。“痛苦恐惧症”的尽头是“死亡恐惧症”。大流行病使我们曾费尽心机要驱散、要抹除的死亡再次触目可及。大众媒体对死亡的过度曝光,使人们格外焦虑。
生存社会完全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健康被拔高为目的本身,为了这一目的,人们甚至牺牲了享受(Genuss,或“嗜好”)。比如严苛的禁烟令,便证实了一种生存癔症(Hysterie des Überlebens)的存在。在生存面前,享受也不得不让步。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生命上升为超越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为了生存,我们心甘情愿牺牲一切使生命变得有价值的东西。面对大流行病,人们也默默接受了对基本权利的极端限制。我们毫无抵抗地顺服于紧急状态,它将生命还原为“赤裸的生命”。在由病毒引起的紧急状态下,我们自愿将自己隔离起来。隔离区是营房的病毒化变体,在这里,赤裸的生命统治一切。[24]新自由主义的劳改营在大流行病期间被叫作家庭办公室(Homeoffice),它与专制政权的劳改营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健康意识形态和自我剥削那似是而非的一点自由。
大流行病之下,生存社会甚至在复活节期间也禁止礼拜。神职人员也要注意“保持社交距离”并佩戴口罩。他们完全将信仰牺牲给了生存。矛盾的是,睦邻之爱的表现方式竟然是保持距离,邻人被看作潜在的病毒携带者。病毒学剥夺了神学的权力,病毒学家获得了绝对的解释权,所有人都听他们的话。“复活”的叙事完全让位于健康与生存的意识形态。在病毒面前,信仰沦为闹剧,被重症监护室和呼吸机所取代。人们每天都在统计死亡人数,生命已完全被死亡掌控,它将生命抽空为生存。
生存癔症使生命变得极其短暂,它被缩减为一个待优化的生物学过程,失去了所有形而上的维度。自我跟踪(Self-Tracking)升级为一种狂热崇拜。数字化疑心病,运用健康及健身Apps长期进行自我测量,使生命降格为一种功能。它被剥夺了所有能创造意义的叙事,它不再是可讲述的,而是可测量、可计数的。生命变得赤裸,或说淫秽。没什么能承诺永远。同样黯淡无光的还包括所有的象征、叙事或者仪式,它们原本可以使生命比单纯的生存更为丰盈。祖先崇拜等文化习俗甚至能赋予死者生命力。生与死在一种象征性的交流中彼此联系。由于那些能安放生命的文化习俗已经从我们身边消失,生存癔症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如今,死对我们来说尤为困难,因为我们再也不可能有意义地结束生命,它的终结总是不合时宜。不能在对的时间死去的人,势必会在错的时间死去。我们未老而先衰。
资本主义缺乏对美好生活的叙事,它将生存绝对化了。这种无意识的信仰更多地是关于资本,而非死亡;它助长了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是为了对抗死亡,它被想象为生存的能力。[25]因为生命时间(Lebenszeit)有限,人们便积累着资本时间(Kapitalzeit)。大流行病虽然令资本主义措手不及,但却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从中没能发展出对抗资本主义的反叙事,因而也不会发生什么病毒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并没有减速,它只是被迫暂停而已。到处都是使人焦虑的停工停产状态。隔离所带来的不是浮生一日闲,而是迫不得已的无所事事,它并非栖息之地。并不是说在大流行病之下,健康就优先于经济了,整个增长经济、绩效经济本身就是为了生存。
为求生存的战斗必须用对美好生活的“操心”(Sorge)来对抗。被生存癔症控制的社会是一个僵尸社会。对于死来说我们太生机勃勃,而对于生来说我们又太死气沉沉。当我们的关注点仅为生存,那我们与病毒这种不死之物无异,同样只为繁衍;或说只为生存,不为生命。
妥协社会是一个肯定社会,无限的放任是它的标志,多样性、社区性和共享性是它的标语。人们把他者视为敌人,让其消失。在没有他者之免疫抵抗的地方,信息与资本的循环才如愿达到速度峰值。如此一来,“过渡”(Übergang)被踏平为“通道”(Durchgang),边界被消除,门槛被拆毁来自他者的免疫防御也就被极度削弱了。
如同冷战时期一样,以免疫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被栅栏和城墙包围。整个空间由多个彼此独立的街区构成。起免疫作用的障碍物使商品与资本的流通十分缓慢。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开始盛行。作为去免疫化过程,全球化将这些障碍物彻底拆除,以加速商品与资本流通。敌人的否定性虽然有免疫作用,却与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的法则格格不入。这里的战争主要是自己对自己发动,外来剥削让位于自我剥削。
目前,病毒引发了一场免疫危机,它侵入在免疫方面已大为削弱的放任型社会,并使其陷入一种休克强直状态。惊慌失措中,人们再度关闭边境。空间彼此隔绝,出行和接触极度受限,整个社会被调回到免疫防御模式。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敌人的回归。我们正在与看不见的敌人—病毒交战。
大流行病的行事作风与恐怖主义相似,都是将赤裸的死亡直接抛于赤裸的生命面前,并由此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在机场,每个人都被当作潜在的恐怖分子对待。我们毫不抵抗,默默忍受着颇有些侮辱性的安保措施。我们容许别人在身上探测,检查是否暗藏武器。病毒是无形的恐怖。每个人都被怀疑为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这将制造出一个隔离社会,并导致一种生命政治意义上的监视政权。大流行病让我们无从期待其他的生活方式。在这场与病毒的战争中,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仅为生存。生存癔症在病毒的作用下愈演愈烈。
痛苦恐惧症 1
幸福强制 9
生 存 17
痛苦之无意义 23
痛苦之狡计 31
痛苦之为真理 37
痛苦之诗学 41
痛苦之辩证法 47
痛苦之存在论 53
痛苦之伦理学 63
最后之人 69
注 释 77
附录 韩炳哲著作年谱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