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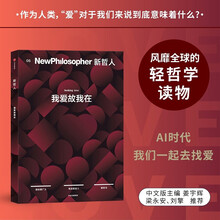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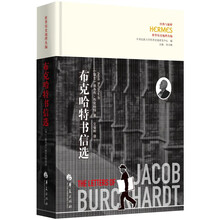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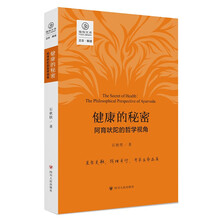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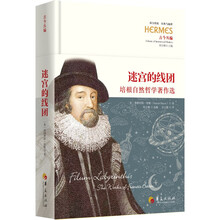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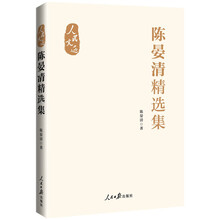
这是一个关于两次哲学之旅的故事:一次发生在约翰·卡格的青年时期,19岁的他只身前往阿尔卑斯山,在群山间寻找尼采写下名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灵感之源;另一次则发生在17年后,人到中年的卡格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在截然不同的心境之下携妻女重上阿尔卑斯山,再度与尼采的困境与救赎相遇。
何为“超人”?如何“成为你自己”?这是尼采哲学中两个极为关键的命题,而本书作者卡格认为,这两个问题在某个层面上可以合而为一。“超人”是对平凡自我的超越,但实际上也正在“自我”之中;“自我”并非一个被动存在于某处等待我们去发现的事物,而是一个在不断积极变化的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的形象。
攀登尼采,是攀登尼采走过的崎岖山峰,是攀登尼采哲学中的精奥之处,也是在攀登的姿态里叩响与尼采理想的共鸣,在人生无可避免的坠落处,找到那条回归自我的“超人”之路。
在阿尔卑斯山区,任何地方都可能暗藏危险。你可以通过选择你的行走路线和方式,来提高或降低危险的程度。我走了通向菲克斯谷的那条较高的山路,它在海拔约7000英尺处穿山脉而过。不过,在行走了两个小时后,我暂时停下了脚步,望向头上的山顶处,朝那个方向走的话,就能到达海拔11200英尺的特莱莫吉亚峰。我并不格外想要到那里去,但我的确想要登上某座山的山顶。因此我采用了一种青少年时代常常使用的策略,直接沿着垂直方向爬向那条路。这段路也没多远,就几千英尺而已。在年轻时我曾这样做过,而这一次我也确信自己还能做到。
攀爬是一种很暧昧的活动,它处于步行和严格意义上的攀登之间的地带。你需要像野兽那样四肢着地,手臂前拉,双腿上推,全身协同用力。在阿尔卑斯山脉中,你可以走那些既定的可靠路线,它们由瑞士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标示了出来(这是由一群年逾八旬的老人组成的登山组织,所有其他运动员的功绩与他们相比都会黯然失色),你也可以自己爬出一条新路来。说实话,我很少见到有其他徒步者选择后者—其实亲眼见过的一个都没有,但我确信大多数攀爬者都在清晨出发,并且都会像我一样,先以最快的速度爬上前一百英尺再说。在几分钟之内,他们就会攀爬到一个你听不见他们声音的高度,继而彻底消失在你的视野里。我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飞跑着离开步道:可能是因为害怕自己因跨过了某种未被标记出的界线而被抓住,或是被惩罚。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我可以这样做。无论如何,在这个早上,我尽可能地加快步伐。
在阿尔卑斯山间攀爬,需要遵守两条规则(也可能还有其他规则,只是我尚未知晓)。第一条就是需要“找到一条线”—也就是说,找到一条你能活着爬过去的路线。你可以使用一张标注详细的地形图,但我始终觉得那像是在作弊。攀爬者需要找到的这条路线上松动的岩石应该尽可能少,并且不能有任何超过10英尺高的垂直岩壁。要当心所有可能打滑的表面—湿滑或结了冰的岩石,并且谨慎地判断靴子每一步的落点—或者,在我的例子中是旧运动鞋。而关于攀爬的第二条规则,则是千万不要被这个词无害的表象欺骗了。听上去,“攀爬”可能远没有“登山运动”显得危险。事实上的确如此,前提是你在攀爬过程中腰间得一直系着安全绳。如果一个登山运动员滑落山崖,我们会期待安全绳能救此人一命。但攀爬者的身上却没有绳索。你得在没有任何助力的条件下一直抓住岩壁,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不让自己置身险地,不要遇到落入虚空的可能。
攀爬一开始是很轻松的:半山处长满苔藓的草甸为我提供了用以借力的抓手,而且山的坡度也不算陡峭。脚下打滑的话可能会擦伤膝盖,但也仅此而已。我一步步向上攀登,顺利地爬完了第一段坡,没遇上什么麻烦。当然,这只是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上方需要继续爬的路线。又爬上了两段坡后,我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始发点在哪里了。我试图找到它,但这只是徒劳。或许这并不是我的错,失去关于自己身后那段近期历史的视野,可能正是业余攀爬者的宿命。我知道我的出发点是在距此很远的山下某处,但究竟在哪里只有天知道。我对自己的目的地也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到了上方某个很高很高的地方,我就会停下。只有在过了几个小时之后,目的地才会显露出来。我发现了一条小路,通向菲克斯山谷上某条无名山脊的顶峰。在接近傍晚的某个时刻,我终于在某处岩石壁架上停下了脚步,它看上去和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悬崖很像。
这个地方已经够高了。我从几乎空无一物的背包里掏出《瞧,这个人》,并暗自发誓只读几页就转身下山,赶在夜幕降临之前。只读几页就好:“谁若善于呼吸我的著作的气息,他就懂得那是一种高空的气息,一种强烈的气息。人们必须是对此特别适合的,不然的话,在其中着凉伤风的危险是不小的。”《瞧,这个人》是尼采的自传。这是他处在精神崩溃边缘时所做的叙述。或许正是这个故事给了他许可,让他可以越过那条清醒与疯狂之间的界限。这的确是我读过的所有故事里,最为个人化,也最为真实地不真实的一个了。其中充斥着夸大其词和自吹自擂,突兀的转折和断裂,许多读者认为这是他此时心智已经失常的表现。“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的书”,这些都是《瞧,这个人》主要章节的标题。我同意,如果尼采本人意识不到自己的言辞之浮夸,那他就彻底疯了。但这些却都是有自知的、假装出来的吹嘘。
反讽允许人同时说两件事情,实际上,它让人可以在同一句话中传达两个互斥的现实。它让人可以同时言说爱与恨,感激和忘恩负义,拯救和罪孽,高歌猛进和一败涂地。“我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家”“我是完美的家长”“我有绝对的自知”,此类全然不可信的夸张语句,实际上就是在诚实地表明自己所述有多么远离实情。反讽是有两张面孔者的语言,它让你可以同时做颓废者与其反面。尼采承认:“这样一种双重的经验,这样一种向表面上分离的世界的接近,重复出现在我天性的每个方面:我有极其相似的两副面孔,除了第一副面孔,也有第二副面孔。或许还有第三副面孔呢。”
或许这些都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或者更具体地说,就像朱利安·杨所论证的那样,是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或者尼采是在引导读者的目光,让他们注意到很大一部分人现实背后的分裂本质,注意到一个人在其成年生活中经历到的那些分裂和断裂。去深切地感受“变老”所带来的、掺杂着智慧的哀伤,去理解一个人的青春并非早已逝去,而是藏匿在某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直面自我毁灭,而同时又渴望着创造—这就是与《瞧,这个人》搏斗的体验。为人父母也就意味着在现实中实践责任和个人自由之间的这种割裂—全心全意爱孩子,但同时也在人格中保留一部分不受养育子女这一活动影响的东西。尼采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分裂的自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尼采的标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瞧,这个人”是本丢·彼拉多在钉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将他指给众人看时说的话。1这时耶稣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头上戴着荆冠,作为人们对他的最后一项侮辱,还披着国王的紫袍。瞧,这个人,他如此软弱和痛苦。瞧,这个人,他竟然冒称弥赛亚。在卡拉瓦乔于1605年绘制的关于这个场景的画作中,彼拉多身穿16世纪贵族—学者的服饰,站在耶稣身前,直视着画面外的观众。就好像他刚刚拉开帘幕,正在将未来的弥赛亚呈现在我们面前一般。他的姿势和那只扬起来指向耶稣的手都清晰地说道:“看,我早告诉过你们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而耶稣就站在旁边,有些人甚至会认为他根本不是这幅画的重点—就只是一个身材中等、凌乱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荆冠的家伙,目光看向地面,像是在为自己身处的困境感到羞耻。他身后就是那个折磨他的人,一个奇异的两副面孔的人,正在给这个被定罪者披上袍子,既出于憎恨也出于怜悯。当然,耶稣才应该是那个最典型的分裂的存在—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但在《瞧,这个人》中,他完全是人性的,或许还太人性了一点。在《瞧,这个人》的结尾处,唯一还剩下的,就是空空的坟墓这个谜题。
开始下起了小雨。此时已近傍晚,虽然我不大情愿,但还是要尽快离开这里了。我向悬崖边缘望去,看到了一处高约200英尺的断崖,之后坡度渐趋平缓了些。《瞧,这个人》是关于“暴露”的,将自己拉出人群,显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身上那些通常被视为禁区的部分。攀岩者们提到“暴露”1,也有的时候总是带着那种独特的、混合着钦慕和恐惧的语气,而且他们也理当如此。将自己直接暴露在严酷的自然中,有一种致命的胜利意味。尼采引用了奥维德的一句话“Nitimur in vetitum”,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追求被禁忌者”。他在都灵的最后那段时间,刚刚完成《瞧,这个人》的写作时,著名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会的,我会发疯的。”
为什么尼采和荷尔德林都如此被恩培多克勒吸引?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爱—恨宇宙观。传说恩培多克勒本人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登山者。有一天,他登上了埃特纳火山,这是一座位于西西里岛东岸处的活火山,比那座更著名的、埋葬了庞贝城的维苏威火山还要大上一倍半。恩培多克勒爬到了埃特纳火山的山顶,纵身跃入了火山口中。
这并不是普通的自杀而已;根据传说,他的死其实是永恒生命的开端:当他被火焰吞噬时就被赋予了不朽。如果你这样解读这个故事的话,会觉得在正确的时刻死去其实颇有好处。尼采年轻时读到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之死》,并立刻迷上了它。在《瞧,这个人》中他又明确地回到了这个主题:“一个人要想不朽,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在他的一生中,他必须死好几次。”罗马诗人贺拉斯将恩培多克勒之死视作一个典型的创造行动,一个证明了规律的存在的例外—艺术家有这种为了独创性而毁灭自我的倾向,同时他们这样做也是被允许的。
我从被打湿了的书中抬起头来,向山下看去。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了“找到路”这项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攀爬者应该为自己规划出一条可以轻松下山的路线。在干燥的环境里,这算不上什么巨大的困难。但现在小雨下个不停,岩石都又湿又滑。很多被困在山上的游客实际上都不是正儿八经的登山者,而是些攀爬者,他们不慎爬得太高,然后就因为惧怕坠崖不敢往下走了。运气好的时候,会有直升机过来救他们脱离困境,回到安全的区域。上一次造访阿尔卑斯山脉的时候,我就目睹过这一场景:两名身穿红色雨披的徒步者爬到了科尔瓦奇峰上一万英尺高的地方,然后被困在了某条山脊上,无法向前一步。当直升机前去营救他们时,我都为他们感到窘迫。现在我打算在雨中试试运气,但这次我会很小心的。
我缓慢地向山下行进,黄昏也倏然而至。我突然想起了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之死》中的一个我之前忽视了的情节。这首诗的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埃特纳火山上。恩培多克勒已经到了山上,思考着自己的命运,就在这时,他的亲人和好友们找到了他。妻子恳求他从岩石壁架上下来,再尝试一次过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她的恳求让他更加确信了,下山的路只有唯一的一条。如果一个人需要被别人恳求着离开悬崖边缘的话,那么火焰或许的确有它的魅力。恩培多克勒跳进火山,不是为了获得不朽,而是为了证明他已经超脱了生命这场漫长的苦难。他被火焰彻底烧灼殆尽,几乎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来—或许只留下了一样东西。在远离埃特纳火山的某个地方,一只青铜制成的凉鞋从天而降。恩培多克勒的鞋子,是他这场或致命或神圣的试验留在世上的唯一遗物。
或许,《瞧,这个人》就是尼采版本的恩培多克勒之跃。他并不是失足滑落: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看起来很疯狂,可能也的确如此,但这疯狂也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
再或者,《瞧,这个人》只是尼采的凉鞋。
序言 母山
第一部分
旅程的开始
长久的伴侣
末等人
永恒轮回
第二部分
恋爱中的查拉图斯特拉
在山中
论谱系
颓废与厌恶
深渊大酒店
第三部分
马
瞧,这个人
荒原狼
成为你自己
尾声 清晨的火光
尼采生平与著作年表
参考文献和延伸阅读
译名对照表
致 谢
《攀登尼采》这本书不仅是对于尼采思想的简明导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证明,即在哲学为有益无害的所谓“智者的忧郁”提供解决方案之时,也正是哲学本身滋生发展的时刻。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非学术性质的思辨之作……书中最终探讨的问题是,如此恰切地描绘着某种潜藏的庞大欲望的尼采哲学,究竟能否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卡格在书中的回答既简略又深邃,展现了他对人生母题的深刻理解。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卡格是一位优秀的故事讲述者,在他的故事中,尼采的人生经历和他自己的人生产生着一次又一次微妙的联系……他试图用《攀登尼采》这本书发起挑战,引领读者去发现自己究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关于人生苦难的回忆录,而是关于哲学如何关照人生的严肃讨论,而这种讨论是通过作者个人的部分人生经历来呈现的。本书内容可读性强又趣味盎然,但并不显得松散随意,体现出了作者非常优秀的写作技巧。
——奈杰尔·沃伯顿(Nigel Warburton),英国开放大学哲学教授,著有《哲学小史》(A Little History of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