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世纪著名文史学家、“清华四剑客”之一李长之经典之作。李长之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注目于那些“文化托命之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李商隐、韩愈等,并卓有成果。其关于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人的研究,至今是研究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的必读书目。
2.资料翔实,考据有据,全面解读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李长之治学严谨,注重史料的选择与提炼,对司马迁的研究,几十余种参考书,真正做到了下笔有出处,言必有据,这些都凝结着他的史的眼光和不苟的精神。
3.版本权威。李长之直系亲属,女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于天池、女儿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亲自作序推荐。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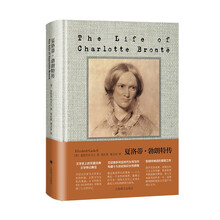


李长之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现当代的学者中卓然独立,似乎很少有学者能够与其比肩。 虽然他只活了69岁,从事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实际岁月不足40年,可留下来的论文,单就中国文学的研究已有600余篇,10余种学术专著。其作品数量惊人,跨度极大,从上古文学到现当代文学都有所涉猎,涵盖了多个领域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家。其研究所及,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这也正是他的毕生渴望——用尽心血撰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他的论著质量也非常高。长之先生去世后,其著作没有被人忘记,被汇成文集,许多专著被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有的一版再版,像他的《孔子的故事》现已有二十多个版本;有些著作还被译成英、俄、日等国文字在海外流行,有着极高的学术声誉。 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精彩纷呈、风姿各异,却也有着统一的风格,带有长之先生特有的烙印,这些烙印散见于论文,更鲜明地集中体现在他研究作家的传记中。也因此,长之先生虽然集诗人、学者、批评家、翻译家于一身,却往往被一些学者称为传记文学作家或传记式文学批评家。 长之先生的传记式文学批评简单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是视野开阔,能够把传主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后世影响,不仅置于当代的背景,而且置于中国的文学长河中审视,尤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并给以透彻明了的说明。 长之先生会多种语言,学贯中西,他常言有三个向往的时代,“这三个向往的时代:一是古代的希腊,二是中国的周秦,三是德国的古典时代”。在叙述传主生平的时候,他往往以这三个时代为参照。谈孔子,他开宗明义说:“二千五百年前,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国家都呈现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就是这种灿烂文化的代表。在希腊有自发唯物论的奠基者泰勒斯(约在公元前六二四至前五四七年)和辩证法的奠基者赫拉克利特(约在公元前五四〇至前四八〇年),在印度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约生于公元前五五〇年),在中国有孔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年)。”谈司马迁的历史观,他说:“一个历史家的可贵,首在有一种‘历史意识’。有历史意识,然后才能产生一种历史范畴。历史范畴是什么呢?历史范畴就是演化。凡是认为一切不变的,都不足以言史。自来的思想家,不外这两个观点:一是从概念出发,如柏拉图,如康德;一是从演化出发,如亚里斯多德,如黑格尔。司马迁恰恰是属于后者的。用他的名词说,就是变,就是渐,就是终始。”叙及李白的才气,他比照说:“倘若说在屈原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理想(Ideal)而奋斗的,在陶潜的诗里是表现着为自由而奋斗的,在杜甫的诗里是表现着为人性而奋斗的,在李商隐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爱、为美而奋斗的,那么,在李白的诗里,却也有同样表现着的奋斗的对象了,这就是生命和生活。”对于李白的豪气和才气,他说:“李白诗的特色,还是在他的豪气,‘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对于他的诗的写照了!在一种不能包容的势派之下,他的诗一无形式!或者更恰当地说,正如康德(Kant)那意见,天才不是规律的奴隶,而是规律的主人,李白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文学传记中对于人物的评价描述,颇近似于物理学中的定位。物理学中对于物体的定位,原则是参照的坐标越多,审视的高度越高渺,定位就越准确。现代物理的定位系统已发展为多个卫星高空定位。文学传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描述也是这样,囿于一隅一时,坐井观天,是绝对写不出好的传记来的。正如庄子所说:“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阅读长之先生的传记文学,你能够感受到他丰厚的学术根基、雄阔的学术视野,他对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化了如指掌,随手拈来,参照比较,得心应手。唯其站得高远,比照观察的对象丰富,故其叙述能高屋建瓴,挥洒自如,对于传主的生平、学术、影响的判断也就格外精准,这是一些盲人摸象、目光如豆的传记作家所难以比拟的。 其二,是他的文学传记富于浓郁的感情色彩,耐读,有兴味,具有抒情性。长之先生主张:“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他不但把自己的个人的偏见、偏好除去,就是他当时的一般人的偏见、偏好,他也要涤除净尽。他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因为不是如此,我们会即使有了钥匙也无所用之。”但他又说:“具体的,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喜欢浓烈的情绪和极端的思想的”,“以感情作为批评态度”,“以写出感情的型作为*高文艺标准”。他说:“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的。我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 如果说,长之先生主张的前者是对于一般传记作家的要求的话,那么,他所主张的后者则是张扬着自己的要求,体现了他的个人色彩。 写传记时跳入传主的世界不易,与传主同悲欢,进一步诉之于有浓烈情感的文字更不易。为什么呢?因为传主是有感情的人,文学艺术家传主的感情较之一般人更是敏感丰富,否则他们怎么能写出感人的作品呢?但感知一个伟大灵魂的情感,即使不是另一个伟大的灵魂,起码要相去不远。所以古人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庆幸的是,有着丰厚学术根基的长之先生恰恰同时也是诗人,也是散文家,是一个在感情上敏感而丰富的人。他多思善感,读《红楼梦》可以热泪盈眶;重校自己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关于李陵案的一章,竟然“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他自己就是美学中“移情”的典范。所以,就“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就宛如自己也有那些思想和情绪”而言,他与一般的传记文学作者并没有区别;但以长之先生的性格,以他的感情的批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言,他的传记文学所表现的感情色彩就较之一般的传记文学要强烈张扬得多。由于他具有语言天赋,他的笔锋又足以传递出那感情的浓烈,阅读他的传记文学就很容易感同身受,被其强烈的抒情性所吸引、感染。 其三,他的传记文学能够把学术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结合,雅俗共赏,老少咸宜。长之先生的许多传记文学起初是作为通俗读物出版的。《孔子的故事》自不待言,《韩愈》在民国时期被列入“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曾在《国文月刊》上连载,《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三联书店以“中国历史小丛书”形式出版。但它们又有很高的学术性,不失为严谨的学术性著作。七万余字的《孔子的故事》,脚注多达二百三十九条,几乎每页都有相关的脚注,引书达几十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作为大学本科研究《史记》的必读书目,其中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辩》在一九五五年还被一个叫刘际铨的人剽窃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为此,长之先生致信郭沫若,《历史研究》杂志发表声明致歉,而“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遂成为司马迁生年研究中的重要一说。他的《陶渊明传论》发表后,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界掀起了讨论陶渊明的热潮。 关于通俗读物的写作,长之先生有热情,也有明确的追求,那就是宋人所说的,“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他一生的论著其实也都本着这一原则。但他很谦虚地表示:“至于做到做不到,自己却不敢说了。” 眼下读者所见到的长之先生关于文学家的传记式批评,共有六种,它们是《孔子的故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韩愈》《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以及《鲁迅批判》。但长之先生所写成和计划想写的其实远不止这些。已经成文发表的古典文学长篇论文还有《屈原作品之真伪及其时代的一个蠡测》《孟轲之生平及时代》《西晋诗人潘岳的生平及其创作》《李清照论》《〈琵琶记〉的悲剧性和语言艺术》《关汉卿的剧作技巧》《洪昇及其〈长生殿〉》《章学诚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刘熙载的生平及其思想》《红楼梦批判》等;至于专著,尚有《杜甫论》《李商隐论纲》等未完成。后二者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之先生撰写《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时就立志要写的。可惜天不遂人愿,虽然长之先生已然有了充分的构思,完稿指日可待,可由于某些原因,戛然而止。关于杜甫的传记,只留下提纲;关于李商隐的传记,只来得及写了论纲——均成了《广陵散》,给后人留下无比的遗憾和悬想!
于天池、李书 2021年于疫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