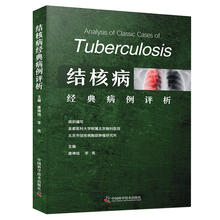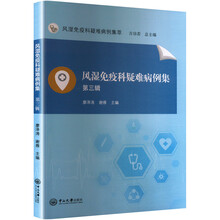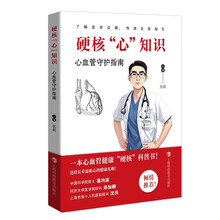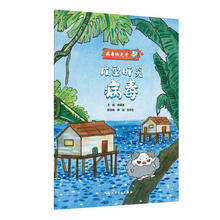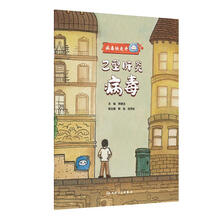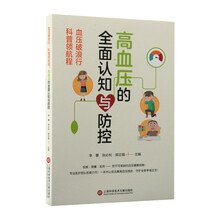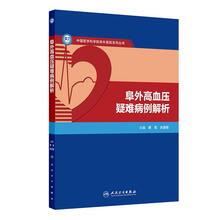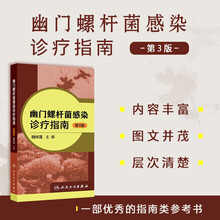第1章 整合肠道病学概论
人体的肠道包括小肠和大肠,小肠5~6m,大肠1.5m。肠道完全伸展后总面积为300~.400m2,甚至比肺泡的总面积还大。肠道内有数百万个神经元,并且是自主神经系统,具有人体“第二大脑”之称。肠道内有数万亿个微生物,其数量与全身的细胞数量相当,在人体肠道细菌中,只有10%~20%的细菌是与他人相同的,其他微生物群因人而异,多取决于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肠道的功能不只是消化和吸收所摄食物,还会对人体身心健康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肠道中的微生物种群影响着人的健康和食欲、体重和心情;肠道还是人体*大的免疫排毒器官,影响免疫力、皮肤健康和精神状态。因此,肠道又被称为“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整合肠道病学》的编写,是立足于樊代明院士所提出整合医学(holistic integrative medicine,HIM)的理念,聚焦于肠道生理、病理和良恶性疾病的解析与诠释,注重与传统肠病学专著传递的思维方式相区分,从整合医学的视角聚焦肠病学,力图填补相关领域内空白,给予读者新概念、新思考、新启示。本章概论内容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抛砖引玉,以引发读者从整合思维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下肠病研究的思考。
一、进化学比对为研究人类肠道提供独*视角
食物为生命体提供了组织构建的原材料,同时也提供了活动的原动力。消化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获得食物并从中摄取营养物质。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为适应大自然的复杂环境,不同种类动物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消化道的结构产生了不同的进化。在人体消化道中,胃对吞咽下的食物进行储存和初步加工,小肠靠各种消化酶直接吸收营养,而大肠则靠微生物来发酵小肠未吸收的部分,从而间接获得营养。相比于动物性食物,多数植物性食物中的糖、蛋白质和脂肪比较少,再加上其中常有各种消化酶抑制剂,众多成分不能被小肠吸收。大量难以消化的成分,会进入结肠发酵,产生丁酸,而丁酸滋养肠道上皮细胞,诱导其生长、分化,维持肠道微环境。因此饮食构成中的植物性食物越多,就越需要结肠;而饮食构成中的动物性食物越多,就越需要小肠。人类的结肠体积只占20%左右,小肠体积却高达60%,说明在进化史上,人类饮食中有很多可直接被消化吸收的营养,少部分食物经历结肠的发酵。人类的整个消化道占体重的比例,也是灵长类里*小的,这也说明在进化史上,人类吃的食物通常都很好消化。有人类学家认为,消化道非常耗能,靠大量获取动物性食物而缩小消化道,可以节省许多能量以供应大脑,即所谓的“昂贵器官假说”。
除了小肠和结肠的比例之外,消化道中另一个与饮食构成密切相关的因素是胃环境的酸碱性。学界一直把高酸性的胃部环境视为理所当然,其实在动物界中,极低的胃部 pH是很少见的。因为无论是生产强酸,还是保护胃部不受酸伤害,都需要更多能量,所以除非必要,动物不会发展出很高的胃部酸性环境——这是一种昂贵的身体配置。胃部酸性的主要功能有帮助分解蛋白质——酸性环境除了能直接灭活、分解许多蛋白质外,还能将胃蛋白酶原激活成胃蛋白酶,并保证蛋白水解的正常进行;过滤伴随饮食的外来微生物,减少感染风险,维持肠道微生物群的稳定。因此,饮食中的蛋白质越少,越不需要胃酸。植食动物的胃部通常有着很低的酸性(pH多在3~7),肉食动物中的腐食动物都有着极高的胃部酸性(pH<2)。由此可见,人类与各类动物的胃肠道结构、功能存在着巨大差异。在科研过程中,常采用大鼠、小鼠进行包括饮食实验在内的各类实验,由此产生的实验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将来仍需寻找更加贴近人类胃肠道结构功能的动物模型进行更好的研究。
二、肠道菌群参与人体多种疾病发生发展,提供了整合医学范例
人的一生是与肠道菌群休戚与共的一生。从先天由母体获得的少量微生物,到后天随人体生长发育逐渐在肠道内安营扎寨,扩充增殖的庞大军团,再到由人体自身衰老或外界病理因素所致的菌群生态失衡、数量衰减及相伴而来的肠道疾病,肠道菌群一直同人类并肩同行,形影不离地走过生老病死。这些数以万计、种类繁多的肠道微生物构成人体的另类器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与人体肠道健康及肠道疾病息息相关。肠道菌群包含千种细菌,其数量超过人体自身细胞的10倍,基因总数更是达百倍以上,并具有多种多样的生理功能。从整合医学的观点出发,健康的肠道菌群不仅可直接作用于肠道本身,促进肠道生长发育,参与食物消化吸收及物质代谢转化,形成肠道黏膜屏障,保护机体免受外来病原菌或理化因素的直接侵害,刺激、塑造、调节局部黏膜免疫;还可通过脑-肠-微生物轴等通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全身多种系统继而间接调节肠道的生长发育、消化吸收、代谢分泌等生理过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疾病被认为与肠道菌群生态失衡和功能失调有关,从类风湿关节炎、糖尿病、哮喘,到自闭症、肥胖、心血管疾病等,虽然临床应用粪菌移植、益生菌和益生元补充等来治疗这些疾病的机制尚未被阐明,但也改变了西医对疾病治疗的理念,体现了整合医学实践。肠道菌群一方面直接作用于肠道本身引发的肠道疾病,如肠道菌群失调相关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腹泻、便秘、肠易激综合征;局部菌群屏障减弱引发的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相关肠道感染;肠道菌群结构变化、肠黏膜局部免疫稳态破坏及免疫应答异常激活等因素相关的炎症性肠病、肠道肿瘤等。另一方面,肠道菌群可通过作用于全身其他系统影响肠道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如通过改变脑-肠轴的功能反应调节机体激素分泌,诱发自主神经反应,激活情感应激通路等参与炎症性肠病的发生发展;通过调节血液循环中生物活性因子水平及机体免疫功能等参与肠道肿瘤的发生发展及其对抗肿瘤治疗的反应。因此,在对肠道菌群和疾病相关性的探索研究过程中,应当运用整合医学思维,全面、系统、综合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中找到有效的预防及治疗策略。
三、内外科整合的肠病实践逐渐深入,传统内外科格局被打破
肠病学领域内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内外科的界限逐渐模糊,如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已成为早期癌症切除的技术,免除了开腹手术的痛苦和器官的切除,但与此同时常会带来一些新的治疗选择决策。针对组织学侵犯较深、早期转移可能性更高的“交界性”病例,需要内外科和病理等多学科整合诊治讨论进行抉择,有些高危病例即使进行了内镜切除治疗,仍需要追加手术。因此,多学科参与的治疗、护理、监测随访等全程整合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外科理念的不断更新,原来单纯地彻底切除病变逐渐转变为在追求*佳康复效果的目标下,实现彻底切除目标病灶的同时,充分保证剩余器官结构的完整性,*大限度地保留脏器功能。对于外科的要求也从 resection、repair、replace到 regenerate、rehabilitate、rejuvenate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意味着手术风险更高、难度更大,对医护团队的挑战更大、对手术技艺要求更高。在上述理念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肿瘤手术不再盲目追求切除范围的扩大,而是在保证肿瘤根除效果的基础上,尽量保留更多的器官功能。扩大根治范围并不能带来更多的远期生存获益,扩大根治术越来越少见,如目前直肠癌手术几乎已不做侧方淋巴结清扫,因为上述术式扩大了患者的创伤范围,由此带来了手术风险及并发症的增加,麻醉时长的增加,影响术后康复,但在患者远期生存方面的贡献却不大。与此同时,微创外科技术不断发展,微创外科的理念也不断更新。从手术入路、手术途径、手术范围的微创发展到身体、心理等方面综合的微创,而不再仅仅追求切口的微创。由此发展而来的快速康复外科学,倡导消化道手术早期经口进食,术后早期恢复活动,术前不再肠道准备,术中尽可能缩短手术麻醉时间等。目前,麻醉微创、切口微创、组织微创、术后康复微创等一系列措施已成为身心综合微创的重要途径,被越来越多的同仁所认可。由此可见,上述举措充分体现了整合医学理念在临床医学实践中的运用。
四、关注儿童和老年人肠道健康,是当下社会的迫切需求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8.7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除了正常的生理变化外,许多因素,包括环境暴露、获得性遗传性改变、药物治疗等,都会导致正常胃肠功能的破坏增加。老年患者食管和胃部疾病的发病率高,运动异常、胃食管反流、反流并发症、胃溃疡和胃肠道出血的发生率更高。类似地,下消化道疾病,如盆底疾病、便秘、腹泻、憩室病、炎症性肠病和结直肠癌,在老年患者中出现的频率增加并且通常不典型。老年患者也面临独*的营养挑战。由于小肠绒毛退化影响吸收,小肠肌间神经丛神经细胞数量减少等可能导致营养吸收减弱,营养不良也是常见问题。针对老年患者制订临床决策的过程也面临更多的并发症风险和不确定性。生命的本质必然由健康走向衰老、衰竭,躯体失能、失智,器官功能到达极限,老年人自然衰老常与病理改变相并发,存在多病共存、互相激惹的情况,针对老年群体的治疗更应注重整合医学思想的融入,并体现较浓的人文关怀。
另外,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放开,关注儿童肠道健康、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也是社会的迫切需求。人体在不同时期肠道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在结构上,新生儿、婴幼儿和儿童的肠道长度相对比成人长,为身高的5~7倍,但婴幼儿的肠壁薄,黏膜脆弱,肠系膜长而薄弱,结肠没有明显的结肠带与脂肪垂,升结肠与后壁固定差,容易发生肠扭转和肠套叠;在功能上,肠道长有利于增加肠道消化和吸收食物的面积,以满足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需要,但儿童肠液中各种酶含量较成人低,其消化吸收功能弱,且肠壁薄,导致通透性增高,肠道屏障功能差,肠内毒素等消化不全产物和过敏原,可以经过肠黏膜进入体内,引起全身感染和变态反应性疾病,且婴幼儿神经系统功能发育不完善,在其他系统有症状时,如发热、感冒等均可影响其肠道运动及分泌消化液的功能,导致食欲缺乏、呕吐和腹泻。儿童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乳糜泻、食物不耐受或营养不良发生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国民健康和人口素质,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需要关注的是,很多肠道疾病都是慢性的或无法治愈的,不仅影响孩子的童年,还会影响他们的整个成年生活。这些疾病的管理策略需要更加广泛的多学科讨论,不仅关注短期的适宜治疗策略,还需关注长期的改善效果。例如,儿童 IBD发病率高,需要儿科胃肠病学者、外科医师、营养师、护士和心理学者组成的团队进行多学科整合诊治(MDT to HIM)讨论联合制订策略,对于改善预后至关重要。对于儿童 IBD如何制订个体化的干预措施?如何应用新技术的发展(包括高通量测序、菌群相关研究)更好地理解遗传性因素和细菌因子在肠道炎症中的作用?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理解仍然存在许多不足,需要不断进行整合研究。
五、中西医整合肠病学兴起,双剑合璧荡疠气
我国传统医学对肠道也有独*的认识。据中医脏象学说,“肠”是“六腑”之一,属于多气多血的阳明经络,为“传导之官”,肠与肺互为“表里”,主要功能是传导糟粕和吸收津液。大肠的传导与肺气的肃降、胃气的通降、脾气的运化及肾气的蒸化和固摄作用有关,体现了维持肠道健康稳态和预防其他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具有重要联系。西医治疗主要采取“辨病治疗”和“对症治疗”的方法,起效快,但有些肠道疾病如肠道功能性疾病,西医治疗存在一定难度,有“无处下手”的感觉。中医治疗注重整体,主要采取“辨证论治”方法,大多起效慢,疗效持续时间长。中医学认为,肠病的病因以正气虚损为内因、邪毒入侵为外因,两者相互影响。小肠病常见病机为小肠虚寒、小肠实热、小肠气痛,治疗宜温通小肠、清热泻火、理气止痛;大肠病常见病机为大肠燥结、大肠湿热、大肠寒湿、肠痈、大肠虚寒,治疗以泄热通便、清利湿热、温化寒湿佐以行气散寒、清热化瘀并解毒散痈、温中散寒为主。中医治疗主要是针对症状的缓解,特别是肠道功能性疾病,而对大多数肠道器质性疾病却“力不从心”。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