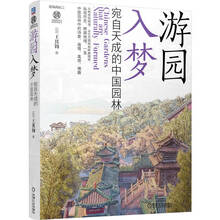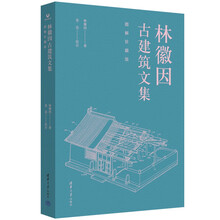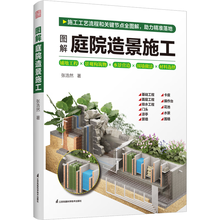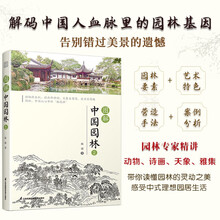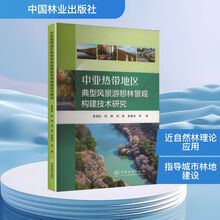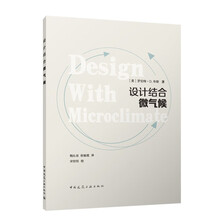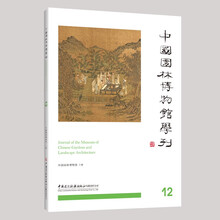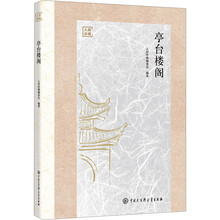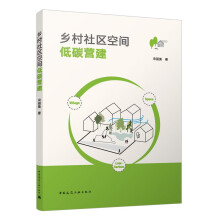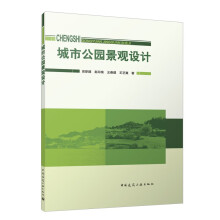比起其他的因素,中式建筑这一新奇的艺术风格被接受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游戏感。中国艺术风格的建筑设计一直局限于小型建筑,因此园林给这类建筑提供了恰到好处的环境。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式建筑中存在一些不是小型建筑的例外,比如特里亚农瓷宫(Trianon de Porcelaine, 图38)、皮尔尼茨宫(Pillnitz, 图39)、在德累斯顿的日本宫(Japanese Palace, 图93),以及再晚一些的,位于巴勒莫(Palermo)附近的法沃利塔别墅(Villa Favorita, 图92)。这些建筑所体现出的中国艺术风格本质上只是装饰艺术,只不过因为对中国艺术风格建筑一时的兴致,而将这种装饰艺术的规模远远扩大了。梅索尼埃(Meissonier)为圣叙尔比斯教堂(St. Sulpice)所绘的设计平面图可以追溯到1726年,圣叙尔比斯教堂也体现出了中国艺术风格的影响。当然,教堂建筑不会刻意模仿中式建筑,但考虑到圣叙尔比斯教堂的曲面屋顶和屋檐下火焰状的装饰图案,人们无法完全否认中国风建筑对它的影响。圣叙尔比斯教堂的建筑设计让人想起带有青铜镀金装饰的中国青花瓷瓶,这种花瓶那时在法国很受欢迎。圣叙尔比斯教堂带有内敛优美的线条,周围点缀着一连串洛可可风格的装饰物。梅索尼埃设计的圣叙尔比斯教堂被否决了,因为这种装饰风格不符合法国人的古典主义建筑审美,而古典主义建筑的美学概念在法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只有曲面屋顶的设计进入了重要建筑的领域,这种屋顶让建筑的轮廓更有生气。然而,曲面屋顶*常见的建筑形式,也就是复折式屋顶,采用了折曲线设计,因此与中国的曲面屋顶有很大的不同,以至于你甚至看不到两种屋顶设计之间存在什么直接关联。
在十七世纪以及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风格(chinoiserie)的发展历史与装饰艺术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在他*具解释性的作品中,赖西魏因(Reichwein)详细地描写了这股中国风潮。在瓷器、漆器、家具等领域都有学者对中国艺术风格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法国,柯迪尔(Cordier)对有关中国风格的研究做出了概括性总结。
西方将中国看作远东的丝绸之乡的这种认识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在之后的岁月中,中国和欧洲的贸易从未停止。根据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游记(1272—1293),我们可以对十三世纪的中国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那是一片富有而奇妙的东方国土,是之后哥伦布尝试从海路到达的目的地。在葡萄牙人通过海路绕过非洲、使通往中国的航路成为可能之前,来自中国的货物和消息都要经过漫长且艰难的旅途才能到达欧洲。这一路上要经过很多中间站,货物和消息在众多中间商之间几经转手,以至于只有寥寥无几的远东知识被传播到欧洲。然而,在葡萄牙人于1515年首次到达中国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世界上新的国家被发现,欧洲人被激发起了对陌生国家及其居民的浓厚兴趣,而随着兴趣的增长,欧洲人对异国的商品也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尤其是对“东印度的货物”—那时候所有从南亚和东亚进口的货物都被称作“东印度的货物”。在十六世纪的东亚贸易中,葡萄牙人是唯一的主导者,十七世纪的时候,荷兰人取得了贸易上的霸权,在十八世纪,贸易霸权又转移到了英国人手中。法国人从这些航行远洋的国家那里收获了来自中国的商品,同时也收获了许多来自远东的灵感,并把这些灵感吸收和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法国人在所有时尚和优秀品味相关问题上是拥有独断权的,而正是他们赋予了中国风格重要的地位。中国艺术风格正是从巴黎开始征服欧洲,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式园林的特征才和法国园林的特征混合在一起。因此,装饰性中国风建筑领域的任何研究都应从研究法国的中式建筑开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