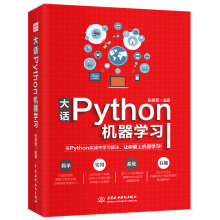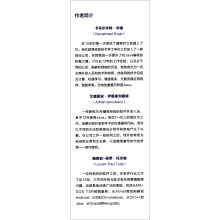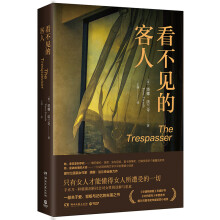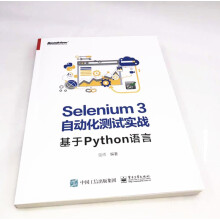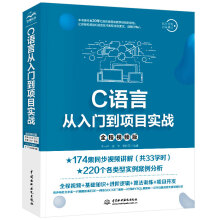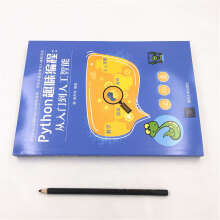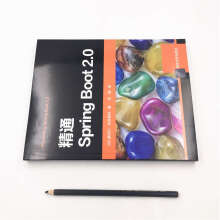《行走姑苏:城市更新 琢玉苏州》:
远,远方的城市更新。
很多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比我们早。因此,积累了诸多与城市更新相关的规划理论:
19世纪下半叶,工业大生产带来经济高速发展,而经济高速发展催生快速城市化。霍华德基于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关注,一直在探索城乡接合、分散布局的理想“田园城市”。
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大都市的城市更新与规划建设中,柯布西耶崇尚机械理性主义规划,强调机械之美、集中之序。他以横平竖直的视角来布局城市,最好还能充分表达纪念性与象征意义。
介于分散主义与集中主义两者之间的,是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芒福德更强调人的价值,强调文化要素对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盖迪斯把自然环境禀赋和周边乡村拉入视野,认为景观与人的工作生活方式必须协调发展。而汽车的普及,让莱特产生了低密度“广亩城市”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城市破坏巨大,很多大型城市完全是从废墟上“重生”。同时,随着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解决随之而来的住宅匮乏问题,在美国、欧洲,新城和卫星城大量涌现。郊区化、新城化使得城市中心的作用降低,旧城区呈现衰败。旧城区中,最初的城市更新方式简单粗暴,即推倒重建。
这种城市更新的方式破坏了城市文化特色和传统邻里体系,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雅格布斯批评大拆大建式的城市更新,提出城市的本质在于多样性,城市的活力也正是来自多样性。整整一个甲子后,她的观点读起来还让人有所感触:
街边步道要连续,有各类杂货店铺,才能成为安全健康的城市公共交流场所。公园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并不是当然的活力场所,周边应与其他功能设施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公共场所的价值。
城市应该分解成高效的、尺度适宜的社区单位。城市地区至少要有两种主要功能相混合,以保证在不同的时段都能够有足够的人流来满足对一些共同设施的使用。
街区要短小,社区单元应沿街道来构成一个安全的生活网络。城市需要不同年代的旧建筑,不单因为它们是文物,,而是因为它们的租金便宜从而可以孵化多种创新性的小企业,有利于促进城市的活力。
大型旧城改造工程,特别是救济式住房项目,不能与城市原有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相割裂,改造后的工程必须能重新融入原有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肌理……
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普遍对于城市更新进行了反思,也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其中,特别强调保留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大量新建城区的结构引导与优化作用,一方面使得旧城区的城市中心作用不断弱化;但另一方面,旧城区也得到喘息机会,历史建筑、历史城区的保护工作日益被社会各界重视。
70年代起,由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工作全面展开。在开展城市更新规划时,政府更加重视对于经济、人文、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也有很多城市,以地产机构为主,进行开发式更新。90年代后,在城市更新中,更多是以政府、社会资本、社区居民等多方参与、共同发力。
可以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的城市更新从推土机式的重建,政府福利导向的改造,地产导向的旧城开发,一直走到现在。目前,普遍做法是政府主导规划政策,引导激励社会资本投入,社区积极参与,形成多方协调合作的城市更新机制,可以说是建筑、环境、经济和社会多维度的社区复兴。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城市的运营方式,也深刻改变了规划的技术手段与思考逻辑。从最初的数据模拟,到了如今的数字孪生城市。同时,对城市人文环境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刻。近年来,文化、生态、碳达峰、海绵城市、绿色发展等理念,也在城市更新中有越来越多的体现。
每个城市有各自的特点,理论提供的是一种思考方式。近现代西方城市更新理论十分庞杂,我们点到即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