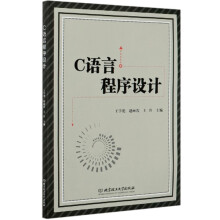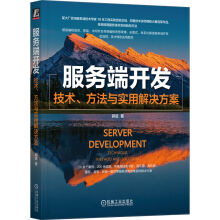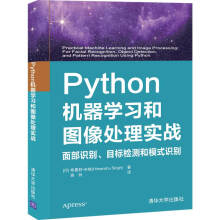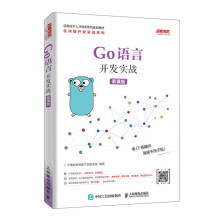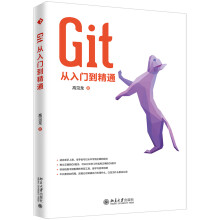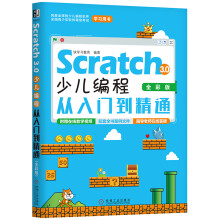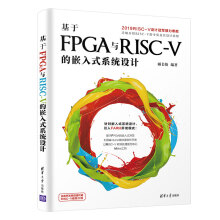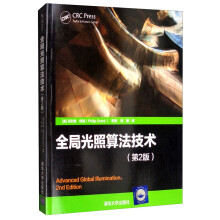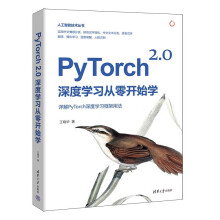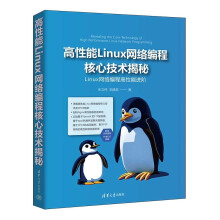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西部乡村是我国乡村全面振兴的难点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大国。建设富美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是我国政府的长期目标。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并逐渐从人口空心化演化为人口、土地、技术、产业、服务、文化和公共设施整体空心化,一些农村经济社会陷入整体性衰落与凋敝,尤其是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农村更甚(刘彦随等,2016)。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且在乡村表现得*为突出。西部乡村生态脆弱、区位偏远、设施不足、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文化多样性突出、旅游资源富集、人地协同可持续发展机制欠缺(刘小鹏和苏晓芳,2014)。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意志”,是我国“三农”工作的主要抓手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标志性目标。中国已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不同于相对发达地区乡村直接向乡村振兴聚焦发力,欠发达的西部乡村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期,同时面临着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两大历史任务,是我国乡村全面振兴的难点所在。
2.旅游是西部乡村人地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
贫困是某一地区在多种因素制约下人地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党中央、国务院把旅游确定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工作。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相关部委日益加强深度合作。2014年底,全国6130个村被列入旅游扶贫重点村,2015年560个村开展旅游扶贫试点,并将旅游扶贫列入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积极探索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旅游助力脱贫经验、道路及模式,是明确这些重点村和试点的应有之义。乡村旅游扶贫的本质是通过旅游业改善村民的生计方式,建构新型人地关系(李燕琴,2018)。我国不少文化原真性和生态多样性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且内生能力不足的西部乡村通过旅游扶贫消灭了绝对贫困,但仍是我国欠发达地区。西部乡村旅游发展面临人财等要素资源短缺、硬件设施建设滞后、产品创意品位不足、管理服务不够规范、产业质量效益欠佳、社会文化和生态风险突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脱贫成效难以巩固、与乡村振兴衔接不畅等问题。其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科学构建乡村旅游中的人地协同发展机制,以实现由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西部乡村旅游如何让人地两个交互约束的系统实现协同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是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书将“乡村旅游”与“人地协同发展”研究有机相连,多层面、多维度地剖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构建西部乡村旅游中人地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定性、定量分析人地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和约束条件,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人地关系协同发展的内涵、特征、要素、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从个体-区域协同发展的视角测算旅游助力西部乡村发展绩效,不仅注重外部多元帮扶,也强调内部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不仅关系到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旅游已然成为当地农户的新生计之后这一新生计的可持续性。考察西部乡村旅游中的个体-区域协同发展要素和过程,测算旅游助力乡村发展的“贡献”,明确各利益主体的责任和激发各自潜力,从而实现人地协同发展,进一步夯实旅游助力乡村发展的理论基础,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理论体系。
2.现实意义
为实现我国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需要依据西部乡村的人地关系现状、人地协同可持续发展潜力制定应对策略。本书紧扣西部乡村旅游中的人地协同发展这一主题,通过理论梳理、现状把握、实证分析、比较借鉴、调控对策等几大板块的系统研究,坚持统筹发展,突破传统思维,从人地协同发展的视角分析西部乡村旅游中人地协同发展的要素与结构、特性与演化、作用与机制、协调与优化,为西部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借助人地协同发展这一先进理论建设富美乡村、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案例支撑、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目标提供有益借鉴。
1.2 研究进展与述评
早在1996年旅游助力欠发达地区发展研究就成了国家旅游局的重要调研议题,并成为我国旅游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点,并由此经历了起步、初步发展、快速发展三个阶段(李佳等,2009a)。现阶段已批准建立了六盘山、内蒙古阿尔山、河北阜平、江西赣州和吉安5个国家旅游发展试验区。1999年4月,英国国际发展局提出了PPT(Pro-Poor Tourism)的概念,使旅游助力发展成为世界旅游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并在尼泊尔等6个国家(4个非洲国家、1个亚洲国家和1个拉丁美洲国家)开展了一系列PPT个案研究,形成了一系列PPT项目报告(Poultney and Spenceley,2001;Karin and Jurgens,2001;Naomi,2001;Nicanor,2001;Williams et al.,2001;Braman and Amazonia,2001;Renard,2001;Cattarinich,2001)。2002年8月,世界旅游组织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首次提出ST-EP这一概念。ST-EP在PPT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旅游的可持续性,因为只有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低收入人口的持续旅游受益。
1.2.1 主要研究内容
1.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的资源基础
我国中西部民族欠发达地区、乡村地区和生态旅游资源富集区存在叠加性(肖胜和,1997;马忠玉,2001;荣金凤等,2007;王兆峰,2011)。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多为文化或地理边疆的民族地区(李燕琴和束晟,2015)。民族地区是涵盖地域文化、建筑节庆、民族传统生计等自然和人文要素的民族聚居区(高永久和朱军,2009),是人类千百年来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基础上生产生活所形成的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特征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崔海洋,2009)。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新时期巩固脱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刘南勇,2012)。西南民族欠发达地区呈现生态脆弱地区、民族自治地区和省界或边境地区“三重耦合”的空间特征,云贵川的边界地带是欠发达重灾(度)区(向玲凛等,2013)。西南民族农村收入严重不平等,低收入问题严峻,基础设施薄弱,公共品匮乏,贫富分化明显,农户抗风险能力弱。土地、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和民族特征的差异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耕地和物资匮乏、民族特征是主要致贫因素(杨栋会,2009)。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地震、干旱、滑坡、泥石流、洪灾、低温冷害等自然灾害频发地带,自然灾害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民脱贫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庄天慧等,2010)。在市场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地方性文化与主流发展话语不相容是西南民族地区久扶不脱贫问题的两个关键因素(杨小柳,2010)。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方面的发展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未来的脱贫政策应注重向社会公共服务保障和脱贫项目的目标瞄准(向玲凛和邓翔,2014)。旅游业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人地关系的变迁,带来了社区重构(Li et al.,2016)。民族地区旅游与区域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曾本祥,2006)。
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使旅游成了民族欠发达地区居民的重要生计选择,当地民族生计方式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发生变迁(Donaldson,2007;Liet al.,2016)。旅游生计方式为民族地区发展带来了就业机会增多、经济收入增加、妇女地位提高、民族意识增强等积极效应(Yang and Geoffrey,2009)。然而,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居民生计变迁会造成社会结构破坏(左冰,2016)、相关利益群体间冲突(Matthew and Harold,2000)、过度商业化(保继刚和林敏慧,2014)、民族语言消失(刘宏宇和李琰,2011)、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陈佳等,2015)等问题。研究表明,旅游多功能发展能降低生计脆弱性,提升可持续生计资本(史玉丁和李建军,2018)。
国际上的旅游助力欠发达地区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Spenceley et al.,2010;Job and Paesler,2013;Kiernan,2013)、文化遗产旅游地(Poyya,2003;Hampton,2005;Suntikul et al.,2009)和乡村农业旅游地(Torres and Momsen,2004;Rogerson,2012;Pillay and Rogerson,2013;Rid et al.,2014)。
2.旅游助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效应
从经济效应看,旅游能提高社区居民从业和收入机会,促进收入增加,优化地区产业结构(蔡雄和连漪,1997;Ashley et al.,2000;张伟,2005;张遵东和章立峰,2011)。但也可能由于外来资本占据了本地的大部分旅游市场,旅游漏损严重,存在经济风险与限制(Taylor,2001;刘筏筏,2006;张小利,2007;Scheyvens and Russell,2012)。此外,旅游对当地群体的影响并不均衡,高收入群体旅游获利高于低收入群体(Blake et al.,2008),如在南非Meander地区,黑人社区的旅游受益十分有限(Rogerson,2012)。
从非经济效应看,旅游发展优化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制度(Wall,1996;冯灿飞,2006)促进就业(Mitchell and Ashley,2009)、性别平等(Scheyvens and Russell,2012)、教育与文化传播(Ashley et al.,2001)、中小微企业发展(Rogerson,2012)以及跨产业部门的合作(Meyer,2004),但也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增大、犯罪率上升、社会文化冲突加剧、地方民俗文化商品化和同化等社会文化问题(Gurung,1991;Zurick,1992;Nicholson,1997;刘筏筏,2006)。随着旅游活动的深入开展,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向延平,2011)。旅游开发能促进自然生态保护(良警宇,2005;陈巧等,2006;常慧丽,2007;Saarinen,2010)。国际上的研究同样发现,PPT的非经济效应也很显著,如交通、健康、卫生的改善及当地人素质的提高(Lepp,2007;Muchapondwa and Stage,2013;Hadi et al.,2013),并深入分析了影响旅游助力脱贫效果,发现年龄、第二语言、旅游线路的控制程度等是影响旅游从业的重要因素(León,2007)。
3.旅游精准扶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经历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贫困县瞄准为重点、区域和个体双重扶贫瞄准等阶段性演进历程。精准扶贫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期的新机制。其目标在于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优化配置扶贫资源,实现扶贫到村到户,建档立卡与信息化建设、干部驻村帮扶工作制度和精准考核机制的建立等是其重点工作(黄承伟和覃志敏,2015)。新时期中国农村亟须创新精准扶贫机制,推进精准扶贫综合战略和“六度”评估(刘彦随等,2016)。实践中存在精准识别可能排斥低收入人口,帮扶供需尚未*优匹配,资源动员非制度化,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黄承伟和覃志敏,2015),农户对互助资金借贷率不高(丁昭等,2014)等多种排斥问题(邓维杰,2014)。关于原因,学者们认为在于信息不对称(陈准,2011),瞄准机制和识别系统不统一(汪三贵和Albert Park,2010),农户参与方法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