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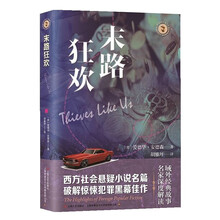






天津卫南市源德公寓2号院呈长方形,四周的房屋相围像棺材,每层楼由天桥连接,属于典型的大杂院,像口琴孔那样家家小屋紧紧相挨。中间直通一楼底的天井,幽深如深井。1945年的“红绣鞋案”把百户人家全部卷了进去。
前警察局长和私家侦探密友联手办案,意外死亡接踵而来,案中有案,每个住户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谎言中有真相,真相中有谎言。悬念丛生,尽显复杂人心。
穿越近百年,再现上世纪40年代天津卫普通女性之间的恩恩怨怨与悲欢离合。津腔津韵,折射世情百态与人性幽微。
融合了侦探、悬疑、历史、爱情、推理、抗战、江湖、黑道等元素,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小说。盘根错节,犹如一出出连环戏剧: 《绣鞋计》《连环套》《移花接木》《捉放曹》《桃花扇》……
第一章
1
1945 年农历八月的一天。吃过晚晌饭不久,源德公寓 2 号大杂院的人们隐约听见胡同外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声如潮。就在大家正纳闷的当口儿,七婶站在一楼天井里,一手掐腰一手挥舞,扯着脖子喊:“大伙儿听好喽,电匣子播得真真儿的,小日本在美国大火轮(船)上签字降服啦,抗战得胜啦!我的妈耶,可盼到今天喽!往后咱们可以大米、白面随便吃啦!上边叫家家户户全出去庆祝哇!”闻信,大杂院里的人们纷纷涌出家门,携老挈幼地奔出胡同、跑向大街,融入汹涌喧嚣的人群。受尽了欺压屈辱的人们,此刻将积压在心头的愤懑统统发泄出来,欢呼雀跃,喜极而泣。几个半大小子拿砖头砸着一家紧紧闭户的日本大烟馆,边骂边砸,围观的大人拍手叫好。
十一点多钟光景,七婶独自折返大杂院。院里灯光全熄,无一丝光亮,唯有天井黝黑,寂然无声,稀薄的月光星星点点地洒落下来,显得十分怪异且清冷。她猛然哆嗦一下,打了个寒战,一种本能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无意间抬头,发现三楼天桥影绰绰地吊了个女人,再细瞧,女人穿着粉白色长袍睡衣,垂发掩面,麻绳一头系着女人脖颈,一头拴着天桥的栏杆……顿时,七婶汗毛倒竖,吓瘫于地。片刻,她艰难地爬起来,疯了般向外跑,连哭带喊:“出大事儿啦,救命呀,大院里有吊死鬼儿……”迎头碰见正返回大院的人们,大家随七婶心惊胆战地奔进天井,一个邻居认出了上吊女人:“哟,那不是唱评戏的覃姨吗?”几个老爷们儿壮着胆子,上了三楼,解下绳子,把覃姨放了下来,此时覃姨已经彻底凉了。七婶张罗着将覃姨抬回家,安放在床板上,用被单覆盖住全身。
此时院里的所有人再无睡意,围拢一块儿七嘴八舌地悄声议论着:“覃姨活得好好的,干吗寻死啊?”“多漂亮的人儿,三十多岁的年纪,正是鲜花开得最艳的时候,这说走就走了。” “覃姨孤苦伶仃一个人来一个人去,着实太可怜呀。”
七婶镇定许多,她必须镇定,因为她是副保长,是大杂院的头头儿。她冲大家喊:“全回屋歇着,赶明儿我请警察查案。”
众人各自回了屋。天井静默下来,七婶连跑带颠儿地奔进家,倒插门关严,不放心地隔窗户朝外张望。躺凉席上的爷们儿斜眼老贾嘟哝道:“甭瞅啦。覃姨死得不明不白的,说不定含冤而死,冤死鬼天上不收,进不了地府,时不时会在大院里飘来荡去。”
一番话吓得七婶缩回脑袋,拉紧窗帘。忽闻天井里一阵“啪嗒啪嗒”的脚步响,七婶“噌”地蹿上床,扎进老贾怀中不停打战。斜眼老贾推开她,说:“大热天的你黏糊我干吗呀?没闹鬼。那是霞姑的二虎收了煎饼馃子摊儿回院子。”
此夜,大杂院里家家灯光通明。
次日清早,七婶红肿着眼泡,同爷们儿斜眼老贾一起搬着八仙桌子和俩凳子放在天井。斜眼老贾在永安大街开家杂货铺,他得去卸门板营业,提前走了。
七婶生炉子烧水,用高沫沏了一壶酽茶放在桌上,然后跷着二郎腿坐着,点了根烟卷抽了起来,专等警长孙春英到来。
在玉清池澡堂子前摆“大碗茶”的霞姑领着四闺女大梅走下楼梯,靠近来顺手抓了一把茶叶,说着便宜话:“七婶呀,我借你点儿茶叶使使。摆茶摊儿我用茶砖,今儿拿你的高沫儿沏,叫那些喝茶的常客尝尝鲜儿。”七婶老大不高兴:“你摆摊儿挣钱用我的茶叶,小算盘打得精。”霞姑嘴不饶人:“七婶呀,当我不知道,你的茶叶不是大家伙凑钱买的?里头有我一份呐。”言罢,拽大梅匆匆走出院门。
将近晌午,警长孙春英带名警员晃荡荡踏进大院。七婶跳起来,迎上前,满脸赔笑地说:“小孙呀,你可来啦。我们院子出了大事儿。先抽烟、喝茶,歇歇气儿再办案。”孙春英接过七婶递的烟卷,放鼻尖嗅嗅,点着嘬一口,说:“七婶,办案要紧。你立马带我俩到案发现场。”七婶指指天井,又指指三楼天桥,说:“现场就这儿,昨夜个住二楼西北角的覃姨跑三楼上吊,人已经没气了,停尸她自个儿家。”孙春英闻言,惊掉了烟卷,“嘛玩儿死人大案呐?抓着凶手了吗?”七婶说:“哪来的凶手,她兴许自个儿寻的短见。”孙春英教训起七婶:“您当副保长一个月二十块大洋,比我挣得多,不许胡编乱猜。你红口白牙愣说她自杀,真凭实据呢?断案拿贼得靠我们警察判断。”
“对对,孙警长,烦劳您到覃家查案断案。”
孙春英却一屁股坐凳子上,说:“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带了警法科警医小吴。这在从前叫仵作。
这小伙子灵着呐。你领他去吧。”言罢,自己斟杯茶,慢条斯理抿起来。
不大工夫儿,天井一下子聚拢了很多人,远远站一堆儿伸头探脑、窃窃私语。等候两个多小时,警医小吴和七婶满头大汗返回,警医小吴向孙春英汇报:“死者覃淑芳,二十八岁,曾经为国光评剧团演员,现歇业在家。经验:死尸已被移动,现场遭到破坏。她死于昨晚七点至十二点之间,身无外伤,脖颈呈半圆勒痕。初步判断自杀可能性大。现场遗留死者红色绣花拖鞋两只,一只掉落天井,一只丢在后胡同;另外死者明显喝过大量烈酒,酒气今晨仍能闻到。此两种甚为可疑。”
晌午已过,孙春英起身冲众邻居说道:“瞧见没有,警察办案利索又细致,我赞同小吴警官判断,覃淑芳自杀无疑,你们街坊邻居的,念她孤身一人,大伙凑钱买棺材葬喽。我回警局复命结案。”七婶狐疑地问:“覃姨好么秧儿的,为啥自杀啊?另外,唱戏的嗓子是本钱,齁儿咸齁儿辣的全不行,喝酒更坏嗓子!覃姨一直都是滴酒不沾的,你断得准不准啊。”孙春英一脸不悦,说:“七婶呀,你纯属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女人自杀可能性多了,比如负债累累、恋爱受挫、情绪不稳定、一时想不开,等等。心情不好借酒浇愁呗,合情合理。对了,昨天是日本鬼子降服日,她为啥偏偏在全国庆祝胜利日的时候自杀?
怎么着,对抗战胜利心怀不满而心生绝望?备不住属于政治事件呢。国民政府大员即将接手城市,首要惩办通敌分子、狗汉奸,我回去查查档案,覃淑芳是否存在通敌嫌疑。”
七婶见他越琢磨越悬乎,匆忙往他手心塞几张票子,说:“你断得准,覃姨光会唱戏,哪有本事通敌?她兴许真是一时想不开自杀。没别的。”
孙春英带小吴离开大杂院后,七婶疑虑重重,警察一群白吃饱。覃姨死得糊里糊涂,冤呐。冤死人的魂儿不散,真如爷们儿斜眼老贾所讲的那样,鬼魂整日里在大院游荡。那还了得,吓死人呐!必须另请高人,查明覃姨死因。
七婶思来想去,琢磨到我舅舅——私人侦探秦少明头上。
2
当天下午,七婶蹑手蹑脚地溜进源德公寓 1号院,1 号院属于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平时由我姥姥与女用温姨住。温姨住一楼,我姥姥住二楼。
当时我姥姥正午睡,被七婶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赶忙披衣下到一楼客厅。七婶哭丧着胖脸,央求道:“秦奶奶,您老行行好,请您家的秦神探出山吧。覃姨死得蹊跷,我总觉着她的魂儿在天井里晃来晃去的。咱瞧不着覃姨,她瞧着咱,撞一块儿那可活见鬼啦!”
姥姥答应很干脆:“行吧,明儿一早我也去 2号院。”
我说过大杂院拢共有四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大房间,全在一楼,分别把着四个角。装饰奢华,租金贵,一般穷人是租不起的。我姥姥占一间,平时她待在 1 号院,房子总空着;七婶占一间,把前门口;林太太占一间;剩下一间由去年搬进来的女人租住,房子旁边通后胡同,租金最贵。
那女人独身,来历不明、长相特殊:棕红色头发,深凹眼,高鼻梁,白皮肤,像洋娘们儿,大杂院人们暗地里给她起外号“外国串儿”。
次日清早,我舅舅秦少明踏进姥姥家,七婶闻信儿屁颠颠地跑来。女用温姨沏两杯茶分别端到他们面前,舅舅犯矫情,说:“我饿肚子呢,空腹饮茶伤胃。”温姨立马下厨房热奶、煎蛋,被姥姥拦住:“先谈正事,晚吃会儿未尝不可。”
舅舅掏出烟斗抽,不放烟丝,不用煤油、打火机点,装样子。他装模作样地叼着烟斗,听着七婶讲述事情过程。七婶由于惊吓过度,前言不搭后语,连续讲了两遍,舅舅方听出点儿眉目来。
七婶舒口气,情绪平息下来,说道:“覃淑芳好人呐,是唱评戏的名角儿。甭看她素常不愿搭理大院的娘们儿,人老实巴交哇,从不招谁惹谁,不爱记仇,咋无缘无故寻死?总得有个缘由吧?警察小孙那个王八蛋,人命关天的案子不上心,晃荡一圈愣说覃淑芳是想不开自杀的,这个结果我不接受,我不信。警医小吴查着她上吊时掉了两只红色儿绣花拖鞋,一只掉天井,另一只落在后胡同口。秦神探你断断,覃淑芳在三楼天桥吊死,跑后胡同干吗去?哦,魂儿跑去的?”
舅舅管温姨要张白纸,从上衣口袋掏出钢笔往上面画,点头示意道:“七婶,您接着讲。”
七婶得到神探认可,来了劲头儿,滔滔不绝讲起来:“我猜你准扫听覃淑芳死前跟谁闹架。还真有。晌午前儿,煤铺的‘赛李逵’给覃淑芳背一筐煤球送进屋,二楼的陶娘多嘴多舌甩闲话,数落‘赛李逵’看人下菜碟儿,送煤一律倒门外过道,没见给哪家送煤送进屋,要不见人家年轻漂亮、趁钱,赶着巴结?搁平日,覃淑芳都不搭腔,昨天不知她怎么了,要不就是在外受了闲气,替‘赛李逵’拔闯,冲出家对陶娘说:“如果你年轻漂亮,他给你把煤球送进屋、送上床。”陶娘哪是省油的灯啊,对着覃淑芳破口大骂,覃淑芳也不示弱,还嘴怼她,二人一直闹腾到晌午才被邻居们劝开。”
舅舅依旧在白纸上画不停,随口问:“后来呢?”七婶翻白眼琢磨半天:“后来?后来经大伙儿一劝,都各自回屋了呗。哦,下午林太太、‘外国串儿’前后脚地上覃淑芳家劝解。在大杂院数她们仨关系走的近。”
眼瞅七婶没词儿了,舅舅将画好的纸递给她:“七婶,我画了张大杂院各家住户位置图,您在每家分别填上姓甚名谁,这就算齐活了。”
七婶接手里,焦急地说:“神探大侄子,您千万抓紧。停尸已经一天半,按老例儿七天后出殡。真要一时半会儿破不了案,下不了葬,尸首得放臭喽。”
舅舅根本不理会七婶,冲温姨喊:“我的早餐呐?”
七婶自觉多余,疑疑惑惑地走出 1 号院。姥姥对舅舅说:“你搬回家住多好,一人待外边多业障。”
舅舅风扫残云般吃光早餐,用餐巾抹抹嘴头,说:“谢谢老娘,我乐意住外边,自由自在没人管。”
姥姥嗔怪道:“看你自由自在能到什么时候?我托人给你找媳妇。我管不了你,让她管你。”过午,姥姥独自迈进 2 号院,连串两家门。头一家是陶娘。
陶娘似乎预知姥姥的来意,关严房门,拉上窗帘,又扒窗缝朝外瞧了瞧。姥姥捂住鼻子,问:“陶娘,你屋里嘛味儿?怪呛鼻子的。”
陶娘习惯把家捂得严严实实的,关门闭户不算,后窗糊了报纸,无一处透亮,黑乎乎像山洞。
她年轻时守寡多年,人懒心也懒,没心思拾掇屋子,床上被窝常年不叠,地上尿桶不倒,桌上碗筷不洗涮,一股酸溜溜、臭烘烘气味儿打犄角旮旯冒出来。陶娘嘴不懒,逢人便吹胡她的前死鬼爷们儿当过大官,住三进四合院,丫鬟、用人十几口,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出门坐包月车,天天上戏园子看大戏。若非爷们儿先抽大烟、后吸白面儿败了家,掏虚了身子,末了冻死街头成了“倒卧儿”,她也不至于带着七岁的儿子“一尺二”下嫁拉胶皮的酒鬼爷们儿董锡贵,搬进源德公寓这种穷地方。大院人们从不信她,给她起外号“瞎话篓子”。
陶娘四十岁出头,风韵犹存,脸蛋粉嫩,手修长,印证她曾有过优裕的生活。她现任丈夫董锡贵拉胶皮,黑脸膛,身材魁梧,谈吐粗俗,远近闻名的大“酒鬼”。两个不同阶层的人凑一起,吵架拌嘴似家常便饭,高下不言则明。陶娘很强势,董锡贵常常被陶娘轰出家门,蹲在楼道边举着瓶白酒“咕嘟嘟”扬脖灌,然后站楼道逞酒劲儿骂海街。
陶娘犹如遭受莫大委屈,说:“秦奶奶,您算大院明眼人,那帮娘们儿看不透的事儿您看得透。
我跟覃姨矫情两句,她至于上吊吗?瞎鬼!”姥姥说:“按常理儿不至于。偏偏你俩晌午打架,晚上覃姨就寻了短见,太巧了不是?”“寸劲儿嘛。”陶娘急赤白脸辩解,“咱大院历来的规矩:打架不揭短儿,打人不打脸。我倒骂了覃姨,但我讲口德,不揭覃姨臭底子,不讲犯歹话,她犯不着想不开。我嫁过大户人家当太太懂礼数,跟一个下九流的戏子较嘛真。可有一节,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傍黑,林太太偷偷摸摸上覃姨家串门,嘀咕半天才出来。秦奶奶,大院娘们儿哪个不有点儿见不得亮的丑事,明着不讲,暗地里说可挡不住。林太太爱挑拨离间,哼,难怪覃姨末了就……”
姥姥沉吟片刻,喃喃道:“覃姨死得离奇,真的自杀吗?备不住被人害死的呢?”
陶娘撅起嘴,说:“拿不准。大院水深着呢,明面一团和气,背地里谁对谁都龇牙。林太太呀鬼难拿,凡事不做,懒得光长肥膘儿。爷们儿小程子在饭馆跑堂,愣比她小十来岁,家里那么趁钱?来路不明呀。其实林太太恨覃姨,俩人有过节。我懂规矩,不挑明。秦奶奶,大杂院属您资格老,您得主持公道,替我做主啊。”
姥姥见问不出什么,便说:“陶娘你先歇着,我再转悠转悠。
姥姥辞别陶娘,敲响林太太的家门。
林太太三十来岁,矮个儿,虽然闲居在家,成天介描眉画脸、穿金戴银,活脱脱一个富贵人家少妇。她不明姥姥来意,热情地沏茶倒水,向姥姥显摆新入手的一枚碧绿的翡翠戒指:“房东奶奶,您老来得正巧,俺刚念叨您呐。”姥姥微笑:“念叨我做嘛?交房租差十多天,不急。”林太太亲昵地拉姥姥坐进床沿,说:“您老逗笑呐。咱大院数您心善、见识广,俺得了翡翠戒指,您老上法眼瞧个真假。”姥姥接过戒指,端详半天,说:“真,皇宫里的东西,哪儿淘换的?”林太太长脸笑开花:“瞒谁不能瞒您老。俺从‘外国串儿’手里买的,200 块钱。不要钞票非要现大洋。值不值?”姥姥肯定说:“那你占便宜啦,在中原公司买少说得翻两倍。”林太太喜不自胜,接手中把玩翡翠戒指:“‘外国串儿’家里趁货,珍珠翡翠、金银财宝装满小皮箱。您说她整天闲在家,咋藏着那么多稀罕宝贝?”姥姥纠正她:“甭总称呼人家外号,她有名有姓——苏洛娅小姐。”林太太讪笑:“咋不知道她叫啥,瞧她那模样儿,中不中、洋不洋的,说话‘叽叽嘎嘎’听不清,就忘了她的大名。”
姥姥直奔正题:“林太太,前天下午你去覃姨家劝架吗?”
林太太撇撇嘴:“俺哪有那份闲心?再说俺跟覃姨平时不对付,唱戏的角儿穷酸,凡人不理,干吗巴结她。‘外国串儿’,哦,苏洛娅小姐先去了吗,俺追了去,我为趁机会管苏洛娅套瓷儿,把戒指搞到手。”
“覃姨可有不正常的地方?”
“俺瞧不出来,覃姨光捂脸哭不搭腔。俺以为唱戏的能装,没往心里去,谁猜到她大半夜上吊了。”
“苏洛娅对覃姨说了些嘛?”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40
第三章 // 75
第四章 // 108
第五章 // 141
第六章 // 168
第七章 // 221
第八章 // 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