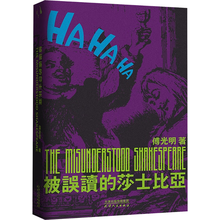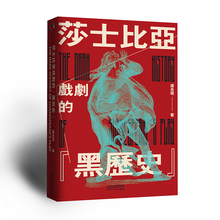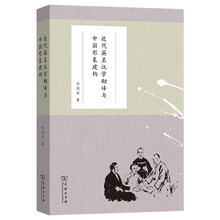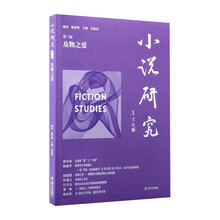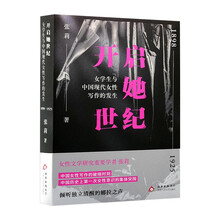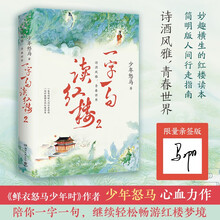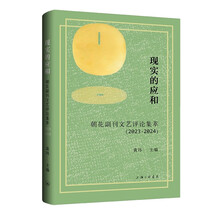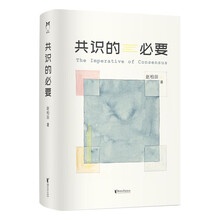正如勃兰兑斯和鲁迅提出的“流亡文学”和“侨寓文学”各自所处的特定的法国和中国历史语境,中国和美国的戏剧文学交流的动力亦来自于两种戏剧文化传统间的差异,因此,中美戏剧交流的历史,同时也是彼此互为文化他者,确认、否定并超越自我的历史。提出这一历史描述的立场和研究、写作的前提是必要的。这一写作立场决定了“中美戏剧文学交流史”的主旨是要探讨时间向度上的贯穿性问题,即在中美戏剧间的双向互动的各个历史阶段,二者是如何借助对方完成各自的“世界性”参与和“现代性”转化的。
在“传播有关别国特点和文化的知识”时,遭遇的第一问题就是文学译介中的语言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发生文化转向,侧重点由既往的是否忠实原作转移到翻译中的文化权力以及在目标语境中的文化功能。这个转向潜在地对既有的国别文学交流史研究和写作带来很多冲击。廖炳惠、朱耀伟等学者都曾借用罗伯特.J.C.扬的观点,主张把translation译/“易”为“翻易”,就是在强调跨文化译介过程中的翻译,同时也是改易的过程,它更强调“分歧、断裂、演现效果”。文化批评领域的这一实践成果,对我们审视、重构“影响一接受”的文化交流模式有着诸多启迪。
在“影响一接受”的文化交流模式中,处于弱势的一极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它面对强势文化的覆盖性冲击,往往会主动地加以判断、选择和创造;同时,它亦会给予强势文化造成回馈性影响,虽然二者存在着明显的话语逆差。这种事实存在于中美戏剧交流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该研究正是从这个思考基点和基本观念出发,清理中美戏剧交流的事实,并分析这个交流历史所隐喻的两种文化主体的自身认同。比如,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奥尼尔在中国的译介密度越来越大,其影响的发生几乎和中国现代戏剧(包括戏曲)的现代转型的历史同步。从洪深、曹禺到李龙云的戏剧观念和创作,还有借用其戏剧题材的戏曲创作,都能够看到奥尼尔的戏剧思想的影响。但是,奥尼尔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的结果,并非中美文化“杂交”后的戏剧“混血儿”,更多的是一种“启示”——为中国现代戏剧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了一块可供熔铸的基石;而中国戏剧家们在判断、选择基础上的创造性成果,反过来也为“世界”现代戏剧艺术谱系增添无可替代的东方戏剧艺术精神。中国传统戏曲艺术随着19世纪末赴美华工一起登陆美国,作为一种社区文化活动,不仅具有缓解乡愁和族群认同的社会动员功能,还为美国借鉴戏曲手法的实验戏剧的形成,提供了部分重要的灵感。梅兰芳在1930年访美演出,更是中国戏剧的世界参与和现代转型的一次自觉实践。这次演出,从世界性的文化视野中反证了本土戏曲艺术的价值,成为中国戏曲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同时也给美国的先锋艺术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同样,美国的艺术家亦从中进行了判断和选择,并进行了价值置换,他们真正认同的是西方的古老戏剧传统。在观众的参与、选择、共享与创造中,美国剧作家征用中国题材与异国情调,致力于“中国性”的表述。美国戏剧的“中国”想象经历了一个从“阿新”到“阔阔真”,再到“蝴蝶君”这样一个多面、驳杂的过程。从总体上看,“中国”一直徘徊在低劣和美好的两极之间。虽然西方戏剧中的“中国”都在不同的尺度上强调其“真实”,但它们与现实的中国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是“美国臆想之中国”。在中美戏剧文化双向交流的历史中,两种戏剧文化无一例外地都履行了各自的文化主体的自身认同功能,双方都扮演了一个文化他者的角色。
上述具有反思性的“影响一接受”的文化交流模式,或者说是一种双向的“影响——反哺”模式,在理论背景上,具有明显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反写”色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