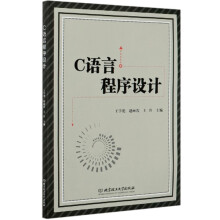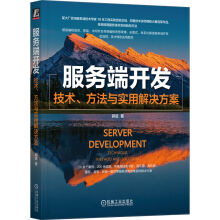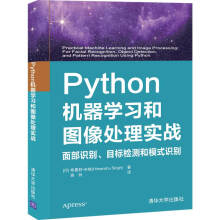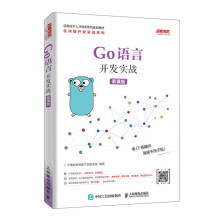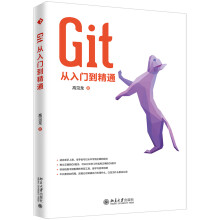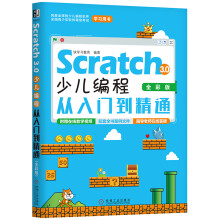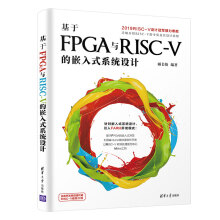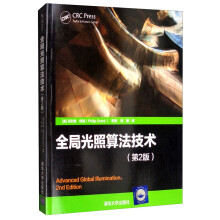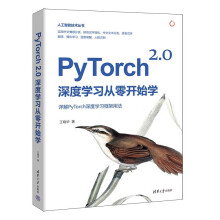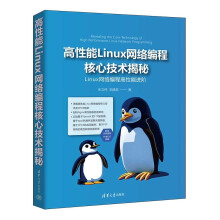迷失而不自知,结果便是自我的沉沦,但能够意识到迷失而主动寻找出路便是救赎。扎东点亮心灵之灯是从祭祀神箭的伐木活动开始的,然而寻找之路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晨曦中,当一棵棵白杨树在汗水和斧凿之间应声倒下的时候,当年轻人肩扛手抬搬运木材下山的时候,当木材变成一支支巨大的神箭在山顶矗立而起的时候,当松柏煨桑烟雾霭霭升起的时候,追寻信仰的动力在扎东心中不断聚集。
身为射箭世家传承人的扎东,还是一年一度祭祀活动中羌姆舞的舞者。主人公的这一身份设置颇具深意,一方面,在电影中如扎东的父亲所言,想要射箭射得好首先要把羌姆舞跳好,这羌姆舞是根据神秘岩画“拉龙巴多射杀朗达玛”的故事改编的,所有箭法的精要都在羌姆舞的舞步当中。但是祭祀庆典上跳羌姆舞的扎东却不以为然,舞步凌乱,心思全在台下的尼玛与德吉身上。另一方面,羌姆舞者是典型的藏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万玛才旦于2004年拍摄的纪录片《最后的防雹师》中的防雹师(民间可以阻止冰雹的巫师)也是藏文化中特有的职业。羌姆舞者、防雹师等的存在对于传承民族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羌姆舞者,扎东无疑也成为藏族文化的传承者。羌姆舞不仅需要舞者在形式上完成每一个舞步,更主要的是舞动者精神信念的秉持与彰显,显然此时的扎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追寻信仰的开始是意识到了自我的迷失,这也是自我救赎的开端。首先,扎东在祭祀当晚的宴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的射箭技艺不如尼玛,第二年的神箭比赛还是无法获胜,这种姿态表明扎东开始正视自己,并且他和伙伴们自此开始积极的“求索”之路。于是,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来年的神箭比赛中拉隆村的射手们都拿着先进的现代弓箭,对此他们的族人一无所知。扎东最终胜利了,但是胜之不武,比赛成绩作废,这样的努力并没有赢得族人的认可,这条求索之路失败了。值得思考的是,通常“现代化”的引入都具有正面的意义,而在影片中却没有被认可,这一点随着影片的推进将进一步展开。此处,导演想表达的大概是当下一种普遍的矛盾状态,“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没有能力保持自己,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能不能生存下去”(万玛才旦语)。传统射箭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运动,更重要的是藏民族传统的精神信仰。
主人公的追寻还在继续。对于此时的扎东而言,怎样才能既赢得比赛,又赢得族人的认可,他心里没有底。随着镜头的切换,扎东年幼的弟弟也在像模像样地练习射箭。弟弟是扎东的影子,从镜头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童年的扎东也是一路勤奋练习,直到今天遇到瓶颈,扎东的困惑也许是弟弟将来某一天也要面对的。扎东的困惑是射箭除了常年苦练的技艺之外还有什么?老父亲身体力行地给了他答案。父亲与扎东一起练习射箭,父亲虽然年迈,射出一箭就要耗费很大的气力,箭法却十分精准。为何?当扎东按父亲的指引再次来到描绘拉龙巴多射杀朗达玛传说的岩洞时,当酥油灯照亮岩壁也照亮扎东双眼时,当一幅幅岩画从扎东眼前细细掠过时,射箭人找到了答案……羌姆舞再次跳起,气氛庄严而雄浑,扎东的步伐坚定而沉稳。扎东终于找到了射箭的精髓,找到了心中的神箭,自我救赎也就此完成。
电影结尾,应县文化局之邀,两个年轻人站在了现代化的体育馆里比赛。他们手持传统弓箭,他俩每每射箭前都会轻念祈祷词,然后举臂弯弓,一气呵成,比赛最终以平局结束。此刻关于神箭的信念被两个年轻人传承并坚守。现代体育馆的场域中,传统的射箭运动包括仪式被保留下来,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没有胜负只有交流与融合。这种运动和运动的精神、民族的信仰将在变通中保有、坚守,并继续弘扬下去。
电影中扎东始终身着红色衣服,红色与扎东本人的形象一样,表现藏族文化性格中进取、奔放的一面。藏族作为草原民族,善骑射,能歌舞,具有不服输的坚韧精神。尼玛则始终一袭白衣,白色如同尼玛的性格,纯正、洁净,表现藏族文化性格中宁静、和谐的一面。整部影片中尼玛坚守信念,心中有爱,能够宽恕“对手”,这种包容性是藏族的底色。在万玛才旦看来,藏族文化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处处体现对人、对生命的关怀。他认为那是一种慈悲智慧、宁静和谐的博大文化。在现代文明背景下,扎东和尼玛从不同层面展现了民族性格和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
让我们共同祝愿五彩神箭在它的故乡代代传承。许多年后的某一天,当你走在神箭故乡的土地上,身边经过的也许就是新的扎东和尼玛。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