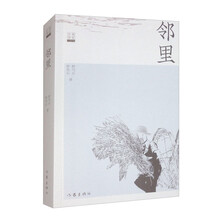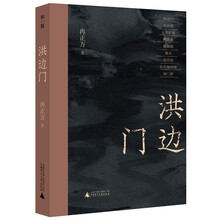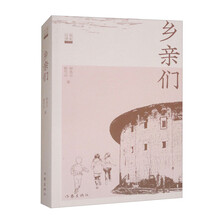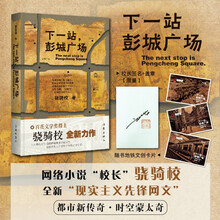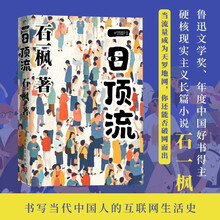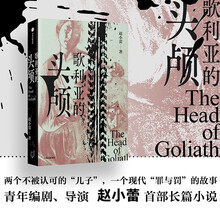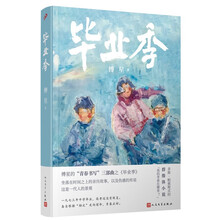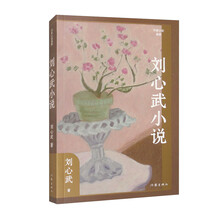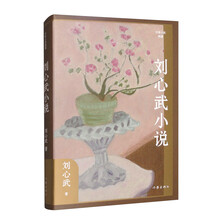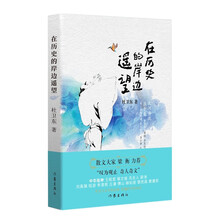第一章 故乡情思
绿水青山情自流,相山叠翠映高楼。
登高犹知儿时梦,幕幕皆源雁翅沟①。
我出身于农家,贫苦的农村生活和繁忙的农业劳作从少年时期就伴随着我。参加力所能及的劳作,特别是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三年锻炼,使我深谙了那时褐土地上依靠人力畜力的生产劳动。“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诗句道出了我的心声。我至今对故乡那片褐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以及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坑一洼常怀深沉的眷恋,对那时依靠人力畜力的生产劳作记忆犹新、难以忘却。
一、故乡溯
思忆故乡是一个远离家乡人的永远情愫,特别是退休颐养之后,眼前时常显现那里的亲邻故伴、坑圩溪塘、花草林木、牛马骡驴、猫狗猪羊、田园虫鸣、日出日落、寒暑往来……
我的故乡周大庄,距濉溪县县城100余里,坐落于韩村、五沟两个集镇之间。1980年归属五沟公社管辖,设区划乡时,划归五沟区小湖乡。2001年撤区建镇时,即入韩村镇。
乡思
读罢南窗放眼望,心头一念归家乡。
坑涯柳桐槐茂密,圩里杂院草坯房。
纵横菜畦正滴翠,丝瓜葫芦爬一墙。
葡萄串串果园挂,荷藕池池送清香。
队队马牛拴棚下,家家猪羊卧树旁。 祖传耕地两千亩,畜力人力犁耙耩。
出工出勤无逼迫,自觉自愿献力量。
一家有难众伸手,助人为乐成时尚。
僻壤穷乡民风淳,乡旮旯人品高尚。
经年面土背朝天,自给自足累日忙。
母亲溪流雁翅水,潺潺日夜东南淌。
虫鸣蛙唱蝶飞舞,风弄庄稼嘘嘘响。
从小就在那刨食,每土我脚都曾丈。
走出家乡四十年,虽有时归多匆忙。
那儿长存我记忆,一草一木总回想。
传说村里人祖上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落脚在这穷乡僻壤之处是为了逃避荒乱。由于闭塞,我小时候连汽车都很少见过。八九岁时村上来了辆勘探钻井的汽车,一群群孩子惊奇着、呼喊着、追着撵着看。村里很多人一辈子没坐过汽车,没见过火车。
全村都是周姓人家,祖祖辈辈大都是文盲,读过书的寥寥无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也只有少数人家的孩子上了学,能读完小学的也是微乎其微。全村世世代代没有乡绅名流、达官显宦,没有宗祠族谱、历史遗迹,也没有显耀的地标性建筑。只有“学”字开始的辈分:学全士德,丙鲁维宗,开家继业,忠孝友功。这些从远祖流传了下来。
难忘的家乡
我的家,在淮北乡下,
没有高坡,没有山崖,
一马平川的绿地,
土地生长着庄稼。 我的家,算得上穷乡僻壤,
没有高楼,没有大厦,
茅草土坯房里,
有我的婶子、大叔、大爷、大妈。
我的家,虽然多是水洼,
然冬能溜冰,夏可捉蛙,
水车那吱呀的声音,
伴奏着鹅鸭游戏鱼虾。
我的家,就在那旮旯,
没有大道,乡路夹巴,
悠远似羊肠啊!
老辈人习惯了肩挑、背扛、板车拖拉。
我的家,远离繁华,
星稀月明,白开水那都叫作茶。
习惯不?新媳妇进门叫爹是“大”,喊自己的男人
是“他”。哈哈!
老辈人照样把这种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好那个潇洒!
我的家,犁耕耙拉,
几十头牲口千亩地,一年收种两茬。
人不饱餐畜更苦,畜力羸弱曾人拉,
光膀黝黑套上绳,赤步烈炎下,回看新田乐哈哈。
我的家,改革带来大变化,
耕种有机械,腰包鼓起啦!
轿车开进院,家家盖楼厦,
就算进了城,也常来度节假。
P1-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