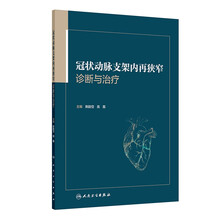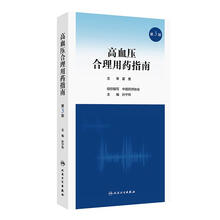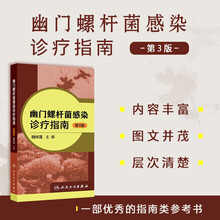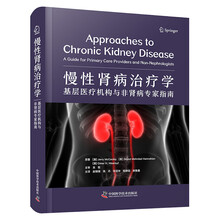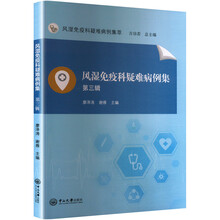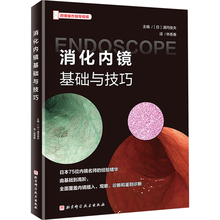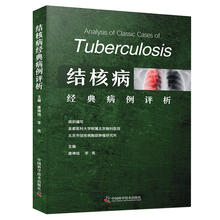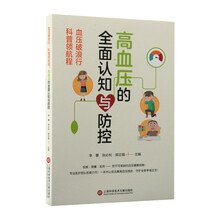总论
第一章血液系统疾病概述
第一节造血组织的结构及其生成调节
人类的骨髓、胸腺、淋巴结、肝、脾、胚胎及胎儿的造血组织,在生命的不同时期分别承担着造血任务,称造血组织。胎儿出生后,骨髓腔里的骨髓是造血发生的主要部位。当骨髓腔储备血力量不足,需要动用骨髓以外的器官(如肝、脾)参与造血时,称髓外造血。血液系统疾病的发生,不仅与造血细胞相关,还受位于骨髓中的非造血细胞及其分泌产物提供的细胞和分子影响,并可能有肝、脾等髓外器官的参与。本节就造血组织的结构及其生成、调节机制进行详细阐述。
一、造血细胞与造血发生
造血干细胞(HSC)起源于骨髓,是血液细胞与免疫细胞的共同起源,其在生物体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受到细胞自主程序和环境因素的严格控制。在发育过程中,HSC首先出现于主动脉-性腺-中肾区(AGM),并迁移到胎盘、胎儿肝和脾等不同的造血器官,不断自我更新和扩张,达到稳态。胎儿出生后,大多数HSC在骨髓中,并休眠以维持终身造血功能,少量HSC在血液或脾等外周组织中可以被发现。
骨髓是HSC的主要发生和存在部位。骨髓分为红骨髓和黄骨髓,红骨髓具有活跃的造血功能。胎儿出生之后,红骨髓仅集中在颅骨、脊椎骨、肩骨、骨盆带、肋骨和胸骨,其余部位的红骨髓则逐渐退缩而被富含脂肪细胞的黄骨髓取代。HSC是终身造血的核心,它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自我更新的能力,即每个HSC都可以分裂成两个HSC;二是分化为所有成熟血细胞的能力,称为多能。HSC的活性限制在HSC谱系的Lin./lowScal+c-kit+(也称为LSK)部分,由功能异质的多能长期造血干细胞(LT-HSC)和其产生的短期造血干细胞(ST-HSC)组成,LT-HSC具有长期重建潜能,可进一步分化为多能ST-HSC,随后分化产生共同淋巴样祖细胞(CLP),能够产生完整的淋巴系细胞(包括自然杀伤细胞、B淋巴细胞和T淋巴细胞),或共同髓样祖细胞(CMP),后者能够向髓系分化,定向为巨核细胞-红细胞祖细胞(MEP)和粒细胞-巨噬细胞祖细胞(GMP),并进一步在骨髓(BM)中形成所有成熟的髓系细胞。
二、骨髓微环境与造血调节
(一)骨髓微环境的组成和功能
骨髓造血龛概念的提出者认为,造血龛为骨髓微环境内的特殊结构,该结构不仅为HSC提供居住场所,还提供必要的自分泌、内分泌和旁分泌信号,以及细胞与细胞直接的相互作用,以维持HSC自我更新和向所有谱系血细胞的分化。此后,对造血龛的认识逐渐丰富。骨髓微环境不是一个造血龛,而是几个“微龛”的集合,它们由不同的细胞群同时产生,并诱导HSC产生归巢、动员、静止、自我更新或谱分化等不同的反应。截至目前,研究证实的造血龛组成具体功能如下。
1.骨内膜龛
在稳态条件下,HSC靠近骨内膜表面生长。对小鼠的研究表明,在移植时,HSC优先迁移到骨内膜区域,与骨内衬细胞密切相关。此外,从该区域分离的HSC具有更高的增殖潜力和更好的长期造血重建潜力,而分化的造血祖细胞主要存在于血管周围的中央骨髓区。
2.成骨细胞
成骨细胞谱系的细胞对HSC的作用包括:①促进HSC的自我更新和扩增,但可能对HSC的扩展能力有限。骨形态发生蛋白(BMP)ⅠA型受体的条件缺失或成骨细胞特异性激活甲状旁腺激素(PTH)导致成骨细胞数量增加,与HSC数量增加有关。②成骨细胞数量减少促进髓系扩增,但抑制淋巴细胞和红系扩增。这种转变类似于造血衰老的特征,可能是骨髓中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更容易植入和形成的先决条件。③调节HSC归巢,紧密黏附在骨膜表面的HSC表现出较高的增殖和长期植入潜力。
成骨细胞对HSC的作用机制可能为成骨细胞分泌调节HSC归巢、动员、静止的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如CXC-趋化因子配体12(CXCL12)、干细胞因子(SCF)、骨桥蛋白(OPN)、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AnnexinA2(ANXA2)、血管生成素1(ANG1)或血小板生成素(TPO)。CXCL12[或称基质衍生因子1(SDF-1)]主要由未成熟的成骨细胞产生,但也由内皮细胞产生,并控制HSC的归巢、保留和再增殖。OPN是一种糖蛋白基质成分,在骨膜内表面HSC的增殖和分化、迁移和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G-CSF是支持骨髓生成所必需的,主要由成骨细胞释放。成骨细胞和内皮细胞均高表达的ANXA2调节HSC的归巢和植入。成骨细胞表达的ANG1与其受体Tie-2相互作用,促进HSC的静止和黏附。成骨细胞TPO的表达参与LT-HSC静止的调节。成骨细胞中PTH信号通路活化后Jagged-1表达增强,随后的Notch-1在HSC中活化,这一改变在增加成骨细胞数量的同时,促进HSC的自我更新和再增殖。
细胞内的典型Notch信号对体内HSC的维持并不重要,HSC中Notch信号的激活是由骨髓造血龛中的细胞诱导的。事实上,内皮细胞中的典型Notch信号缺陷改变了造血稳态,导致骨髓增殖性疾病的发生。根据其与HSC的靠近程度,骨内膜龛间充质干细胞(MSC)表现出不同的分子特征:*靠近骨内膜龛的MSC表达了三个先前与HSC生物学无关的分子[RNase血管生成素、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8和黏附分子栓塞素],这些分子参与HSC的静息调节。
3.骨细胞
骨细胞占成熟骨细胞的90%,骨细胞嵌在骨基质中,并延伸以长投影形状与周围的骨细胞及骨内成骨细胞连接。鉴于其解剖位置,骨细胞对HSC池的影响可能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骨内成骨细胞达到的。骨细胞通过对G-CSF的分泌和响应参与了HSC的控制。骨细胞中Gs-α信号的中断导致骨丢失和髓系扩增,部分与骨细胞释放G-CSF相关。骨细胞的消融不会影响HSC的数量,但会损害HSC被G-CSF动员的能力。骨细胞特异性激活PTH受体1(PTHR1),尽管扩大了成骨细胞池,但不足以增加HSC的数量或增强其功能。此外,骨细胞中β连锁蛋白(β-catenin)的激活增强了Notch信号通路的成分,但不改变造血或其存活。
4.血管周围龛
血管周围龛是骨髓进行气体交换、输送营养和清除废物必不可少的结构。HSC与血管周围和内皮的基质细胞共存于促进其生长和扩张的环境中。休眠(静止)的HSC位于小动脉附近,尤其是骨膜表面,而不是血窦附近,这表明在骨髓中静止和增殖的HSC各有其单独的血管周围龛。
5.内皮细胞
内皮细胞排列在血管内层,血管将氧气和营养物质输送到细胞,并形成了血管周围龛。造血干细胞、造血祖细胞,定位于血管内皮表面的内皮结构附近。对骨髓造血龛的体内成像显示,HSC位于位置上紧密靠近的内皮细胞和骨内成骨细胞之间的区域,这表明这两种细胞类型可能是特定造血龛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皮细胞通过细胞间的直接接触及分泌血管分泌因子调控HSC。尽管内皮细胞中SCF的特异性缺失不会导致HSC功能的丧失,表明内皮细胞可能不直接支持HSC。但内皮细胞分泌的CXCL1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A,VEGF-A)、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FGF2)、ANG1、血小板反应素-1(thrombospondin1,TSP1)和Notch配体,已经被证实具有维持干细胞池和调节HSC的自我更新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小动脉还是血窦细胞都与其附近的MSC共同作用,一起支持HSC。
6.表达瘦素受体的血管周围细胞
脂肪细胞特异性激素瘦素的受体是MSC的一个成熟标志。事实上,成年小鼠骨髓中94%的成纤维细胞集落形成单位(CFU-Fs)是瘦素受体阳性(LepR+)细胞。无论是LepR+基质细胞还是含CXCL12丰富的网状(CAR)细胞都主要在血窦周围重叠排列,对于HSC的维持至关重要。维持HSC的重要生长因子(包括CXCL12和SCF)也主要由这些细胞分泌。这些基质细胞负责将成人骨髓中的MSC转化为脂肪(脂肪细胞)、骨(成骨细胞)和软骨(软骨细胞)。
7.表达神经上皮干细胞蛋白的间充质干细胞
神经上皮干细胞蛋白(巢蛋白)阳性(Nestin+)为MSC的另一个标志,MSC含有所有的骨髓成纤维细胞集落形成单位活性。此外,这些Nestin+细胞与HSC共定位于血管周围区域,Nestin+耗竭导致HSC动员。Nestin+产生参与HSC维持的可溶性因子,如CXCL12和SCF,于是有研究者猜想MSC直接与HSC形成造血龛并维持HSC的活性。小动脉的低渗透性被认为提供了一个“代谢不活跃”的微环境,有利于HSC的静止。
8.CXCL12丰富的CAR细胞
CAR细胞是高表达CXCL12的一类MSC,CXCL12在促进HSC增殖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数表达CXCL12的细胞为LepR+,与内皮细胞密切相关,使LepR+细胞和内皮细胞CXCL12表达缺失,可以去除成人骨髓中所有静止和连续移植的HSC。
9.交感神经系统(SNS)和胶质细胞
SNS是HSC骨髓造血龛的调节因子。由交感神经产生的儿茶酚胺通过血液循环或以旁分泌方式从神经末梢分泌传递到骨髓生境。SNS通过直接作用于HSC或通过微环境间接影响HSC从骨髓向外周血流的迁移。抑制CXCL12可促进HSC迁移,骨髓中的成骨细胞可以通过SNS调节及抑制CXCL12的产生,影响HSC释放。骨髓中的胶质细胞与HSC密切相关,清除胶质细胞导致休眠的HSC缺失,*终导致HSC数量减少。
(二)炎症因子对造血的调节
1.炎症因子的来源
维持HSC所必需的炎症因子包括CXCL12、SCF、血管生成素、血小板生成素、FGF和IL-6等。其中许多细胞因子并非完全由单一的龛细胞产生,而是由多种龛细胞共同产生。在这些龛细胞中,*突出的是骨髓血管周围区域的基质细胞群体,包括CAR细胞、LepR+细胞、神经胶质抗原2(NG2)阳性细胞和Nestin+细胞。这些细胞及表达CXCL12的内皮细胞是骨髓中SCF的主要来源。
Nestin+细胞为间充质干细胞,该细胞进一步被细分为Nestinhigh细胞和Nestinlow细胞。成人HSC的功能与Nestinhigh细胞密切相关,其静止受NG2+的小动脉血管周围基质细胞调节,去除Nestinhigh细胞耗竭导致HSC进入循环并远离动脉。小动脉NG2+细胞中CXCL12选择性缺失导致HSC减少并改变其在骨髓中的定位,而LepR+细胞中的SCF缺失同样导致HSC减少。事实上,绝大多数LepR+群体也表达了高水平的SCF和CXCL12,这表明CAR、LepR+和Nestin+细胞,这三个血管周围群体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然而,这三种血管周围细胞分泌不同的炎症因子,以维持不同的血管壁龛中HSC的功能。
2.炎症因子的作用
当机体处于感染、自身免疫和组织损伤等状态时,成熟的免疫细胞不仅具有防御功能,还通过分泌炎症因子刺激免疫的激活。长期以来,骨髓一直被认为是免疫特权器官,免疫反应很少,因此骨髓内的HSC被认为不受免疫刺激的影响。然而,*近的研究表明,成人HSC实际上不仅能够对炎症信号做出反应,而且能够分泌促炎因子/趋化因子,包括干扰素(IFN)-α、肿瘤坏死因子(TNF)、肿瘤生长因子(TGF)、IL-1、IL-6和模式识别受体(PRR)。
IFN-α是一种调节细胞生长和分化的Ⅰ型干扰素,其抗病毒作用已被证明能调节龛细胞和HSC功能。IFN-γ是免疫细胞在病毒或细菌感染时产生的抗病毒细胞因子,在感染期间和正常造血过程中,IFN-γ通过其稳态表达直接促进HSC增殖。TNF-α在小鼠卵黄囊和胎儿肝中表达丰富,暗示其在胚胎造血中具有潜在作用。TGF-β被称为血液发育的负调节因子,其激活会损害小鼠胚胎中的内皮细胞向造血干细胞的转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