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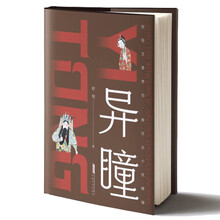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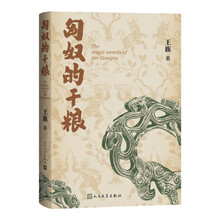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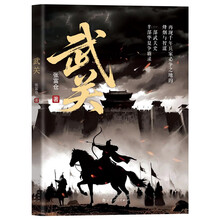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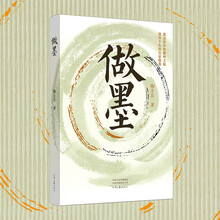
• 《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道尽战争阴影中被迫流离失所者的恐惧与悲愁。
• 逃亡中的人必须依靠偶然事件活下去,偶然事件越不可信,就越使人觉得正常。罗斯在去世当天把他的护照送给了我,我暂时有了新名字,有了未来,成为不幸的逃亡者中“最幸运”的那一小撮人。但过往的记忆却始终如幽灵般紧紧追随,等待时机将我击毙。我知道,我需要为这野蛮的、鹰隼般的、让人上气不接下气的自由付出代价。
• 经典译本,全新呈现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鲍勃·迪伦推崇的大师,茨威格、林语堂、木心盛赞的名家
这一夜我睡得非常糟糕,清晨我离开旅馆—在西尔弗斯处上班很早。我在第五大道乘上公共汽车,直到通往83街的交叉路口的车站才下车,以便到大都会博物馆去。博物馆还没有开门。我穿过博物馆后面的中央公园到了莎士比亚纪念碑,我继续沿着湖滨往前走,来到席勒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同样显得陌生。它也许是几十年前一位海外德侨捐款建造的。眼下,一个色情狂已经把它美化了,碑上用红颜色画了一个丰满的弯着腰的女人,她遭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从后面强暴。这幅素描画并非拙劣之作,但是它与《奥尔良的姑娘》的作者是极不相配的。我继续往前逛,一个蓄着大胡子、仪表威严的人来跟我攀谈。我起初猜想他是个画家,可是,当他问我是否吃过早饭时,我才发觉碰上了一个感情丰富的同性恋,于是摆脱了他。这时,博物馆已经开放。
博物馆我已去过几次。它使我回忆起我在布鲁塞尔博物馆度过的时光,而最奇怪的是令我想起了馆中的寂静。那最初几个月令人难熬的无聊、使人厌倦的紧张、担心被发现的持续的恐惧,已逐渐转变成为听天由命的习惯,所有这一切,随后似乎都沉降到地平线下,留下来的只是可怕的寂静,摆脱各种关系的生活,尽管周围风暴旋转呼啸,但是在风平浪静、船帆不飘动的龙卷风的寂静中心,这种生活,似乎总是安全的。
这一次去那里我害怕会唤起我心中更多的回忆,但是事实上,仿佛纽约的这个博物馆把我藏到了同样使人受到保护的寂静中。当我迟疑不决地走过这些大房间时,一点动静也没有。墙壁上激动人心的战斗场景、带有一些特别的形而上学色彩的事物所显出的宁静、隐藏“在一切事物之后”的宁静—这过去的非同寻常的宁静,正因为它已经过去,所以才显得宁静,预言家谈到它这么说,上帝并非在风暴中,而是在宁静中—这显而易见的宁静把一切固定在一个地方,它让战争在平面上存在,不让它在空间中进行,它似乎也在保护我。在这些陈列室里,我突然萌生了生命无限而纯洁的感觉,印度人称这种感觉为“萨马迪”。当它一度像陡峭的喷泉涌到双眼之间并在一只眼的上方消失时,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它,它是否还留存,那是无所谓的。留下来的,就是对世界迷人的幻想。这迷人的幻想就是:生命是永恒的,如果成功地蜕去自我这层皮并知道死亡不过是转化,那么我们就永远活着。我是在观看描绘托莱多的风景画时产生这一幻想的,格列柯那幅阴暗而又庄严的画,紧挨着挂在宗教审判所大审讯官(秘密警察和世界上所有施刑者极好的原型)那大得多的肖像旁。我不知道,这是否有关联,我在这瞬间感觉到,虚无和万物有关联,这一关联无非是人类的破烂货,一半是谎言、另一半是不可理解的真理。但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真理和一个不可理解的谎言有什么区别呢?
我去博物馆,并非偶然。莫勒的死给我带来的不安比我所预料的要大。开始时它并未使我非常震惊,因为我在逃亡途中、在法国,常常经历类似的情况。例如哈斯特内克尔,他因法国不负责的官僚主义而莫名其妙地一直被关在拘留营里,得不到帮助,当德国人离拘留营只有数小时路程时,他宁可选择自杀,而不愿落入他们沾满鲜血的手中—但这是在极其危险的处境中的惊慌失措,是可以理解的。这次的情况则不同。这里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不想继续活下去,而他并非随便哪个人,他和我们大家都有关。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偶然事件来摆脱,但是它又悄悄地紧随着我,不让我安宁。这就是我现在在这儿从这幅画看到那幅画,一直来到有格列柯那幅画的大厅的原因。
托莱多的风景今天给人以阴暗和无光泽的印象。这也许和光线的照射有关,但同样和我抑郁的心情有关。以前我什么也没有在意,今天我来了,为的是自己可以从风景画中得到些慰藉—而这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骗人把戏。艺术作品不是护士。谁寻找安慰,就应该祈祷。这也是自我暗示。风景画不会说话。它既不会谈永恒的生命,也不会谈尘世的生活,它美丽、安静,而恰好现在,正当我在它那里寻找生命,以便逃避死亡念头的纠缠时,它却随着幽灵般的光线显示出一些骷髅的特征,仿佛它就在冥河的彼岸。但与此相反,宗教审判所大审讯官的巨幅画像却从未有过地闪闪发亮,无论是其冷漠的红袍,还是一双眼睛,都是如此。那目光始终跟随着人,你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仿佛在几个世纪之后,画像突然又获得了生命。它显得非常强大,在展室里起了主导作用。它没有死亡。它可能永远不会死去。刑讯是永恒的。恐惧仍然存在。没有人得救。我突然明白,谁杀死了莫勒。我对自己在这儿的最初经历并不绝望。它仍然留着。但是另一段经历也留着,若是人们相信已经得救,它的影响仍然会致命的。
我继续往前走,一直来到摆放中国青铜器的几个展室。我喜欢一只蛋青色的青铜碗,它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而我首先就寻找它。它不像绿色的、有尖角的周朝青铜器一样抛光过,后者属于放在展室中间的一个壮丽祭坛的一部分,祭坛的青铜器像玉一样闪闪发亮,青铜器上有岁月留下的丝绸般的微光。我真想把它们捧在手里几分钟,但是所有展品都放在玻璃柜中,这样做是从保护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手上看不见的汗很容易给这些价值连城的展品造成损害。我站了一会儿,想象着自己抚摩着它们。真奇怪,这么做也使我平静下来。泛着光的高大又明亮的展室中,竟也有第二大道和第三大道上古董商店里那魔术般吸引着我的东西。时间停止了,为了使自己活着,我不得不浪费如此多的时间啊!
这家殡仪馆虽然便宜,但完全是用虚假的激情布置起来的,这就产生出一种效果,几块薄木板或是一辆灵车使人觉得葬礼更加隆重。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肃穆—办丧事的慎重,严肃的表情,哀伤的面容,入口处的黄杨木盆,风琴,后来我才知道那风琴声不过是留声机。贝蒂满脸通红,汗水直淌,连衣裙上黑色褶子非常多,她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这时我几乎像是得到了拯救似的。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公正。但是,在死亡这件事上,要避免激情,避免并非自己躺在那可怕的、抛光的木箱中这一受抑制的潜在满足感,是很不容易的。人们憎恨可又逃脱不了的这种感觉,这容易使一切变样,走向极端和不真实。此外,我当时神经过敏。
当我缓慢地走近14街时,对于火葬场痛苦的回忆越来越使我激动。这期间我得知,殡仪馆当然没有自己的火葬场—只有德国的集中营才会有。但是这回忆像只大黄蜂一样叮在我的脑袋上,赶也赶不走。被动进行回忆对我来说已经够难的了。我已经有了打算,若是在追悼会之后,我们必须像以往在欧洲时一样一道乘车去参加火化仪式,那我将拒绝前去。不仅仅拒绝,我干脆就悄悄溜走。利普许茨讲话,我没留心听。我被闷热的天气和棺材上鲜花的浓郁气味搞得昏昏沉沉。我看着弗里斯伦德尔和拉宾诺维奇。来的人有二三十个。有一半人我不认识,有几个是作家和演员。科勒尔姐妹俩也来了,她们的头发闪闪发亮,坐在弗里斯伦德尔和他的太太旁边。卡恩独自坐在那里,他没跟卡门一起坐,她隔着两条长凳坐在他前面。我的印象是,她在利普许茨讲话时睡着了。整个追悼会也出现了每个追悼会都经常出现的不和谐。一些永远想象不到的事情悄悄地渗透进来,人们试图用祷告、风琴声和讲话把它们变成一些可以想象的事情,当然人们是以小市民的立场和慈悲为怀对这些想象不到的事情加以掩饰的。
突然,四个戴黑色手套的男子站在棺材旁边,用举枪一样的动作迅速而又轻松地把棺材抬起,并相当快地齐步从橡皮垫上走出去,他们动作的熟练程度令人想起了死刑执行官的助手。在不知不觉间,这一幕已经过去。当他们紧靠我身旁走过时,我突然觉得我的胃也被抬起似的,随后我惊奇地感到我的两眼已经湿润了。
我们走了出去。我环顾四周,棺材已经不见了。在出口处我发现自己站在弗里斯伦德尔身旁。我考虑是否要对借钱一事表示感谢。
“您来。”他说,“我的车子就在那里。”
“到哪里去?”我惊恐地问道。
“到贝蒂那里。她已经准备好一些吃的和喝的。”
“我没那么多的时间。”
“现在正是中午。您无须待很长时间。目的只是让她看看某某人来了。这样她觉得亲切。每一次都这样。您知道她是怎样的人。您来。”
拉宾诺维奇、科勒尔姐妹、卡恩和卡门一道搭车走。“这是阻止她再次见莫勒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拉宾诺维奇解释道,“我们说过,所有的人在追悼会后将到她那里。这是迈尔的主意。它起作用了。这位数十年来善良的女房东胜利了。她早晨六点钟就起床烧烧煮煮。我们对她说过,在这样的大热天,最好弄几样餐前小吃和一个冷盘。要准备这些东西,需要较长时间,因为它们必定还会变冷。她一直忙到一个小时前。谢天谢地!这样炎热的天气,莫勒现在看上去想必会怎样啊!”
贝蒂朝我们走来。科勒尔姐妹俩立即和她一道进厨房帮忙。桌子上已经摆上了瓷器。这种可怕的操心令人感动,同时又令人沮丧。“这玩意儿在比较原始的民族那里称之为丧礼后的筵席。”拉宾诺维奇解释道,“此外是个古老的习俗……”他着迷地、不厌其烦地探讨在古代这个习俗的起源。
当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阐述并寻找机会逃脱时,我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德国人啊!科勒尔姐妹端来盛满沙丁鱼、鸡肝、金枪鱼和蛋黄酱的盘子。她们在分碟子。我看到,偶尔在贝蒂那里出现的迈尔已偷偷地在姐妹俩中最诱人的那个的屁股上捏了一下。生活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此事是可憎的,却是了不起的,那就看如何认识了。认为这了不起要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