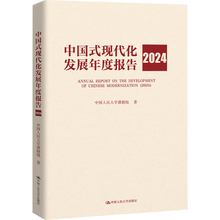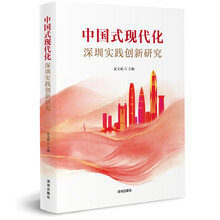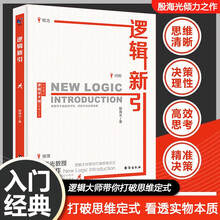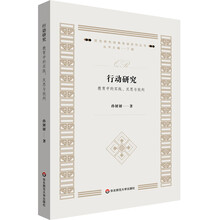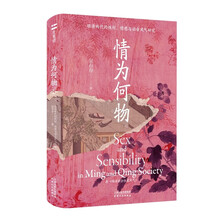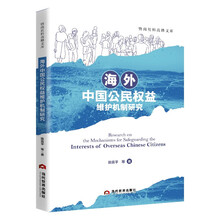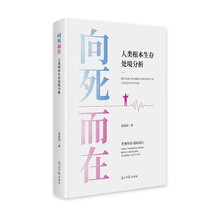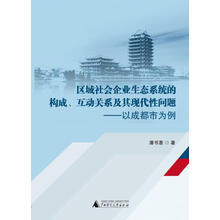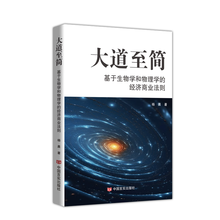《杜威的科学人文主义思想研究》:
总之,半世纪以来的科学哲学家们大都追随着二元划分的传统,把科学和价值放在二元对立的地位。要么是单纯的强调“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不可沟通”等,要么是通过逻辑分析把价值判断隔离在事实判断的范畴之外。这种持“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认为,科学最多也就是具有一种工具价值,但它的认知过程本身不仅是客观的,不涉及任何价值评判的,而且科学也不会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目标是值得追求的这样的终极价值问题。至于科学在社会中的应用所产生的后果,也没有紧密地与科学联系起来。杜威批判了这种逃避科学价值的观点,他指出,事实与价值两分的教条主义往往都忽略了人类实践的历史,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科学是在人类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科学本身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因素,科学价值并不是中立的,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科学事实的进步,其实都跟人们的价值判断有关系,或多或少地受到价值判断的指导,不可能完全脱离价值判断的影响。科学活动并不是纯粹对科学事实的追求,其中也蕴含着人类的价值追求等因素。科学有助于人类评价和辨明人生的终极价值问题。科学正在通过它的巨大技术效用对人类的物质欲望和信仰产生深刻影响,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此时仍然否认科学与人类价值判断之间的无关联性,只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想法。杜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一、两分的教条,忽略了科学探求过程的人性要素和文化要素
杜威指出,“人类有机体生活在一个文化环境中……任何一种欲望和兴趣,它们之所以有别于原始的冲动和纯粹的有机体的嗜好,都是因为它们在后来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了改造。”①可以看出,杜威强调人类的文化背景对人类兴趣活动的导向作用。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兴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科学无论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还是科学知识本身的性质和研究主体来看,都深受人类文化价值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科学知识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建构的产物,不可避免的渗透着人类的“利益”“文化”“实践”等社会和文化因素,科学家并非中立地“发现”了科学知识,而且在各种复杂的背景中“建构”了科学知识。无论是纯粹科学,还是应用科学,由于它们的研究者都是人,因而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价值的影响。科学的发展已经打破了传统的仅依靠个人探索的“小科学”范畴,逐渐转向群体协作的“大科学”合作范畴,这本身就意味着科学活动不再是受一个单一领域价值取向的引导,而是要接受一个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领域,这就使得科学研究本身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作为科学研究主体的科学家,其本身也生活在社会共同体这个大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环境所产生的“舆论气候”的影响,这种影响对科学研究者的心理或兴趣及科研发展的方向都产生作用。
其次,科学也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科学研究本身也是具有目的性的,不可能毫无目的的去从事一项研究,而目的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因此,科学实践中和活动中不可能脱离价值的评判。科学研究不可能脱离人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客观存在,科学家们在选择科学理论时,充满了价值的考虑,这些考虑最终跟伦理学关于好或坏的判断分不开的。科学理论中的术语选择也体现了简单性、融通性等价值特点,这些特点渗透在人类的全部经验中,因此价值判断对科学实践本身来说是必须的。杜威从人类实践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角度出发,否认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分离与对立,倡导“建立一种文化环境,这一种文化环境将为融情感与观念、欲望与鉴定于一身的行为提供支持”。①
杜威把科学放在人类的实践经验领域去研究,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对科学实践本身的作用。科学领域的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离不开人类的特殊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及特殊的问题情境,外在于人类的各种文化因素和问题情境的科学研究,最终只会导向一个超验的科学价值领域。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立足于人类实践的背景,进行“可错地探究、讨论和试验”。②总之,在杜威眼中,科学本身就蕴含着价值,科学价值是一个多维的体系,既包括科学方法、科学目的,也包括科学家个人的兴趣、心理状态、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这些因素在人类的文化背景下结合在一起,让科学价值具有充分的人文因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