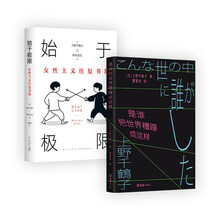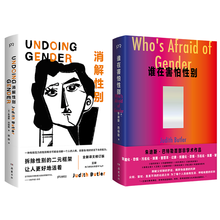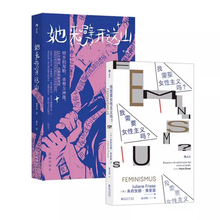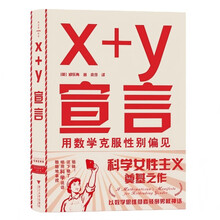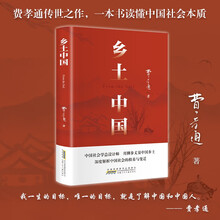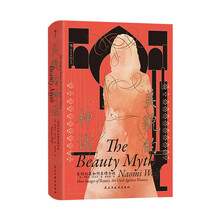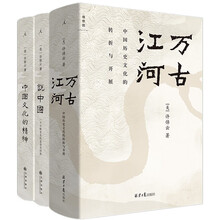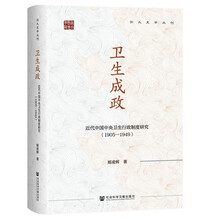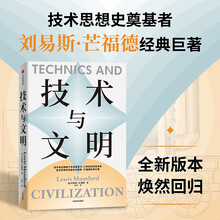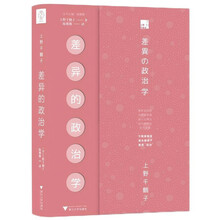比如一个领导者采取弹性坐班制需要假定其企业员工具有成就动机,如果该制度实施的效果不明显,则说明该领导假定上有偏差。一个更为通俗的例子是,一个母亲每天晚上坐在她孩子边上监督他做功课,是建立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缺少学习自觉性之假定,如果她假定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学习自觉性,那么她就会放弃监督。另一个尤为显著的例子是高等院校对于老师的科研要求是采取算工分的激励甚至动不动就处罚、警告,还是只提供研究的机会、经费、环境,而不去过问其每年的生产量是多少,也在于高校领导对知识人的人性假定是什么。采用前者的管理者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科研是没有积极性的(即假定了人之惰性);而采用后者的管理者认为,不断催促科研成果并给予一定的奖惩,人的创造力会衰减,只能疲于应付任务,所以需要给出更加宽松的制度来激发人的潜能(即假定了人有自我实现的愿望)。结果,如果高校坚持以前者安排制度,那么最懒的人被管住了,但最好的学者消失了;如果坚持以后者安排制度,那么最好的科研成果出现了,但懒惰的人也许增多了。至此,如何对科研教学人员进行管理,我们至今也没有认真反思过,但眼下为了高校排名,现行制度的设立导向了每年考核,而要花几年或更长时间从事的研究也在此考核下自然消失。正因为管理者对知识分子的人性假定很随意,所以很多高校发文量上去了,却失去了创新机制。总之,我倾向于认为,很多制度问题被停留在事实层面上来寻求解决方案,是社会或组织得不到治理和改进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许多社会措施达不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比如市场化的社会倾向认为,任何事情有钱就好办,结果是搞创新就是投资;而一种相反的观点是,再多的钱也买不来创造力,发明来自智慧与钻研,否则给再多的钱也出不了发明家。
为了比较完整地讨论信任所牵涉的人性问题,我还是先回到本书前面已经提及的人类生活需要分工协作和彼此依赖开始。我们先做这样一个设想:假如某个体是“全知全能”的,他的生活是否需要信任呢?答案是“不需要”,因为该个体自己拥有得到一切信息并完成一切任务之能力。反之,假如某个体是“无知无能”的,比如婴幼儿或病人、残疾人等,他是否需要信任呢?答案是“绝对需要”,因为片刻间的无人相助,都将导致他无法生存。比较这两个极端,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或者一个婴儿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从绝对需要到尽可能不需要的过程。这是文化习得与技术创新的动力所在。进而在任何社会,提升知识和技能一直是文化对每一个成员的基本要求。当然,目前人类在自我知识和技能的增进方面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即便如此,只要人类还不能做到全知全能,包括我们期待让机器人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复杂问题,且在人机互动(只要机器不出故障或不是伪劣产品,机器不存在动机上的欺骗问题)出现之前,就会不断反复地有对英雄、神话或上帝的敬仰或崇拜,因为正是他们的无私帮助才一再地拯救了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神话或者宗教信仰,也广泛流传着有关巫师的民间故事。信仰和信任可以相连,即是表明在个人或社会感到无助的时候,有神可以帮助信仰者,此即人世间的信任难题最终上升为宗教信仰。其主要内容大都在于神灵会保佑人们,答应满足人的各种愿望。当然,也有一些民间故事告诫人类不能太贪婪,无休止的贪婪会导致他们的愿望要么最终被剥夺,要么为自己埋下祸根,最终回归到以往无助的生活状态中去。其教化意义是,人要知足,要守信用并且对神要虔诚。
英雄、神仙、上帝及巫师等之伟大使得他们同人类有了差距。这个差距令人类自己面对种种无助选择过集体生活,以抵御自然或异族之侵袭以及内部的冲突。从生物学到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群体成员之所以能够彼此依靠,首先是通过信息的交流与货物的共享实现的(动物学家观察到鸟类有序地排列成一定方阵飞翔或者蚂蚁可以职责分明地分工协作,主要是由信息传递引起的,这对机器人的开发有新的思路)。在社会学中,人类所构成的协作关系可以统称为“社会交换”。依照社会资源理论,人们互相交换的内容虽然很丰富,但大体不超过货物、信息、金钱、服务、地位和情感等六大种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