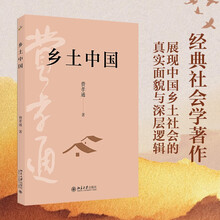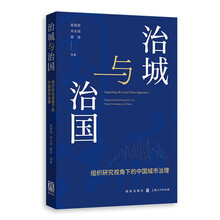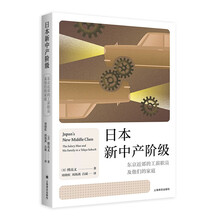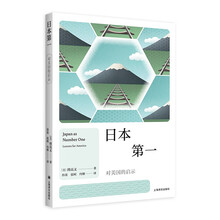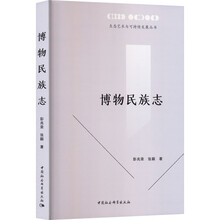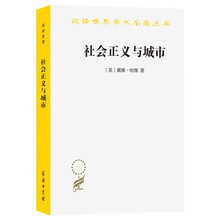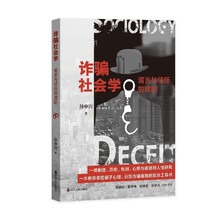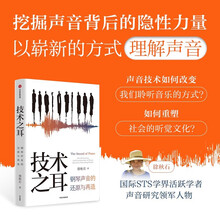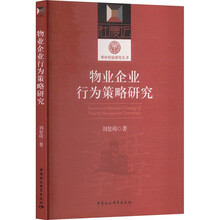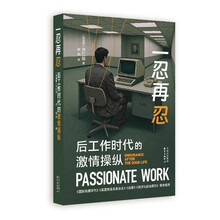《“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三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深层挑战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也承受着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以及市场化、信息化、全球一体化的多重挑战,社会治理任务完成和目标实现的艰巨性也愈发凸显,这也给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一些深层挑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缺乏衔接性的保障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就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基层公共事务的一套结构性制度安排,包括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机制体系等。其中,从治理主体结构或组织体系来看,政府和社会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组织力量。但这两种力量的权力来源并不相同,政府权力来自于科层体系的强制权威,而社会权力则来自于社会契约与协商认同过程。①在治理实践中,政府与社会力量互为补充、相互协同,共同塑造基层社会秩序和激发基层社会活力,并力图维持二者的动态平衡。以前文提到的社会发展目标(社会团结机制、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组织体制和多元治理结构)为例,这些目标的实现无不需要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合作治理。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要探索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模式。
然而,要在基层治理领域形成上述新型政社关系模式并非易事。立足于中观层次的分析,我们发现:政府治理所强调的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与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所借助的横向秩序协调机制各自暗含着一些相关矛盾的诉求,并在各自运作的领域中自发地排斥另一套机制的涉入。②就社会治理而言,政府治理强调的是治理主体上的政府行政权力单一性或主导性,权力运行上的自上而下强制性或单向性,组织体系上的科层结构等级化。而社会协同则体现的是治理主体上的多元中心共治性,权力运行上的政府与社会平等协商性,治理方式上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多样化。可见,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与横向秩序协调机制暗含着相互排斥的理论逻辑,试图将这两种具有内生排斥力的治理机制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都会面临巨大挑战。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两套治理机制也常常相互排斥,因此,这些国家往往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确定政府行为的边界,以保证社会系统的自主性得以申发。从这个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实际上就是要从深层次上推动国家权力(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自治权力)之间的有效衔接、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政府行政权力无限扩张的本质属性,加之权力制衡理念与制度建设赢弱,必然会对社会调节系统与自治权力的生存空间产生强大的制度挤压,致使二者的良性互动在现实中流于形式。因此,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系统的相互衔接也就常会遇到深层次瓶颈,以致出现“行政吸纳社会”的现象。比如:我们常常会发现社区自治平台在行政干预下陷入“空转”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为近年来各地开展的社区治理实践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创新经验。
(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性建设缺乏有效的支持机制
推动公共性是促进社会公共领域有序发展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从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来看,公共性生产的过程就是个体基于理性精神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序有效,需要各治理主体高度关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
任何社会发展时期,如果没有持续生长的公共性作为基础,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将面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以及协同共治也无从谈及。但是,公共性的生产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涉及规范有序的公共领域、公平开放的参与制度以及理性有效的参与机制等多个维度。就此而言,“公共性”生产并不等同于中国传统语境下“公”的重塑,而着重于参与机制和公众有序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从操作性角度来看,公共性生产的过程离不开两个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一是政府对社会领域的有序赋权。因为公共性的生长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改革,没有这种赋权即权力关系的调整,公共性的发育过程就充满不确定性。二是社会形成良性、有序的自我协调与自我组织能力。唯有如此,社会的主体性才能有序生发,个体超越自身狭隘利益、关注公共生活才具有稳定的社会基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