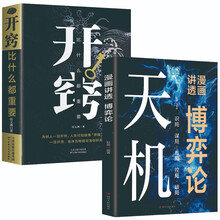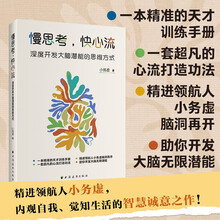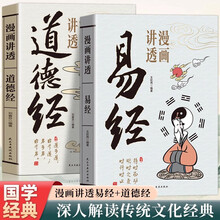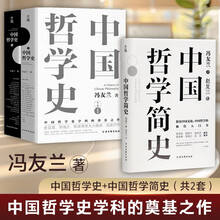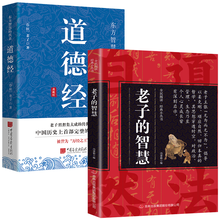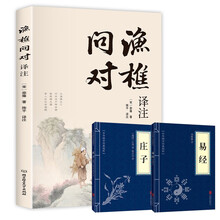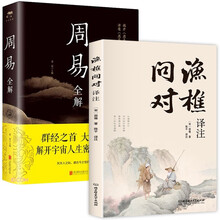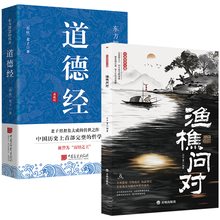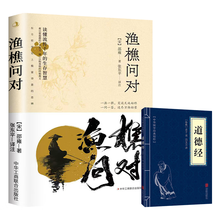《良知学的调适(王塘南与中晚明王学)》:
在阳明的思想中,其对致良知工夫的理解,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是对“四句教”的理解,一是对“事上磨炼”的理解。在四句教中,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当下本有而呈现,因此,“知善知恶”是良知,而“为善去恶”的格物工夫实际上就是致当下呈现的良知于事事物物之工夫。在对“事上磨炼”的理解上,阳明强调磨炼良知而使其精精明明。此实际上是致良知工夫的两个层面:一是推致,一是扩充。此点在张学智先生所撰《明代哲学史》中有较为精彩的分析,在此不作具体展开。总体而言,在阳明的思想中,致良知是达用的工夫。推致与扩充实是两种达用方式,前者是使得良知由知而成行,后者使得良知由源而成流。
阳明一传弟子关于阳明思想所作的辩论,基本围绕以上两个方面进行,并由此形成了以龙溪为代表的推致派与以双江、念庵为代表的扩充派。此是以阳明的思想体系来划分其一传弟子的思想倾向。
阳明一传弟子自身围绕“见在良知”这一中心议题进行辩论,实是将阳明思想中的推致与扩充推向两个极端。龙溪肯认见在良知,强调一悟便了,推致良知的工夫即转化为悟的工夫。双江、念庵否认良知之当下见在性,从而强调一个主于未发的工夫,由此而体得良知当下见在,“体立而用自生”。此时由源而流的扩充工夫实是通过由未发本体而见在良知的立体工夫来体现。就此来看,体用关系是两者思想之不同的关键所在。
龙溪以见在良知为体,因此,工夫就是达用。而双江、念庵以见在良知为用,因此,强调立体工夫。若将体视为知,用视为行,龙溪面对的是知而不行的问题,此点与阳明相似,因而在工夫上强调达用以成行。而双江、念庵面对的是知体未立、以行为知的问题,因而强调立体以成知。
比较而言,后者是否易有只知不行的流弊呢?阳明尝言:“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阳明反对朱子只知不行,双江、念庵在此点上是否类于朱子呢?实则不然。双江、念庵的立体工夫实包含达用工夫,立体是工夫,达用是效验。
因此,双江、念庵与龙溪之不同,主要在于其对见在良知的体用定位不同,由此而分化为立体与达用之两途。
就此两途的比较来看,见在良知的呈现,使得龙溪悟得良知的工夫有了必然性之保证;而未能肯认见在良知,使得双江、念庵主于未发的工夫难免缺少依循。此涉及阳明思想所开发出的另一议题——本体与工夫关系之辩。也就是说,本体在何种层面上对工夫具有作用。
在阳明的思想中,阳明通过“良知为天理的昭明灵觉”消解了立体的工夫,而通过良知的推致与扩充二义肯认了良知本体对工夫的指导意义。龙溪强调本体的见在层面,而双江、念庵强调本体的本有层面。无疑龙溪更能坚持阳明本体对工夫具有引领作用的立场。但是若细析龙溪之工夫为何而易,主于未发的工夫为何为难,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更为复杂。
肯认见在良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肯认了包括工夫在内的任何发用皆可能具有“见在良知”的性质。就此来看,工夫的意义则被取消。双江言龙溪“俱以见成作工夫看”即此意。①否认见在良知,在某种程度上,即对一切发用首先持怀疑态度。因此,作为工夫的发用又如何不被怀疑?双江、念庵之工夫难以令龙溪信服,即在于此。此是本体与工夫关系上较为极端的理解。
变通而言,龙溪肯认见在良知,并不意味着包括工夫在内的现实发用皆具见在良知之性质,因此。见在良知于人而言,则是时有时无。双江、念庵不肯认见在良知,但是肯认通过一种发用工夫可以抵达见在良知,那么此时的发用工夫实际上即具有见在良知的性质。就此来看,见在良知时无时有。因此,阳明后学之两派,在见在良知时有时无这一点上实有共识。但其着眼点有所不同。龙溪着眼于见在良知的“显”而做工夫,双江、念庵着眼于见在良知的“不显”而做工夫。而就工夫的本体依据来看,此须诉诸“志”,后文将有进一步论述。此是阳明一传弟子围绕良知当下呈现与否所展开的争辩。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