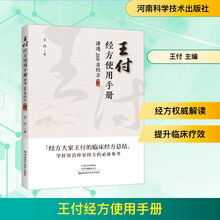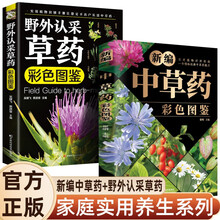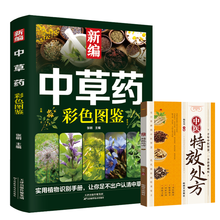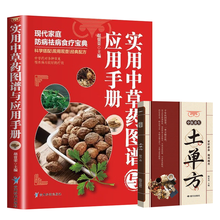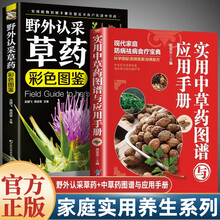《兵道·中医》:
《三国演义》第十八回中,有一段贾诩智胜追曹军的故事,就饱含着军事辩证法的哲理。在安众一带,曹操用计谋打败了张(绣)、刘(表)联军。就在这时,忽报袁绍欲兴兵许都,曹操大惊,匆忙撤军,返回许都。书中写道:操得书心慌,即日回兵。细作报知张绣,绣欲追之。贾诩曰:“不可追也,追之必败。”刘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机会矣。”力劝绣引军万余同往追之。约行十余里,赶上曹军后队。曹军奋力接战,绣、表两军大败而还。绣谓诩曰:“不用公言,果有此败。”诩曰:“今可整兵再往追之。”绣与表俱曰:“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今番追去,必获大胜;如其不然,请斩吾首。”绣信之。刘表疑虑,不肯同往。绣乃自引一军往追。操兵果然大败,军马辎重,连路散弃而走。刘表问贾诩曰:“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败;后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日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验也?愿公明教我。”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操敌手。操军虽败,必有劲将为后殿,以防追兵;我兵虽锐,不能敌之也;故知必败。夫操之急于退兵者,必因许都有事;既破我追军之后,必轻车速回,不复为备;我乘其不备而更追之;故能胜也。”刘表、张绣俱服其高见。
下面我们来看《北史·姚僧垣传》记载的一个医案。梁武帝尝因发热服大黄,僧垣曰:“大黄快药,至尊年高,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梁元帝尝有心腹病,诸医皆请用平药,僧垣曰:“脉洪实,宜用大黄。”元帝从之,进汤讫,果下宿食,因而疾愈。
梁武帝病发热,自以为须服大黄,姚僧垣以为不宜,武帝不听而致病笃;元帝有心腹病,他医请用平药,姚僧垣据脉象认为宜用大黄,元帝从之而疾愈。同服一物,一愈一危,同样饱含着中医辩证法的哲理。
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此一时为是,彼一时为非,一切矛盾都随时间条件而变化。用药如用兵,中医就叫辨证论治。朱良春老中医在治疗风湿病时指出:临床上,在辨证无误的情况下,用药后可出现三种治疗反应,一是药后证减,二是药后平平,三是药后证剧。对于第一种情况,守方较易;对于第二种则守方较难,往往求效心切而改弦易辙;对于第三种情况则守方更难,往往遇此迷茫不解,杂药乱投。对药后证减者,不能简单地守方续进,而要根据某些症状的消退及主要病理变化的突出,进行个别药物的调整或次要药物的取舍,但基本方药不应有大的变化。对于药后平平者,多是证重药轻而致,虽守原方,然须重其制而用之(或加重主药用量,或再增主病药物),集中优势以攻顽克坚。药后证剧者,乃药力生效,外邪欲透之故,可守方续进,以待佳效。大量临床事实可证明此论(痹证专辑),对于药后证剧(就如第一次追击的失败),却蕴含着第二次追击胜利的因素,同样具有辩证法思想。
中医许多治法无处不充满着贾诩在追击中的辩证法。如中医伤寒和温病的治疗理论认为:伤寒热邪在里,劫烁津液,下之宜猛;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不可再下。湿热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大便硬,乃为无湿,始不可再攻也。同样的大便溏,病因不同,治疗也不同,充满了辨证思维。
再如,《伤寒论》为中医的辨证论治思维奠定了基础。岳美中老中医说:《伤寒论》在辨证论治上,既掌握了客观存在的空间,又抓住了发展变化的时间,从哪里见得呢?比如一个太阳中风的病证,有一个针对性强的桂枝汤,不就可以解决得很好吗?为什么他又在桂枝汤的基础上,于后面拟出十几个方剂呢?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不发展的疾病,况且外感热性病属炎上的火,而中风证又体质素弱,抗病力不足,更容易起变化,不抓住它在时间上的运动,只静止孤立地掌握它在空间上的客观存在,会随时碰壁,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仲景以高度的智慧,敏捷的手腕,抓住了疾病运动的时间,随病机以赴,毫不失时地加以分析问题,自使病无所遁,方无虚发。岳老的这段解说很形象地说明,《伤寒论》许多地方也充满着贾诩在追击曹军中的辩证法。
又如山西四大名医之一的李翰卿老中医对《伤寒论》303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有一段体会。李老说:二三日以上,这是从时间上让人辨别是否阴虚有热的一种方法。过去我对这名句话是不太注意的,往往一见心烦不卧就用此方,服过后效果不够满意。有一次我自己患本病很重,自己不能处方,中西药用了好多,效果均不太好。最后,一个朋友坚持主张服用此方,数剂后,疾病完全告愈。过了1年,又患此证,开始即服此药,2剂毫不见效。我的体质本来较弱,年龄75岁,从来不能服泻药,当时脉证如前,所不同者,自己不能考虑。因病难以忍受,放胆服增液承气,一剂其证霍然而愈。因此认为仲景“以上”二字是防止有虚中夹实之证存在,也从此更认识到辨证和实践的重要性。
李老此段认识更证实了岳美中老中医所说的,《伤寒论》在辨证论治上,既掌握了客观存在的空间,又抓住了发展变化的时间,更印证了中医许多地方充满着类似贾诩在追击中运用的辩证法思想。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