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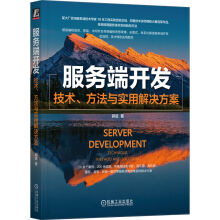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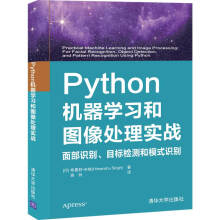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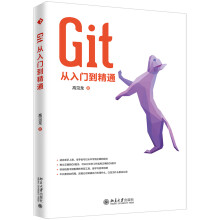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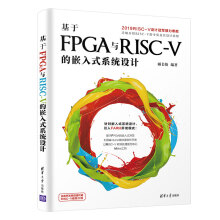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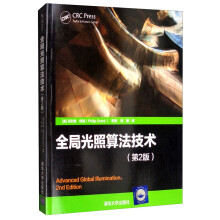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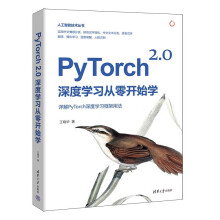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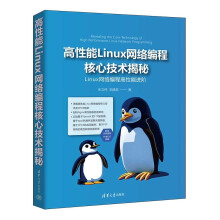
把握和厘清20世纪中国史学演变的线索和格局
本书系探讨20世纪中国史学演变的专门之作。全书以史料派、史观派的分野作为内在线索,将百年中国史学分为1900—1929年、1929—1989年、1989—2000年三个时期,从“问题”出发,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分析,勾勒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填补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新史学”的发轫
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不是3世纪、5世纪,也不是17、18世纪,它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不管此后的历史延伸多久,——不管延伸30世纪还是40世纪,人们都会把20世纪的历史学作为自身的起点,而把此前的历史学当作自己的“史前史”,或仅仅当作史料使用。20世纪是中国史学一次新的日出。
20世纪中国史学由“新史学”思潮开篇。“新史学”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也有独立的内涵特征。
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潮的研究,下列成果较具代表性:俞旦初《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以及《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连载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4期和1983年第2期),后均收入俞氏著《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胡逢
(下转第23页)
(上接第22页)
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蒋俊:《中国史学
近代化进程》,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代序言》,
〔日〕浮田和民讲述、邬国义编校:《史学通论四种合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越最近的研究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不同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后至19 世纪末,中国史学的变化程度与影响力度,总体上并不超出乾嘉史学及以往古代史学的其他时代,这一时期传统史学主体并无根本性变化,难言具有近代史学意义的转变。从学科意义上形成一个新的史学发展阶段,其标志应该是史学自身包括历史观、研究理念、研究视角、课题意识、研究方法、史料观念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要等到20 世纪初期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而形成的“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参见张越:《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梁启超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等文拉开了清季“史界革命”或“新史学”运动的序幕。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激烈批判传统史学,同时提出一套新史学的设想和方案。当其时也,日本的“文明史学”(histories of civilization, 日文英译bummeishiron)正在风行。“文明史学”产生于明治初年,受法国基佐(Guizot)和英国巴克尔(Buckle)的文明史著作以及斯宾塞社会学理论影响,代表人物为福泽谕吉和田口卯吉。它以“鼓动世道之改进,知识之开化”为宗旨,激烈批判封建史学,主张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取代帝王为中心的、偏重政治权力记载的旧史学。戊戌变法的总设计师康有为早在变法前的1897年,就已在其所著《日本书目志》中列出若干日本文明史著作,作为其大弟子的梁启超不可能不留意到。而梁启超也在发表《新史学》的同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东籍月旦》,向国内介绍日本书籍,其中对文明史学作了专门介绍,表示十分推崇。
胡逢祥:《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
梁启超等人受日本文明史学的启发,不但从理论上重新规定了历史学的性质、目的、范围和对象,而且进行了编撰新史的初步尝试,推出了一批“中国通史”“中国历史教科书”性质的作品。其中,1904—1906年出版的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为著名的一部。1903—1904年东新社出版的曾鲲化的《中国历史》也风行一时,1905—1906年刘师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有不小的影响。此外还有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蒋荫椿编《历代史要》,1904年陈庆年编《中国历史》,1907年吕瑞庭、赵徵璧编《新体中国历史》,1909年徐念慈编《中国历史讲义》等。它们都在内容与形式上与旧史相区隔,洋溢着“新史学”的理念和方法。这场“史界革命”宣告了延续两千年的传统史学的终结。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特征可以作如下概括:从历史观或历史本体论上看,新史学是反王朝体系或打破王朝体系的。王朝体系的最大弊端,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二十四史“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以为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8—280页。
而真正的历史不应该是“君史”,应该是“民史”,换句话说,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帝王将相,而是普通国民:“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者,“谓之君史”,“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者,“谓之民史”,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而中国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
邓实:《史学通论》,《政艺通报》第12期(1902年8月18日)、第13期(1902年9月2日)“史学文编”。
因而他们主张应写一部“普通民史”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君史”。1902年,陈黻宸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他说:“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他还设计出一种重视民史的新通史方案,其中有“平民习业表、平民风俗表、义民列传”等内容。曾鲲化编的《中国历史》即非常重视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1904年,以“民史氏”自居的邓实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撰述民史进行了初步尝试,并著成《民史总叙》1篇和《民史分叙》12篇。
如果说从历史观上看,梁启超等人已完成了一场带有颠覆性的“史学革命”,乃至凿开“写自下而上的历史”之先河的话,那么,从方法论上看,新史学的主张者们则同样充当了“以社会科学治史”的首倡者。他们呼吁:历史学必须跨用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和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统计学方法等“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者,还必须借鉴伦理学、心理学和逻辑学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的成果。他们甚至已意识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在这“一切科学”中,“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是史学必须“兼及”者,而作为史学之“首重”和“总法”者,则是“政治学、社会学”。
《陈黻宸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6—677页。
汪荣宝认为,“世运渐进,学术之分科亦如工艺之分业,源一流百,互相会通,凡今日众多之科学,通观之,无不有昆弟伯叔之关系,断无一种之学术,不借他学之应援而独立自存者也。史学之范围,既极广博,从而其求援于他学之点亦与为多焉。”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1902年第9、10期。
章太炎在1902年7月致梁启超的信中曾说:“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
《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1902年第13号。
其时章氏方译毕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可见他已将社会学书籍的译读与《中国通史》的编写结合起来思考了。他的《訄书》中,有不少文字便是运用社会学观点和方法写成的。自章太炎、严复、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开始,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已经发端,他们开跨学科研究之先路。
关于梁启超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作为,可参见石莹丽:《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无论是历史观上的革命,还是方法论上的革命,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尽力把历史学纳入救世的轨道,所以,从著史旨趣上来看,梁启超等新史学的倡导者们反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为学立场,毫不避讳地主张“学以致用”:“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选集》,第287页。
在他们看来,“历史之天职”在于“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与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从而“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出世辞”首编第二章四“进化”,东新译社,1903年。
一句话,“史学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我国遂不可救”。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选集》,第277页。
如此看来,清末民初的“新史学”,从历史观上看,带有“反封建”的启蒙性质;从方法论上看,带有跨学科的现代性质;从为学旨趣上看,带有重致用的功利性质。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以革命为旗帜,在主观上是要截断传统而另起炉灶,事实也是如此,它基本上与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传统史学无缘,它的出现只能意味着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
孙江认为,“新史学在中国的诞生是近代中西遭遇的产物,也是古今中国学术思想断裂和持续努力的结果”。参见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72页。
从整个清代史学、特别是晚清史学的发展大势看,尽管它也一直处在不断的调整和转变的历程之中,但这种调整和转变仍严格限制在传统学术的框架之内,而且基本看不到任何能够生成后来“新史学”的因素。“新史学”的出现严格说来是一场学术突变。学术史家公认,晚清学术界出现了两股思潮,一是经学上兴起了今文运动,二是史学上的西北史地研究很快被“西洋史地”研究所压倒。就史学的后一倾向而言,从“西北史地”研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西洋史地”研究上来的。所以,“西洋史地”研究的热潮在清末的出现,完全是外力所致,是时势剧变的结果。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后,国人就渐渐放弃了自尊自大的心理,到了英法联军之役,外人以少数军队直捣京师,朝野震动,渐感到非接受西洋文化不足以立国,于是,一般士大夫对于西洋学术,兴趣陡增,西学在此之后甚至也成为大众的关注焦点。
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42页。
甲午战后,西学书籍、特别是“西洋史”更是成批涌入中国。
1896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目下收录的世界史译书仅有约25种;而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34年刊本)所收录的出版于辛亥期间的史志译书已达125种,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排在全书之首。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泰西新史揽要》,此书为“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97页。。
《万国史记》出版后也行销一时,“读书界大概人手一编”
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43页。。
还有一部“大受一般学者之欢迎”的《万国史纲》,当时被称作“欲知万国文明之变迁,且研究二十世纪之新史体者,不可不人手一编”。
《万国史纲》再版广告,《中外日报》1904年3月24日。
这些史籍像播下的种子一样终于要破土抽芽了:“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译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远胜过我国的旧史学”,他们因此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也“大有改造的必要”。
齐思和:《晚清史学的发展》,《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248页。
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所谓“新史学”思潮遂应运而生。所以,无论是“反王朝体系”的历史观,还是“以社会科学治史”的方法论,抑或是用发现“公理公例”来造福民族国家的为学旨趣,都与中国传统史学迥异。所以,“新史学”的出现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换句话说,“新史学”完全可以看作是“西洋史”在中国的全盘移植。
这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其实是东京”,“重要的中国史家像梁启超和章太炎”20世纪初曾在那里“接受到日本‘文明历史学’的影响”,因此“中国史家也开始随着日本的前例,根据西方历史模式来再建构和再诠释中国历史”。
参见余英时:《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见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经过这场“史界革命”的洗礼,人们大都认识到,以往延续两千年的正史格局难以维系了,以探求人群社会的进化为目的,突破单一的政治史模式,拓展研究范围,更新研究方法,诸如此类的新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轰动一时的“新史学”思潮大约在辛亥前后就逐渐衰退了。
引言 / 00
一早期阶段:“新史学”与“新汉学”的
交替(1900—1929)
1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新史学”的发轫 / 0
2 胡适、顾颉刚的“新汉学”勃兴与“新史学”
的隐没 / 0
3 “新汉学”的正统化:史语所的设立 / 0
二中期阶段: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及其
主流化(1929—1989)
1 “新史学”的重生:唯物史观派的出场 /
2 “新汉学”的下滑与分化 /
3 唯物史观派跃居主流及意识形态化 /
4 未曾中断的史考传统 /
三最后十年:从“新汉学”复兴到
“新史学”归来(1989—2000)
1 “国学热”席卷而至 /
2 执两用中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
3 “新史学”归来:社会史研究的繁荣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