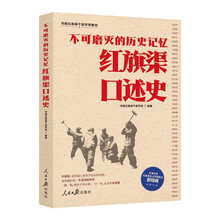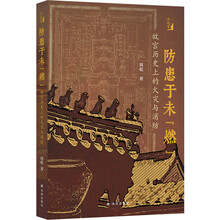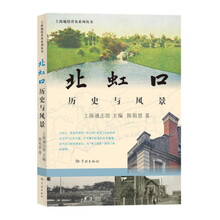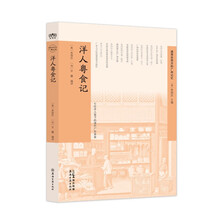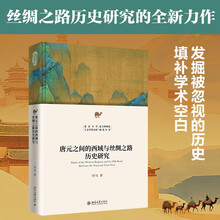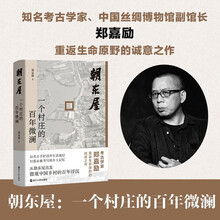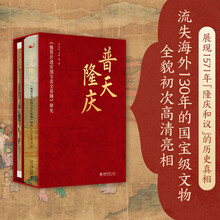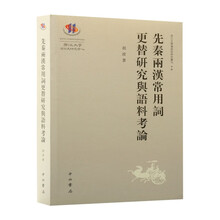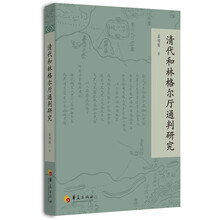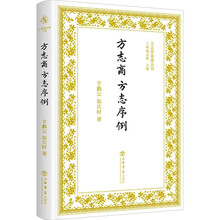从福州建城开始说起
说起福州,我们一般会自豪地介绍道:福州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言下之意,福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福州建城,要追溯到战国末期至汉代初年的无诸与他开创的闽越国。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汉高祖五年(前202),汉朝册封无诸为闽越王,册封地就在台江境内的大庙山。这个历史事件,开启了史书典籍确切记载福建历史事件的时代。
西汉时期,今福州城区的大部分地域还淹在水下。台江境内的大庙山、南禅山、吉祥山、横山、保福山、金斗山、彩气山等,乃滔滔闽江中的小岛。《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所言不虚。离大庙山不远的文山(今福州八中)考古工地,出土过原始青釉弦文盂,胎质坚硬,釉层较薄,器物上有清晰的轮旋纹,饰以铆钉,经考证为商周时期的遗物。这也说明3000多年前,吉祥山一带已有原始部落在这江海交汇的“小岛”上渔猎为生。
战国后期,春秋五霸之一——越王勾践的后裔于越人人闽,与闽人融合,发展为闽越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闽中郡”,废除了勾践第十四世孙无诸的闽越王称号,降为“君长”。秦末,无诸率领闽越军队,先是反秦,后又助汉灭楚。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无诸因助汉有功,被封为闽越王。无诸在惠泽山(即大庙山)筑台接受朝廷册封,史称越王台。后人在越王台旁修建规模宏大的闽越王庙,俗称“大庙”,这也是惠泽山又叫大庙山的由来。
传说无诸后裔东越王余善在“惠泽山之南,崇阜屹立,俯瞰巨潭,钓得白龙”,感到十分祥瑞,也筑一台,称钓龙台。钓龙一说,今天看来类似神话。据学者推测,古代闽人称鳄鱼为“蛟龙”,因此余善钓的龙,可能是鳄鱼之类的两栖爬行动物。古代福建的河流有很多鳄鱼,在水上生活的闽人为了防止蛟龙之害,便在自己的身上以墨文身,自称“龙子”。古人有时也会诱杀鳄鱼,闽王余善钓龙,应当就是铲除鳄鱼的行动。由此观之,余善杀鳄,要比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广东潮汕地区驱鳄早一千多年,这也侧面说明,福州的开发要早于岭南不少地区。
当年无诸依山筑冶城,开辟东、西、南三城门,冶城之南的大庙山周围,都是江河潮水所及之处,百姓散居城外一片片洲地之中,正如后世诗人所称:“无诸建国古蛮州,城下长江水漫流。”汉使奉汉高祖刘邦之命南下册封无诸,船就停泊在南台。需要说明的是,旧时的“南台”意为位于福州城南的高地。清代郑祖庚在《闽县乡土志》中载:“五代南唐时,上下杭皆闽江洋洋,登南城翘望,有台临江……所谓台,即越王台也。”南台的范围大至为北起南门兜,南至烟台山,东至六一路,西至白马河,有别于我们现在说的仓山区所在的“南台岛”。南宋梁克家所著《三山志》对南台之名解释为:“南台,城南有越王钓龙台,故名。”宋名相赵汝愚曾在钓龙台下的潭尾街留下题刻“南台”,今已无寻。
南台成为渡口,得益于其两头通潮水的独特水运优势。仓山岛将闽江分成两个支流,南面乌龙江,北面白龙江(又称台江、闽江)。闽江涨潮时,海水顶托着江水向闽江上游涌流。由于乌龙江江面开阔,江潮先涌进乌龙江,而后向上游涌进,经南台岛中部和北部的贯通乌龙江与白龙江之间的数条河道,涌入白龙江,与闽江上游来水合股形成白龙江自上而下的江潮;白龙江的下游海潮来得较慢,两股潮水交汇于钓龙台下。
当时,闽江下游的船舶航行主要靠潮水和江流,船舶下行时顺流而进,船舶上行时则候潮而行。正因为南台两头通潮,上下游船舶都方便在此停泊,使得南台自然而然地成为福州城南部的水运枢纽和商贸聚集地,并历干余年而延续至今。
无诸册封和余善钓龙之后,与大庙山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就少了。经历过历史的高光时刻,如今的大庙山更像一位慈祥低调的老者,其山体早已与周围的民居和学校融为一体,看起来并不显眼,甚至很多人都没意识到这是一座山。但在三四百前年,大庙山在福州百姓看来依然是高大巍峨的,明代诗人称之为“崇岗”,清中叶还有“高崔嵬”之说。当时,大庙山雄踞水中央,周围江水环潆,一片汪洋,明人有诗赞曰:“吞吐潮声当海口,屈盘山势控闽中。”入夜,登上大庙山山顶极目远眺,点点亮光闪烁,分不清是星辰还是渔火,不知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霸气中充盈着仙气,令人心驰神往。无诸当年受封选择此处,也许看中的就是这份霸气和仙气吧。只是如今,越王庙、越王台、钓鱼台已无踪影,让人生出“龙随人去不复见,古树寒烟锁青苔”的沧桑之感,唯有那些人与事,还留存在史籍上,流传在世人口中,也算是对历史的慰藉吧。
到了汉武帝时期,无诸的后代子孙余善等人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到元封元年(前110)多次攻打周边的汉朝附属国,并挑衅大汉王朝。汉武帝不胜其烦,由于派大军来攻打。灭了闽越国后,汉武帝将闽越族人尽数迁徙到江淮之间,于是福建又回到了莽荒时代,仅少数遗民遁入深山,与世隔绝。三四百年时间过去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躲避战乱,中原的一些家族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