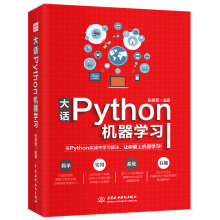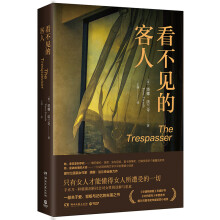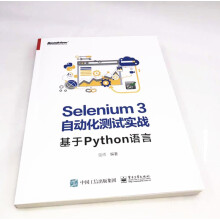第1章能源安全挑战的分析框架
能源的可持续供应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技术转移与合作瓶颈凸显,中东、北非、拉美等能源出口地区地缘局势动荡,特别是俄乌冲突导致欧洲的能源供应紧张波及全球市场,因此国际能源安全态势面临新的更加复杂的局面。
与此同时,对生态环境的关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推动第三次能源转型加速发展,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主导能源是能源转型的必然方向,但转型的过程伴随着技术、环境、政策等多种不确定性,能源的安全稳定供应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能源安全问题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从内涵到策略都需要新的解读和分析范式的创新。
1.1背景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能源供需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应对能源安全问题。不仅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成员国加大了战略石油储备的规模,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在大规模地建立自己的战略石油储备,增加自身应对石油危机和地缘局势变化的能力。同时,各国都在积极地探索替代能源,增强能源的自给能力,表现为新能源新技术和综合实力的竞争。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正改变着世界能源的格局,凭借着先进的生产开发技术和完善的管网设施,美国的页岩气成本巳具备商业竞争力(Wangetal.,2014)。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降低其能源对外依存度,特别是逐渐摆脱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日本的资源极其匮乏,约90%的能源需要依赖进口。不利的自然条件也使得日本十分注重海外能源供应体系的建设,坚持多元化的进口策略,并尽可能降低对政治不稳定地区的能源进口依赖;另外,日本非常重视通过立法促进节能,运输部门、家庭部门、服务业部门的能源效率持续提高(Vivoda,2012;Matsumoto and Shiraki,2018)。德国同样受制于其相对匮乏的能源资源。近年来,为了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德国坚定地将能源战略重心转向可再生能源,从体制机制和技术产业各方面不断创新,逐步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利用(Strunz,2014)。
资源约束是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源。我国“贫油、富煤、少气”的资源禀赋制约了消费侧的能源结构优化,同时导致我国油气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Qiangand Jian,2020)。我国2017年成为世界*大原油进口国,2018年又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大的天然气进口国。2018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同比上升2.6个百分点;天然气进口量125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升至45.3%(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能源需求仍将持续增加,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的主要因素(周大地,2010)。
更为严重的是,当前国际地缘局势动荡,获得海外能源的风险不断增加。美国可能重启对伊朗油气出口制裁等新的地缘因素的出现等不稳定因素,使得能源安全问题更为严峻。能源运输通道和复杂的地缘局势联系在一起,马六甲海峡等高风险地区影响着能源进口供应链的安全。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和市场波动加大了我国经济运行的成本和风险。能源价格的上涨和波动会沿着产业链传导至经济系统的各个部门,成为经济失衡和输入性通胀的风险之一(Lietal.,2017a)。我国能源价格改革尚不完善,在国际能源定价权方面仍缺乏主导能力,被动作为价格接受者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能源贸易风险(范英等,2013)。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提出了碳中和长期目标,我国也宣布了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和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这些战略和政策正在加速推动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次能源转型。此次转型与前两次不同,其源于人们对能源和环境制约下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担忧。转型的根本动力也不仅仅是生产力进步更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与日益恶化的环境、气候和安全问题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发展进程将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何建坤,2014)。近年来,作为替代化石能源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非常迅速,但其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然不高,成本下降出现瓶颈,间歇性和波动性等特点进一步制约了其发展速度,2018年非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为14.3%。但从长期来看,替代能源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未来哪个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方面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哪个国家就能率先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在能源安全方面拥有主动权(Jewell etal.,2014;Larcom et al.,2019)。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境外能源基地局势不稳、运输通道风险增加、替代能源技术亟须突破的严峻挑战,分析国内外能源系统演化规律,量化监测能源安全动态,积极应对我国能源安全现实挑战,对于中国能源安全短期应对策略和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1.2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能源安全挑战
能源安全的概念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并随着时间不断丰富。其*初内涵主要是为了降低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以及确保石油的稳定供应(Lu et al.,2019)。但随着世界能源资源的大量开发和能源体系的低碳化,人类社会对于能源安全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Malik et al.,2020)。能源安全的理论研究伴随着保障能源安全的实践而不断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即能源安全理论的形成阶段、过渡阶段、发展阶段和完善阶段(范英等,2013;Ge and Fan,2013)。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能源安全理论研究处于形成阶段。由于石油危机的巨大冲击,各国政府和学者纷纷致力于石油安全的评估体系及保障石油平稳供应策略的研究,并一直延续至今(Brown et al.,1987;Neff,1997)。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采用多样化的能源政策,能源安全的概念逐步从石油扩展至包括石油在内的多种能源,其中以天然气和新能源供应安全的理论研究*为突出(Pimentel,1991;Dresselhaus and Thomas,2001)。
21世纪初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和能源格局背景下,能源供应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各国从仅仅关注稳定的能源供应,逐步向能源价格安全、能源供应链安全、能源使用安全等多个维度延伸(Yergin,2006)。与此同时,能源的综合评价、国际关系和地缘局势也成为各国学者和能源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IEA,2007a;Coq and Paltseva,2009)。当前,在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下,能源安全问题巳经上升到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能源开发、转化、利用能力的竞争成为各国博弈的核心。学界也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新能源技术投资与研发、能源科技创新、核心技术突破等方面(Chu and Majumdar,2012;Mathews and Tan,2014),试图利用能源转型的契机从根源上解决长期的能源安全问题。
然而,本轮能源转型的核心动机并非完全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当前正处于转型的初期,从全球范围内的转型进程来看,欧盟、中国、美国、日本等能源消费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均在积极探索转型路径,但由于国情和理念的差异,各国的转型路径不尽相同(李俊峰和柴麒敏,2016)。本轮能源转型的核心动机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尽管各国均想实现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的双赢,但由于这两个动机的差异以及资源条件的不同,大部分国家在转型的实践中是以其中一个动机为主导同时兼顾另一个的(范英和衣博文,2021)。由于非化石能源既有零碳属性又兼顾可获得性,因此,从长期角度来看,无论是转型的结果还是两个核心动机的实现都具有高度一致性。然而,各国在各自能源消费结构下实现这个长期目标的路径具有差异性,其转型规律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即资源禀赋和核心动机。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安全在短期视角下是有差异的,应对气候变化需尽可能使用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但保障能源安全应尽快降低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因此,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将经历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通常意义上的一次能源包括四大类,从含碳量角度由低到高排序依次为非化石能源、天然气、石油、煤炭;从供应安全角度排序,各国由于资源禀赋和能源进口通道的差异而不尽相同,但对大部分国家而言,安全角度从髙到低的排序依次为非化石能源、煤炭、天然气、石油(Wang and Zhou,2017)。因此,核心动机的差异会影响转型的短期路径,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非化石能源优先替代何种化石能源,以及过渡能源的选取。同时,各国的资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目前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油气资源。资源禀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进而影响能源安全;同时也决定着能源价格,进而对转型成本产生影响,导致各国的转型决策存在差异。
从“十一五”时期开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能源转型与气候变化,已逐渐形成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动机同时兼顾能源安全的转型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过程中,我国能源安全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背景下,能源安全的概念、内涵及评价体系发生根本改变,有效识别各国尤其是我国能源安全水平需要在新体系下对能源安全进行定量评估和监测预警。其次,我国“缺油、少气”禀赋现实和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增加,在美国页岩油气革命、“一带一路”倡议、“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等宏观新形势下,我国迫切需要调整境外能源基地布局与控制运输通道风险,并建立能源供应中断政策响应机制,保障能源持续供应和经济平稳发展。*后,能源系统转型是能源经济结构和能源创新技术的系统性变革,在深刻认识世界能源系统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制定替代能源发展路径对于我国制定能源长期发展战略,保障能源安全乃至推行能源独立势在必行。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深刻认识能源转型背景下的能源安全关键问题,结合国际局势和能源格局适时制定合理对策与政策有助于解决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挑战。
1.3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能源安全内涵及概念模型
随着碳减排政策从“软引导”转变为“硬约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成为大势所趋,气候环境压力通过气候政策不断从消费端向供给端转移,给能源供给安全带来直接影响(Toke and Vezirgiannidou,2013)。能源转型过程中,复杂的国际局势和能源演化趋势使得国家能源安全的影响要素更加多变,且相互交织。在新形势下,从系统性视角分析能源安全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正确梳理各类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理解能源安全的内在逻辑,从而为制定能源安全策略和应对措施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
为更加全面把握能源安全态势,我们基于当前能源转型新形势和广义能源安全概念,提出能源转型背景下的能源安全的新概念框架,如图1-1所示。我们认为,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能源安全指国家能源系统处于不受能源风险威胁的能源安全状态,以及规避或抵抗能源风险从而维持安全状态的能源安全保障力。其中,能源风险指系统面临或潜在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给能源在供应的数量、价格和环境上带来一定的威胁;能源安全状态指能源在供应的数量上充足可靠、价格上合理、环境上可持续;能源安全保障力指能够对能源风险进行事前预防和事后应急,从而规避能源风险并抵抗能源风险带来的冲击,持续保障能源安全状态的能力。与传统的能源安全相比,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能源安全强调考量环境风险、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可再生清洁能源的长期发展能力等。
首先,能源风险指系统面临或潜在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给能源在供应的数量、价格和环境上带来一定的威胁。按照风险形成的原因划分,大致包括地缘局势动荡、价格大幅波动、不可抗力和事故突发、生态环境恶化等风险。其中,地缘局势动荡风险指能源输入国或者能源输出国因为某种或多种因素被人为地停止或减少能源输入和输出,从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害及其他国家主权与政治等方面的损失;价格大幅波动风险指能源价格在短期内大幅度波动对经济发展可能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