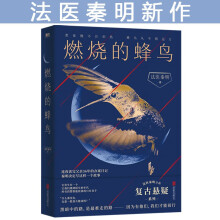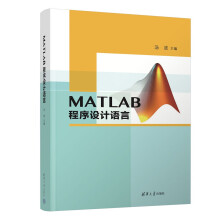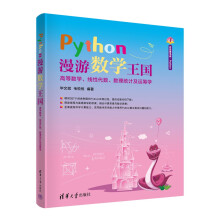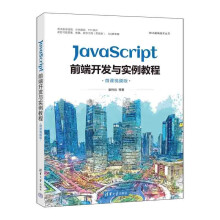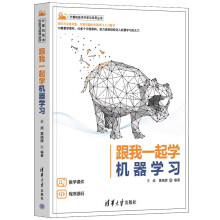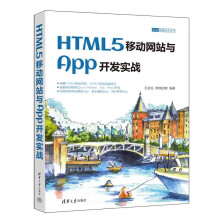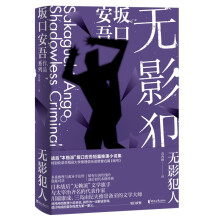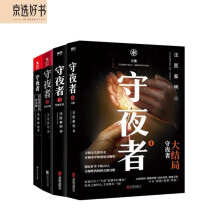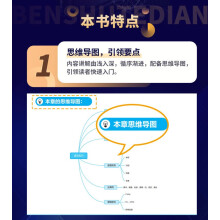一、《析津志》
“析津”一词来自古人的分野说。人们认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是相通的,因此将地上的区域、州县或山川与天上星辰相互对应与映射。历代王朝为宣示天下正统,多顺应此说,将实际统治区域纳入分野,渐使分野具有了疆域象征的政治内涵。1012年,汉文化修养颇高的辽圣宗改元开泰,同时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覃恩中外。“析津”即分野说中的燕地为“析木之津”。辽圣宗改此二字,或有更深远的意味。1153年,金海陵王徙都燕京,改元贞元,“大兴”替代“析津”成为府、县名称。但“析津”作为北京地区的代称仍然流传了下来。
《析津志》,又名《析津志典》,是已知北京地区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颇负盛名。该书成于元末明初。纂者不以当时的名称命名为“大都志”,而称《析津志》,乃是方志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即用地方古名命名书名。
纂者为元末熊梦祥,生卒年不详,字自得,号松云道人,江西丰城人。此人聪敏旷达,博读群书,工书法,擅绘画,又旁通音律。在公卿士人间有一定声望。曾以茂才异等被举荐为白鹿书院山长。后被征召入都,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老疾请归,游于江淮间,放意诗酒。年九十余卒。
令人惋惜的是,该书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即已失传。迄今,不仅纂修背景很难稽考,就是卷数、体例等,我们亦无从得知。成书于明正统六年(1441)的《文渊阁书目》著录有:“《析津志典》,三十四册。”可窥知其内容丰富、体量庞大。
因其佚失较早,史籍中的记载同样非常寥落。明代《赵氏铁网珊瑚》一书《元人诸帖》中收录的两篇诗文,是笔者所见关于该书的最早记载。这两篇诗文或许也是后世所有追溯、探寻该书情况的源头。其中一篇为元代史学家、文学家欧阳玄(字元功)题赠熊氏诗,诗前题:“豫章熊公自得携所著书入都城西山斋堂村,山深民淳,地僻俗美,隐者之所宜居,崇真张宜相真人偕往,作诗送自得,兼柬宜相,平心老人欧阳玄。”另一篇为元代诗人张翥(字仲举)的《次韵圭斋先生寄赠松云隐君》,其中有:“近闻京志将脱稿,贯穿百氏手自翻,朱黄堆案墨满砚,钞写况有能书孙。”3由是我们可以约略知道,熊梦祥曾隐居于北京西山斋堂村(今门头沟区斋堂镇)撰著“京志”,而且其时已近完成。
清初纳兰性德(字容若)《渌水亭杂识》称:“豫章熊自得偕崇真张真人”居京西斋堂村“撰《燕京志》,欧阳元功、张仲举皆有诗送之”,并评论道:“元之《大一统志》卷帙繁富,考证亦綦详矣,而自得复撰《燕京志》,仲举谓其贯穿百氏,必有出于《大一统志》之表者。”认为熊氏所修志书定有所长,只可惜“其书之不传也”。
《[光绪]顺天府志》“纪录顺天事之书”将此书认作两种:“熊自得《析津志典》,佚”;“《析津志》,未见,撰人、卷数无考,《日下旧闻考》引用甚多”。可见撰者当时未见此书,因此也并不清楚二书的关系。前既然说该书已于明万历间失传,但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缘何能引用该书呢?
这不得不归功于明代的《永乐大典》。明永乐初年,先后令解缙、姚广孝主持,将其时能见之书悉数囊括,汇编成文献大成,赐名《永乐大典》。《大典》正文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装为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后来,因火厄、灾害等原因,《大典》收录的很多书籍被毁不存。由于《大典》编修时主张保持典籍原文,不擅作删减与修改,使得许多珍贵典籍借此得以流传。幸运的是,《析津志》亦在其中。通过《大典》,我们可以略见《析津志》之大概。然而,《大典》卷帙浩繁,并未刊刻,原本已秘无所踪。现存世者为明嘉靖间所抄副本,但也所剩不多,仅四百册左右。
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朱彝尊在纂辑《日下旧闻》时,因《大典》藏于内府,未能参考。后来,乾隆皇帝令在其书基础上纂修《日下旧闻考》,隐于《大典》中的《析津志》因保存了大量元代北京的珍贵史料,被反复征引。在某种程度上,《析津志》可谓因官修《日下旧闻考》进入众人视野,引起学者的重视。
至于为何《日下旧闻考》的纂修人员能够想到从《永乐大典》中寻找资料,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此人即朱筠,字竹君,号笥河,顺天府大兴人(今北京市)。清代著名学者。时任安徽学政的他向乾隆帝建议从《永乐大典》中校辑佚书,获得采纳。就目前资料看,《析津志》当时并没有被作为校辑的对象。但该书因为校辑工作进入人们视线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朱筠建议的最大影响是引出了《四库全书》之修纂,囿于主题,不做赘述。
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