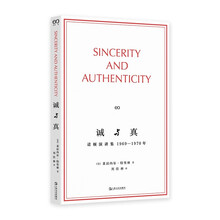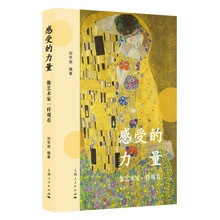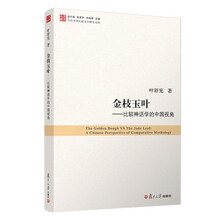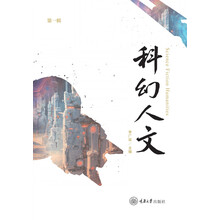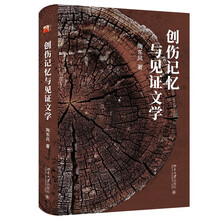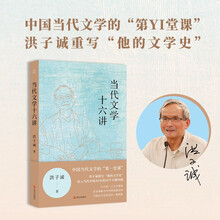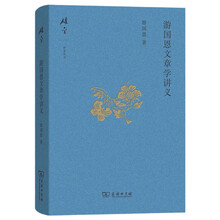诗歌是一种精致的艺术,非常讲求诗美的创造,形式的重要性在诗歌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诗歌艺术技巧的采用可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统一。吕进说过:“总起讲来,内容的抒情美,形式的音乐美,语言的精炼美,这三者的融合就是诗美的本质。”①从诗歌的内容、形式和语言多个方面对诗美进行立体扫描,精炼而集中地阐明“什么是诗美”这个命题。由此看来,对抒情性、节奏感和语言组合的强调直接关系到诗美本质的实现。但90年代一些诗人在消解哲学、后现代哲学反叛姿态的横扫下,头晕目眩地过度发挥,连诗歌艺术美必不可少的组成内容也一概推翻。他们以粗制滥造的艺术手法代替美的追求,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自己多么高明,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消解可谓多种多样,例如:
第一,破坏抒情性。“诗可以叙述生活,但主要是歌唱生活,是敞开直面生活的人(主要是诗人自己)的心灵。”②“歌唱”是抒情的形象说法,抒情对诗歌而言至关重要,虽然任何文学都是作者感情的抒发,但唯有诗歌把感情作为直接言说的对象。“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③吕进这一“诗化”的诗歌定义,更突出了诗歌的抒情特质。“反抒情”作为一个与“抒情”相对的概念出现在诗歌批评中,始于“后朦胧诗”的出现,到了90年代,“反抒情”现象依旧存在。以叙事对抗抒情是“反抒情”的一个重要表现,过多的絮絮叨叨的叙述让诗歌拥挤不堪,流水账式的排列还有什么诗美可言?“擦窗,扫地,用湿布抹去厚厚的积尘,整理/房间,书桌,扔掉无用的纸箱,空瓶,/旧电视报,买年货,拿着500元钱,街上的/人如此之多,节日对于忙碌一年的人来讲,/是准备多一点吃的和玩的,‘来点糖果,瓜子,/和花生,水果也要一些,最好是红富士……”,①。节日的抒情就这样被这些琐碎的叙述埋没,省略号是笔者加上去的,诗人总是在诗行太长的情况下断开诗行,所以引用不得不硬行截止,否则就得引用整首诗。其实这些诗行如果连续不断地写下去,而不分行排列,就成了真正的日志。诗歌并不排斥叙事,适当加入一点叙事性的因素,作为抒情的补充在有些情况下颇为有用,叙事长于营造怀旧氛围、延缓节奏、点染诗思意蕴等。
以叙事对抗抒情之外,诗歌中还出现了滥抒情现象,滥抒情一方面专意反对过去的抒情对象和抒情方式,用戏谑、反讽的方式对待现实世界,例如对祖国好山好水、名胜古迹以及个人美好爱情的消解式表达;另一方面以语词的随意堆积破坏抒情的可能性,读者只有在凌乱中捉寻点滴意义,“抒情美”变得遥不可及。另外,后面将要谈到的对语言诗意的破坏、对意象的破坏等也同样破坏了诗歌的抒情性。
第二,破坏语言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又是所有文学样式中最重视语言艺术的,上面提到的吕进的诗歌定义前半句指明“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然而当消解横扫诗坛的时候连诗歌的语言也不放过,破坏语言诗意的方式非常多,主要是不加选择和修饰地把日常口语移入诗歌中,具体形态包括病态语、碎片语、肮脏语、下流语等。病态语指日常生活中的结巴语、呓语等,典型的是伊沙的《结结巴巴》,应该说这首诗是对诗歌语言最激烈的反叛。碎片语是支离破碎的语言,诗人故意将语言割裂,以为可以增加跳跃性,以为看不懂就说明诗歌有深度。肮脏语也就是通常说的骂人的脏话,有一首诗名字叫作《大好年华》,多美好啊,我们都这样想,但诗人却说:“我当时真愤怒呵/这就是/他妈的人们所说的‘大好年华’。”②《枯燥》中孙文波一声粗野的“他妈的”,把诗歌从想象带回到日常现实,一切依然单调乏味,这“就是我的生活”。日常的多元和丰富在诗人口语化的叙述中迅速萎缩,干巴巴的如同枯树的老皮。下流语则是诗歌中肆意使用和性相关的语言,而且谈得裸露直白,这是有意丑化诗歌的行为,也是对诗歌最大限度的消解。
第三,破坏意象。意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诗歌中有较大的差别,重意或者重象也不尽相同,但它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叶嘉莹说:“中国文学批评对于意象方面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但是诗歌之贵在能有可具感的意象,则是古今中外之所同然的。”①90年代诗歌对意象的破坏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后朦胧诗以来诗歌中有没有意象都令人怀疑。对意象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堆积意象和意象过于私人化两个方面。
堆积意象,顾名思义就是将大量的意象不加选择地堆积在一起,而且往往是丑恶的意象或者普通的意象组合成丑恶的现象。中国古代诗词讲求含蓄美,有时两句诗全由意象组成,例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些意象的组合和整首词的意蕴完美契合,诗人的情绪缓缓流淌而出,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淡远清净的美,丝毫没有拥挤的感觉。使用意象的作用之一是使“意”变得形象可感,然而意象的堆积却使“象”像垃圾一样堆放在诗歌中,非但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反而让诗歌拥挤不堪,大大伤害了诗歌的艺术世界。一个诗人通过一个精神病者的视角带来了一片混乱的意象:“蘑菇云”“猫和老鼠”“小公马”“太阳”“枪”“星星”②,这首诗的其中六行里就包含了这么多的意象,这些意象随意组合在一起,勉强地说可以表现世界的混乱,但表现混乱的方式很多,这样表达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如果没有,为什么还要破坏读者的审美呢?诗歌可以表现丑的意象,但引入丑的事物只是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人们认同和接受世界本来就是丑恶的,丑恶才是真实等等看法。罗振亚说:“在生活未得完满仍残缺之前,隶属于美的诗歌女神完全可以观照丑恶的事物,波德莱尔、李金发乃至朦胧诗等现代主义琴师都曾将恶之花大胆引入,将丑的事物大胆引入。但总是把它作为被征服、被超越、被弥合的对象;而第三代却是……要以粗鄙态袒露人的本原状态。”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