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
“我爱着您。”布尔明说道,“打自心里,爱着,您。”
玛利亚·加甫里洛夫娜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而她终于深深地点了头。
——普希金《暴风雪》
这还真是平凡。年轻男女的情话,不,搞不好大人们的情话也是如此,只要一听,就会因那陈腐与不舒服感而全身汗毛倒竖。
不过这也不能一笑置之,我就听过一个可怕的故事。
有一男一女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男方二十六岁,名叫鹤田庆助,同事们都直接用“阿鹤”来称呼他。而这故事中的女方叫作小森秀,二十一岁,同事们都亲昵地称呼她为“小森”。阿鹤和小森两人彼此有好感。
深秋的某个星期天,两人在东京郊外的井之头公园约会,这时是上午十点。
虽然时间不好,地点也不好,但是两人没有钱。即使拨开草丛往深处走,旁边也依然有看起来“相当明理”的一家人,这两人总是无法好好独处。阿鹤和小森两人都想身处二人世界想得不得了,却又羞于让对方知道,只好开始聊起天空的蓝、红叶的美、空气的清净、社会的混沌、正直的人被当作笨蛋之类可以说是完全心不在焉的话题。他们边分食着便当边拼命做出自己脑袋里面只有诗歌的幼稚表情,忍耐着晚秋的寒冷。到了下午三点,男方终于也高兴不起来了:“回去吧?”他说道。
“好啊。”她说着,接着又无意间补了一句,“要是有能够一起回的家,那该多幸福啊。回到房间,生个火……就算只有三叠一间……”
不能笑他们,毕竟恋爱中的对话必然如此陈腐。但这话正如一把短刀,连刃带柄地整把插进了年轻的他的胸膛。
房间。
阿鹤住在世田谷的宿舍,与另外两位同事挤在六叠一间的小房间里,小森则借住在高圆寺的叔母家。从公司回到家,都还可以看见女侍们忙得鸡飞狗跳的一幕。阿鹤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在三鹰开了间小肉铺的男人,而她家二楼有两间房间。
阿鹤那天将小森送到吉祥寺车站后,为她买了前往高圆寺的车票,自己则买了张前往三鹰的。两人混入月台上的人海,他悄悄地握了一下小森的手道别——他带着想去找房间的决心,握了下去。
“啊,欢迎光临。”
店里只有一个小学徒,正在磨着切肉的剁刀。
“姐夫呢?”
“出门了。”
“去哪了?”
“商谈。”
“大概又是去喝酒了吧?”
这位姐夫堪称酒中豪杰。他乖乖在家里工作的时候比较少。
“姐姐总在了吧?”
“嗯,大概在二楼吧。”
“那我上去找她一下。”
一上去,只见姐姐抱着今年春天刚生的女孩子,侧躺着喂着奶。
“姐夫说我要借的话就借给我。”
“他搞不好是那么说过,但只靠他那句话不算数啊。我这边也有我自己的账要解决。”
“怎样的账?”
“没必要跟你说吧。”
“拿去借给街娼?”
“大概吧。”
“大姐,我这次可是要结婚了,所以拜托借我点儿钱吧!”
“你一个月薪水才多少啊?自己都没办法养活自己了,你知道现在一间房间要多少钱吗?”
“就,就让女方也出一点……”
“你也照照镜子好不好,根本就是去养别人老婆的吧!”
“算了,不借也罢。”
他站了起来,从二楼下来,却又无法就这样真的放弃,反倒是心中的一股憎恶燃起。于是,恼羞成怒的他拿起了店里的一把剁刀:“姐姐说她要用,借一下。”
他抛下这句话,奔上了楼,然后,下手了。
姐姐无声无息地倒下,血溅了阿鹤满脸。用房间一角的婴儿尿布将脸擦干净后,他呼吸紊乱地下了楼,并将放在小盒里的肉铺营收——数千日币一把抓起,塞进了外套的口袋里。店里那时刚进来了两三个客人,小学徒匆忙地对他说:“要回去了?”
“嗯,帮我跟大哥说声好。”
他走出了肉店。薄暮的时刻雾霭弥漫,下班高峰期更是让街上人山人海。游过人海前往车站的他,买了到东京的车票,而在月台上等上行电车的这段时间是如此漫长。“哇!”他不禁想要这么呼喊。恶寒、尿意,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其他人的表情在他眼里,全都一派舒缓安详。在微暗的月台上,他远离人群一人站着,呼吸还是静不下来。
虽然其实他只等了四五分钟,但他总觉得已在月台上耗了半个小时。电车来了,人潮汹涌。他搭上了车。电车上,人的体温,还有那整个钝重的速度感,让他想在电车上拔腿狂奔。
吉祥寺、西荻洼……好慢,真的好慢。顺着电车窗户的裂痕,用指尖追寻那波状的裂线,抚摸之下,阿鹤不禁露出了悲伤且沉重的叹息。
高圆寺车站到了。要下车吗?他一瞬间晕头转向,想要见小森一眼这个念头让他浑身发热,连杀害姐姐这一事情都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萦绕在他胸中的遗憾,不过就是没能好好租到一间房间。两个人一起从公司回来,生个火,相视而笑,吃晚餐,听广播,睡觉。对正在热恋中的年轻人而言,杀了一个人所带来的恐惧,跟没办法租到这样一间爱巢的遗憾比起来,在他心里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当内心动摇的他总算踏出了朝向电车门口的那一步时,车子从高圆寺发车了,车门也应声关上。
他将手探入外套的口袋中,摸到了大量的“纸片”。这是什么呢?他在下一秒才猛然想起,这是钱!于是他的心头又暖了起来——既然如此,就玩乐吧!阿鹤毕竟是个年轻的男人。
他在东京站下了车。今年春天,跟别的公司打棒球赛获胜时,上司曾带阿鹤前往日本桥一间名为“樱”的待合,在那里遇到了一位花名为“雀”、比阿鹤还年长个两到三岁的艺妓。在这家店接到风化场所歇业令前,他又陪上司去了一次“樱”,见了雀一面。
“就算这家店歇业了,只要您来的话,任何时候都能见到我。”
阿鹤想起了这件事,于是晚间七点,他就站在了“樱”的玄关前。他冷静地告知自己所从业的公司名,并双颊微红地表明自己有事要找雀。侍女们毫不怀疑,引他上了二楼内侧的房间,而他也立刻换上了宽松的丹前。
“能洗个澡吗?”他问道。
“请往这边走。”女侍为他带路。而就在这时:“单身还真是麻烦,我想顺便洗衣服。”他用稍为羞赧的表情说着,并抱起还有一点血迹的白衬衫与襟巾。
“那我们帮您洗吧?”
女侍这样说之后,他极其自然地拒绝了:“没问题,我习惯了而且洗得很好。”
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血迹洗掉。洗完衣服后他剃了胡子,成了一个干净的好男人后又回到了房间,将洗好的衣服挂在衣桁上。仔细地检查过其他衣服有没有沾上血迹后,他接连喝了三杯茶,躺在房间里闭上双眼却无法入眠。当他缓缓起身的时候,穿得像个艺妓初学者的雀来了。
“哎呀,好久不见。”
“能不能买点酒来?”
“当然没问题。威士忌好吗?”
“都好,总之帮我买来吧。”
阿鹤从外套的口袋里抽出一张百元钞,抛向雀。
“不用这么多吧?”
“把能买的都买来,不就好了吗。”
“那我就先收下了。”
“顺便也买点烟吧。”
“要什么样的?”
“淡烟就好。手卷烟就免了。”
雀刚一走出房间就停电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中,阿鹤不禁感到恐惧。他好像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但是其实那是他的幻听。他也听到有人蹑手蹑脚地走过走廊,但那也是他的幻觉。阿鹤有点喘不过气来,想要大声哭出来,却又一滴泪都流出不来。但胸中的鼓动又是如此异样地剧烈,双腿像是被抽了神经一样疲软无力。他再度躺了下来,用右臂按在眼上,泫然欲泣的他小声说着:“小森,对不起。”
“晚上好,小庆。”阿鹤,姓鹤田,名庆助。
阿鹤确实听到了如蚊声的细细女嗓。他寒毛倒竖,惊坐而起,拉开纸门,奔出走廊。走廊也是一片黑暗的静寂,只有远处幽幽传来的电车声。
楼梯下出现了微微的光明——举着一盏小油灯的雀现身了,她看着阿鹤,吓了一跳:“哎呀,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小油灯那摇曳的光辉让雀的脸看起来好丑。小森,我好想你啊。
“一个人,很害怕。”
“做黑的,还怕黑呀。”
阿鹤知道,雀似乎一直都觉得自己身上的那些钱是做些黑心事赚来的,这个玩笑让他心情轻松不少,开始有心想喧闹一番。
“酒呢?”
“请侍女帮忙买了,她们说等会儿拿来。最近要弄点东西来都很麻烦,真讨厌。”
威士忌、下酒小菜和香烟。侍女悄悄地把这些东西送来。
“那么,还请静静地喝吧。”
“好。”阿鹤此时倒像是一位高僧般,泰然地笑着,答道。
其下波涛青于绀碧
其上阳光灿灿如金。
然,
不知休憩之此帆
正如于风暴中方有平稳
仅切求狂澜怒涛也。
呜呼,于风暴中方得休心!
阿鹤并非俗称的文学青年,而是个相当温暾的运动员。不过他的情人小森总是随身带着一两册文学书在自己的手提包里。今天早上在井之头公园约会时,她也念了一位名叫莱蒙托夫——二十八岁就因决斗而逝去的天才诗人的诗集给阿鹤听。虽然阿鹤对诗歌一类的东西毫无兴趣,但对这本诗集里面的诗情有独钟,特别是《帆》这首既年轻又乱来的诗,更是完全直击了他现在正在热恋中的心。他让小森一次又一次地朗读这首诗。
于风暴中方有,平稳……于风暴……中……
阿鹤就这样让雀在小油灯的灯光下陪酒,喝着威士忌,渐渐乐于酒醉之中。晚上十点左右,房间的电灯“啪”的一声亮了起来,不过这时无论是电灯的光还是小油灯的光,阿鹤都不需要了。
破晓。
黎明。亲眼见过日出的人一定会知道那种感觉吧!日出以前的薄明绝对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东西,反而像是神明所击打出的那一阵阵愤怒的太鼓声。跟日光完全不同的某种光,那黏稠稠的红豆色的光,将树梢染上了一层血的味道。这还不如说是一种悲惨且令人鼻酸的感觉。
阿鹤于茅房的窗户望见了秋天破晓的震撼,胸口竟因此疼痛不已。他像是个死人般脸色惨白、步履蹒跚地回到了房间。他在张嘴熟睡的雀的枕旁盘腿坐下,痛饮昨晚剩下的威士忌。
钱,还有。
酒劲开始涌上来,阿鹤钻进被窝里抱住雀。他边躺着边喝酒,边烂醉如泥地浅睡。然后又醒来。再度被迫认清自己现在可真是算盘怎么打都不对的穷途末路。他的额头上满是黏汗,心里痛苦,又要雀去买了一罐威士忌,喝了,抱了雀,又醉成一团地睡了,接着,醒了,再喝。
就这样到了太阳要下山的时候,酒杯凑到嘴旁阿鹤都想吐。
“我要走了。”他说道。
连这句话他都说得十分痛苦。本来还想再多说点幽默的小笑话,但他发现只要一开口就想吐,只好默默地爬着拉取自己的衣服后,在雀的帮忙下打点好自己的装束,边不断与自己的呕吐欲抗争,摇摇晃晃,头昏脑涨地走出了日本桥的待合“樱”。
外面已经是近冬的黄昏。从那之后已经过了一整夜。阿鹤钻进桥头正在买晚报的人的队列中,买了三种不同的晚报,从头到尾、从里到外看了一遍。没有!没有!反而更令人不安了。禁止报道!这一定是偷偷在追捕犯人。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多少钱就逃多久,最后自杀吧。
阿鹤一想到自己被逮捕,然后血亲、同事们朝着自己或发怒或悲泣,或疏远或痛骂自己这个下场,就感到一阵厌恶且极度地恐惧。
可是,他累了。
而且,还没上报。
阿鹤鼓起勇气,前往位于世田谷的公司宿舍。总之,在自己的窝里好好地睡上一晚吧!
宿舍的房间是六叠一间大,阿鹤跟两名同事一起住。室友们大概是上街寻花问柳了,都不在。大概是因为附近有主要的电力管线经过,所以这间房间也偷接了电灯。在阿鹤的桌子上,有株被放进杯子里的菊花,花瓣有点发黑的它,一直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阿鹤默默地铺了棉被,关了灯,睡下。但他立刻又起了身,把电灯打开,再度躺下,接着用一只手遮住脸,小声呻吟着。最后,他如死了一般睡去。
早上,他被其中一个同事摇了起来:“喂,阿鹤,你到底闲晃到哪去啦?你三鹰的姐夫打电话来公司好多次,我们都快烦死啦。他说如果阿鹤在的话,请他赶快来三鹰一趟,大概是有什么人突然生病了吧。但是你没来上班,也没回宿舍,小森也说没看到你,总之你今天先去三鹰一趟吧。你姐夫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出大事啦。”
阿鹤瞬间觉得全身寒毛倒竖。
“只说了‘快来’没说别的吗?”
他整个人已经弹了起来,开始穿裤子了。
“嗯,好像很急,你还是快去吧。”
“我去去就回。”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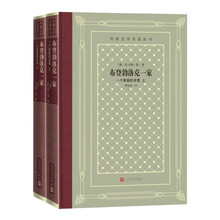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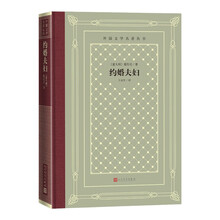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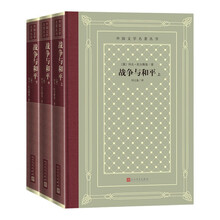



——高尔基
我很喜欢太宰治。
——王家卫
倘若举办一场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各国要挑选一名代表选手的话,日本的代表,或许不是夏目漱石,不是谷崎润一郎,也不是三岛由纪夫,而是太宰治。
——井上靖(日本著名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