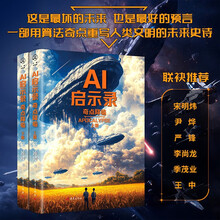序.章
他们落入陷阱,几近冻僵,潜藏着。四周都是森林,让人神经紧绷。慌乱之中,不时瞥见一点迹象——感到它们那刻骨的饥饿,看到一闪而过的血红眼睛——于是焦急地从树林的阴影里疾奔出来,跑到光亮之下。
她来了,很快就来了。
它们将再次自由地驰骋在荒原之上。巫猎将再次回归。
大地浸满鲜血。
葵茵
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比如火车开过来的时候站在铁轨上,又比如把手放在火苗上面。当然你可以很快地扫过火苗,还保持安然无恙,但是我内心里有种东西促使我把手在上面多放一会儿,然后再坚持一会儿,又坚持一会儿。火车轨道、妈妈,就和火苗一样:距离太近,时间太长,就会产生痛苦。
如果让我坐下来列举一下所有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排一个序,从z不应该做的事情开始,那么今天到这里来恐怕要名列榜首,但是,我总是被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所吸引。也许是来看个究竟,看谁会受到伤害,也许吧。
因此,不管我内心那个理性的声音怎样劝阻我,不管我怎样努力地劝说自己,故意丢掉公交车票,故意打扮成古里古怪的样子,我都不可能去别的地方,不是吗?
距离有多近,时间有多长,现在都不重要。现在,我在殡仪馆旁的一座小山上,坐在一棵枯树下瑟瑟发抖,灰暗的天空中有一大片血一样的火红。我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开始下起雨来了,这让我感到高兴。她不喜欢雨。别人不喜欢雨,可能是因为他们被淋成了个落汤鸡,也可能是因为搅了他们在花园里的聚会——但她不一样,她就是很单纯地不喜欢雨。就仿佛她不是由筋骨和肌肉而是由某种特殊材料造成的,一淋雨就会被整个儿冲坏了。
又或许她害怕雨的原因,是怕自己的面具被冲没了——那个满面笑容地和我从未见过的一个男人一起出现在报纸上的面具。满面笑容?不知道她在棺材里会不会还是满面笑容,他们会不会把她的五官装扮成一副令人开心的模样。也许他们希望,这副模样会让那些掌管生死的人为她打开天国之门,而不是将她一把推进深渊。又或许,她的脸部没剩下多少了。
车队开始蜿蜒驶上道路。首先是一辆长长的黑车,后面载着棺椁。车停在殡仪馆前,雨仿佛有知觉一样,下得更大了。伴随着雷声,闪电撕裂了天空。
我在整个队伍的后面逡巡着,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不知道该靠到多近的距离去看着她被火化。暴雨仿佛帮我下定了决心。它仿佛在说:“葵茵,往前去。你得为自己找一个避雨的地方。”
但这只是个借口而已。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她已经死去。
珮珀
我侧身下车。风呼号着把我手里的伞一下子吹得翻了过去。冰冷的雨滴猛烈地打在我的脸上、手上。狂风一瞬间就把我精心梳理的头发吹成一团乱麻。风雨仿佛带着怒火,狠狠地敲打着我的皮肤。我用全部的注意力来感受这种疼痛,努力把其他所有的苦痛都放到一边。
爸爸冲了过来,在我们头顶上撑起一把伞。但是我心里想的却是这雨敲击在她棺椁上面会是怎样的情形。棺材里面会有回声吗?她会不会捶打棺盖,大声抗议:“嘿,赶紧停下来好不好?”她一直生活在阳光里,肯定不希望自己z后一次出门是这样一种状况。
抬棺人迈着仿佛计算好的小步,全然不顾刺骨冷雨的侵袭。我却在心里呐喊着、咆哮着,希望他们快一点儿,快一点儿把她带到没有雨的地方去。爸爸伸出手来,我紧紧地攥住,他的手冰冷冰冷的。我们跟着棺椁——跟着她,跟着妈妈——走进屋里。
一见到我,我的一位婶婶就开始摸着我的头发唠叨起来,然后把我拉到整个队伍的前面。但对这一切,我都没有任何感觉。
我在心里默念着那句陌生的话,“我妈妈死了”。我的世界再不像从前了,一切都不像从前了。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但内心并不明白这其中的意味。棺椁被放在前头——上面一点儿都不湿。有人擦干它了吗?她就在里面,但那里面的并不是真正的她:只是她遗留在这个世界的东西。
这些事情,我都看在眼里,但是我心里一点儿准备都没有。
我内心z深处在摇晃,恐慌一点点地累积。我很想大喊:“你们都停下来,这都不是真的!你们不要在那里装模作样了。”
这不可能是真的。
“冷静下来,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他们都认为这是真实的。我从他们的眼里能看出来——他们要么望着我,要么一与我的眼神触碰就转头看向别处。
“深呼吸,珮珀。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我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不能在这里崩溃,现在不能崩溃。
做点儿别的事情。
我转过身去,望向身后那些人,对他们大多是一扫而过。爸爸的亲戚、同事,还有他和妈妈共同的朋友。人并不多。但是妈妈娘家那边一个人都没有来。她过去的朋友也一个都没有,我指的是她生我之前,也就是十七年前。
还有一堆我学校的朋友。扎克站在他们不远处——有一段距离,但并不远。他坚定的眼神,让我想起他昨晚对我说的话:“我会一直在这里,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做的,尽管说,我一定做。不管什么事情。”看到他的眼神,我感到一些安心,就如昨晚一样。恐慌的情绪稍微平息了一些,但这就足够了。
葬礼仪式马上就要开始,这时后门打开了,牧师停下来等待。是谁来晚了?我听到后面一位婶婶发出一声不满的“哼”。我小心翼翼地回头看去。那人身形很瘦弱,是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女孩,靴子上沾满了泥。她快速朝后排座位走去。头上围着一条彩虹色的围巾,低垂在她脸旁。
她会是谁呢?
难道是……
“不。绝不能这样。尤其是此时此地。”
我的脉搏加快跳动起来。
葵茵
雨水顺着我的大衣流到我的靴子上,然后淌到地板上。头上的围巾已经湿透,我冷得瑟瑟发抖。
我坐下的时候,瞥到前排一个姑娘转过头来。她的头发很长,一半扎着,另一半被风雨吹散。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她头发的颜色——深红色,如火一般。
如火一般的深红颜色——和我的头发一样。
我内心一片死寂,所有的一切都静止了。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大口呼吸,将空气吸到肺里。
我之前没有料到会这样。我本应该能想到的,不是吗?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像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母亲样子的人,完全不知道如何当母亲的人,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给过我母爱,只是时不时拿着一根棍子到我这里搅和一下的人,竟然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个女孩旁边的男人应该是报纸新闻里的那个人。我把手伸进兜里。报纸湿漉漉的,上面的字有一些变形,但实际上我都能背下来了:
女子惨死狗口
上周五晚,来自温切斯特的36岁女子伊莎贝尔·休斯,在遛自家的狗时,突遭群狗袭击,后因伤不治死于医院。攻击她的是4条狗,它们均为早先从附近训练场逃出的护卫狗。这4条狗现已被羁押,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如果没有照片,我根本就不知道死者会是她。她也叫伊莎贝尔,但我一直以为她和我还有外婆一样,都姓布莱克伍德。
伊莎贝尔·休斯死后上了全国新闻,还引发了一场关于护卫狗以及恶狗管控的大讨论,这个结局是够可怕的。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母亲竟然已经死了。她不经常来看望我,看望的间隔时间完全没有规律可言。我猜想她可能是嫌麻烦,我也懒得去想。底下照片里的男人是她老公,雨水把他的样子弄得有些模糊了。我对比着前面那个男人,仔细地研究照片。终于,他稍稍转了一下头:就是他了。她老公?他看起来比伊莎贝尔要老二十岁。但是,报纸上的新闻里根本就没有提到他身边坐着的那个女孩,那个头发颜色和我的一模一样的女孩。
终于,默祷结束了。我心里想着,如果她能转一下头,我就能看到她的样子,但是很快其他人都站了起来,挡住了她,我只瞥见了她那红色的头发。
尽管头巾都湿透了,但我仍然紧紧围着。这一切都不正常。我要离开这里,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但是她还有那个和她站在一起的男人——我估计应该是她的爸爸,至少她还有个爸爸——此时已走到门边。他们的脸背向我坐着的地方。人群从他们身边走过,每个人都停下来和他握手,然后拥抱一下她。那么多人和蔼地望着他们,说着好听的话。那么多人在关心着他们。刚开始那一批人,看起来像是他们的亲朋好友。然后是一长列的少年,年纪和我都差不多,有男孩也有女孩。他们人非常多,肯定是那个姑娘的朋友。每个人走到她跟前,都会说上一两句话,做一两个手势,或是轻轻握一握她的手。然后来了一个年纪大一些的黑头发男孩,个子高高的,他一直躲在后面,等其他人先行,z后才走到她面前。他拥抱了她,很快地吻了她一下,然后握住她爸爸的手,俯身向前说着什么。她爸爸抬手擦眼,旁边有人递过一块手帕。
来之前我还在想,今天我来参加葬礼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伤害到谁,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到头来受伤的竟然会是我自己。我一直紧咬牙关,将痛苦都打成死结,痛苦之中却总是缺失了些什么——但究竟缺了什么呢?那些我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总是如此遥不可及。
我完全做不到,明明知道很多事情,却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走到他们面前,和他们握手。我在座位里缩着身子,希望自己躲进角落,谁都看不见。
声音逐渐远去。门也咔嗒一声关上。他们真的就这样把我留在这里,不来烦我?
然后,一阵咔嗒咔嗒的脚步声慢慢传来,在我面前停止了。
“你好?我们认识吗?”是一个女孩的声音。在这样一个灰暗的日子里,这个声音有如音乐,温暖而急切。
我转过身去,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完全知道是谁在说话。
一道光从高耸的窗户外射进来,照在她火一般的头发上。她好奇地睁大着眼睛——这是一双清澈的、蓝灰色的眼睛。这种眼睛会随着光线、她的心情,还有她的衣着而改变颜色。我之所以了解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的眼睛也是如此。她的肤色很浅,高高的颧骨上有一片淡淡的雀斑。我也有这样的雀斑,我也有这样的颧骨。看着她,就好像我在照镜子一样。
那些我不经意间听到的、神神秘秘的话语——当时我不明白,现在突然有了意义——在我脑子里翻滚,相互撞击。我感觉脑袋轻飘飘的,喘不上气来,要费很大劲儿才能呼吸。
“你没事吧?”她问道,“你要不要看医生?”
我站起来,一甩头把围巾取了下来,然后走到光亮处。
珮珀
我仿佛是在照镜子一样。就连把左边头发拢到耳朵后面,让右边头发顺着脸庞垂下来,也和我平常的做法一样。她眼睛里满是惊异。难道她不知道?
“我们是双胞胎。”我轻声说道,语气里带着惊喜。
她咽了一下口水,舔了舔嘴唇,“我不知道……我是说……怎
么会……”
我伸出手去,“我叫珮珀。”她盯着我的手。“你叫什么?”
她仿佛受了惊吓。“葵茵。我的名字叫葵茵。”她伸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像冰一样冷,很快就又缩了回去。
我回头望向门口。“爸爸可能很快进来找我。我们俩不能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现在还不行。”
“永远都不会。你放心吧,我马上就走。”葵茵答道,她局促不安地挪动着双脚,看起来吓坏了,但我不能让她就这样突然消失掉——尤其是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现在不行。
以后也不行。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求求你。求你再待一会儿。我会让扎克来接你,然后——”
“不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她在往后退缩。
我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希望能伸出手去碰一碰她,抱住她,但是我又害怕她会拒我于千里之外。“你不能这样。求求你了。我不想失去你。不想再失去一个亲人。”
葵茵犹豫了,“你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我们的共同点只是长得像而已。”
泪水滑下我的脸颊。“我们还有同一个妈妈。我们刚刚失去了她。请你不要走。”
“我根本不了解妈妈,”她扫了一眼棺椁,“她真的……真的……”她眼里的怀疑,让我终于把我自己也不相信的事实说了出来。“我们的妈妈真的死了吗?好吧。你想不想看一看她?”
“什么?”
“如果你想看,我可以安排。但是答应我,你会留下来等我,就在这里。不要离开。”我的眼睛里满是恳求。
她的眼里则都是挣扎。她盯着门口,然后叹了一口气,z后点点头。“好吧。”
我感到一阵轻松。
葵茵
她出去后,门关了起来。
你想不想看一看她?她刚才真的是这么说的吗?我硬生生地转过身去,盯着前面摆放着的棺椁。现在大家都走了,房间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棺椁的体积看起来更大了,仿佛占据了整个空间。我的眼睛紧紧盯着棺椁发亮的木头表面。看得久了,仿佛棺椁在长大,在拉扯我,淹没了我所有的感觉,仿佛离我越来越近。然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是我在不自觉地、犹犹豫豫地向它走去。
向她走去。
我想不想看一看她?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确定她已经死去。我的嘴巴发干,努力想咽一下口水。
她随时有可能回来——那个珮珀。我们是双胞胎?珮珀刚说过。尽管我亲眼看到了她,发现我们长得一模一样,但我仍然不敢相信。我怎么可能有一个双胞胎姐妹,之前却完全不知情?我们完全一样,至少外表如此。伊莎贝尔自己是不是也分辨不出我们谁是谁?
也许这就是我们被分开的原因。我感觉自己仿佛刚从一场梦中醒来,终于知道了真相——如此难以置信,令人吃惊。从此将永远地改变我、颠覆我。但我不敢深思,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或者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因为随便一个人打开门,闯进来,就会发现我。如果他们发现我准备碰这里的棺椁,肯定会把警察叫来。或者更糟糕,他们会仔细地看着我,发现我和另外一个人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把我的故事卖给当地小报。我在宾馆工作时,曾见过这种小报。报纸上会出现这样的标题:双胞胎孩子在母亲葬礼时首度会面!当然,严格说来,这并不是我们首次见面。至少在我们出生时,我们曾一起吸进人生的第1口空气。在那之前,我们还相互蜷缩在一起,在同一个子宫里度过了九个月的时间。
她的子宫。
对了,还有珮珀的父亲。如果我们是双胞胎,那我们肯定拥有同一个父亲。那个人也是我的父亲吗?
我身后的门打开了,我立刻转过身去,想着这时候用围巾来遮住自己的脸是不是已经太迟,结果进来的是珮珀。
她朝我走过来,停在我跟前。她上下打量着我,我也一样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仔细观察,看每个细节,每条曲线,每处特征,希望找到一点儿不一样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她比我稍微高一些,但紧接着我低头看到她的鞋跟比我的靴子跟要高那么一点儿。
“没关系的,”她语气平静地说道,“没有人会打扰我们。我告诉他们想和妈妈单独待一会儿。而且,扎克在门口守着呢。他不会让任何人进来的。”
“扎克?”
“我男朋友。来吧。”她向棺椁走去。她的肩膀挺得很直,仿佛在准备做一件大事。我突然意识到,不管那个女人是我的什么人,对她来说却真的就是妈妈。
“你用不着这么做。没有关系的。”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挑起了左边的眉毛。这个动作我也经常做,是一种挑衅的动作。“你也用不着这么做,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下意识地像她那样挺直了肩膀,然后刻意地放松下来。我朝前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和她并排站在棺椁旁。
她是被恶狗袭击致死。她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珮珀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她摇了摇头。“大家之前看过她。殡仪馆的人已经都整理好了。”
棺盖上有两个把手。珮珀抓住棺椁尾部的那个把手,然后瞟了一眼另一个把手,在头部附近。“你可能得帮把手。”
我伸手抓住另一个把手,冷冰冰的,一种光滑的金属触感。
“准备好了吗?”
她低声问道。
我的胃抽搐了一下。我很想说没好,没准备好。我永远也不可能准备好。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她也点点头。我们一起朝上用力。
棺盖是实心的,很重,但是很容易举起来。我们把棺盖慢慢举起来,然后放到一边。棺椁打开了。
我看不到珮珀的眼睛,她正盯着里面。
“我让你独自待一会儿。”她说道,然后转过身子,同时强迫她自己转过头去,仿佛只有这样她才能不盯着里面。然后她走远了。
我看了看地板和墙壁,然后看着我的手——不敢正视棺椁里面。我以前见过死亡,在路边见过,也见过猫咪带回来的死老鼠和死鸟。还有几年前,一只狐狸钻进了鸡棚——那简直就是一场大屠杀。我打扫完鸡棚后,好几个月都做噩梦。她会不会像一只被狐狸虐杀的鸡仔?
我硬下心肠,准备深吸一口气,但立刻停了下来。她会不会有味儿?她死了有多少天了?但是没有味儿。珮珀说过,殡仪馆的人已经都处理好了。不管他们做了什么,肯定能让她安然度过葬礼。
我强迫自己转过脸去看,先看她的脚可能会安全一些。她穿着一条长长的、厚厚的裙子。蓝色的——这是她z喜欢的颜色吗?我努力回想着。她来的次数不多,确实经常穿蓝色,但是我对她了解得实在太少了,无法判断这是不是她z喜欢的颜色。或者她穿这件裙子,是为了把恶狗留下的伤痕都遮盖起来。
我的眼睛往上看去。她的手仿佛是交叉放着的。一只手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另外一只藏在衣袖里面。我咽了一下口水,强迫自己继续朝上望去。这件裙子的领子很高。难道恶狗把她的喉咙咬破了?如果狗和狐狸一样,它们肯定会咬喉咙。
现在——时间到了。
得看她的脸了。
她看上去很放松,很安详。如果你不靠得太近,可能会以为她是睡着了。颧骨高耸,上面是长长的睫毛。头发是赭色的——不是珮珀和我的头发这样的亮红色——披散在肩上。她很漂亮。我现在能看得比较清楚了,因为她没有像往常看我时那样,皱着眉头,满脸的怀疑,完全看不出她正常的模样。
尽管她闭着眼睛,但是没错。就是她。她真的死了。
她的脸上敷满了粉。她的肤色很白——以前就很白,和我一样,但是她颧骨上的红色太过浓重,甚至有点小丑的感觉。底粉很重,看不出来有任何高低起伏,仿佛有些地方是填进去的。我一阵颤抖。四条恶狗,新闻里面是这么说的吧?它们肯定是把她扑到地上,然后发起了攻击。没有命令这些狗是不可能主动攻击的,它们的训练师曾经这么说过,然后遭到了起诉。他搞不懂怎么会这样,更不知道这些狗是怎么跑出去的。但不管怎么样,它们跑出去了,然后咬死了她。
以前,我在生气的时候,曾经想过这样的场景,想过很多次——想着要是她死了就好了。但当现在真的看着她的尸体,我感觉到一阵恶心,她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想起这一点也让我感觉很难受。
她真的死了。
我的身体在颤抖,内心感到窒息——仿佛什么东西停止了。
身后传来脚步声,慢慢走近。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来,得走了。”声音很轻柔。
我们把棺盖移到棺椁上面,然后盖上。我看着妈妈的脸慢慢消失,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站在原地,手仍放在把手上,无法移动。
珮珀的手很温暖,很轻柔。她把我的手指从把手上挪开,把我的头发塞到衣服里,然后仔细地将头巾从我脑后慢慢围到前面,在前面打了一个结,头巾被拉得很低,罩在脸上,这样别人看不到我的脸。她对我眼里不争气地打转的眼泪不置一词。
为什么会流泪?我也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这么在乎?那个女人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的事情。我在害怕、孤独的时候,她从来没有出现过。六岁时我摔断胳膊的时候,她没有出现。后来,当我病倒发烧,因为幻觉吓得大叫,以为如果高烧没有杀死我,黑夜怪物也一定会把我撕成碎片,那个时候她也没有出现。
她从来没有爱过我。
但更糟糕的是:她以后永远也无法爱我了。
珮珀
现在她很安静,也很听话。我告诉她等一会儿的时候,她什么话也没有说。是不是看到妈妈,会让你重新变回一个孩子,即便这个妈妈你根本就不熟悉?
尽管我下定决心不看妈妈,但还是忍不住。我很想盯着她看,牢牢地记住她。我想爬进棺椁里面,躺在她冰冷的身体旁边。也许我能靠我的温暖把她重新带回我的身边来。
我打开门。扎克在那里,如我所料。远处门边还能隐约看到其他人的身影。
他微笑着伸出手,我牵住他的手。“你爸爸在等你,”他说道,“你没事吧?”
“没事。你能帮我做件事吗?”
“当然。什么事?”
我把门打开了一些,好让他看到站在暗处的葵茵。“你能不能……”我欲言又止,不想在这么多人的环境里告诉他这个消息,怕他会有太大的反应。“你能不能把我的朋友带到你家里,等我守完夜就过去找你们?”
看到她,他吃了一惊。“我以为就你自己在里头呢?”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可不可以?”
“当然。”扎克俯身拥抱我。我倚在他怀里,满心希望自己也能和他们一起走,而不用烦心其他的事情。我现在想的只是能和葵茵待在一起:一个能与我一同承担的人。仿佛和她在一起,看着她的脸,就能让这一切都远离自己。
我叹了一口气,抬头看着扎克。“等我们离开了你们再走,
好吗?”
他眼里满是疑问,但他只是点了点头。“好吧。没问题,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回答道,“我会把她带到我那里去,然后我再到你家里跟你会合。”
我皱了皱眉。“不要。你z好和她待在一起。叫她等着我。”虽然她现在状态还可以,但是我不敢保证等这股震惊的情绪过去之后,她会不会又突然消失。
“什么?那可不行。我要来找你。我要和你待在一起,就跟你以前做的一样。”
我摇了摇头。“听我说,扎克。现在你能帮我的z好方式,就是照我说的去做。把葵茵带到你家里,然后和她待在一起。”我朝她那边指了指,她沉默不语地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另外一个方向。“我会尽快赶过去的。好不好?”
他盯着我的眼睛。“我搞不明白,但如果你希望我这样做,那好吧。”
“是的。就这样办吧。”
“我不在你身边,你家人会觉得奇怪的。”他转了转眼睛,我知道只要我家人不给我制造任何麻烦,他是不会管他们的想法的。
“我会告诉他们你有点不舒服或别的什么原因。不用担心。”
他耸了耸肩膀。我朝门外望去。爸爸在往我们这边看,他等不及了。“我得走了。我会把他们带到外面去,好让你们悄悄离开。”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