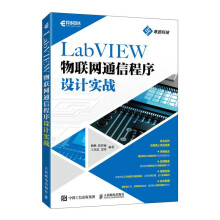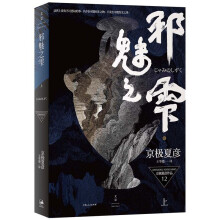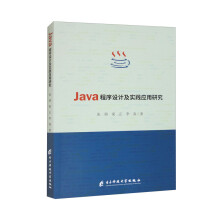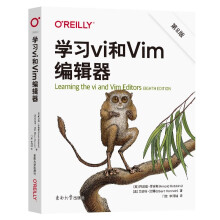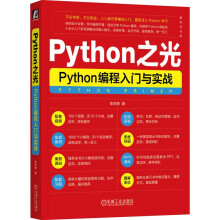《王阳明与其及门四大弟子的情论研究/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一 良知的先后天问题
良知的先后天问题发端于阳明。《周易·乾卦·文言》在描述具有理想道德人格的“大人”的天人合一境界时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对此阳明以良知学进行了解释:“‘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即认为良知属于《周易》所云先天的范畴,而良知的起用则能规范和规定经验后天。阳明有诗云:“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阳明以良知为圣学宗旨,为大规矩,认为后天的知识仪节等方圆都由此而出,良知的先天境界与后天日用常行是相即不离的。龙溪基本继承了阳明良知学先后天的判教:“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学虑而得,先天之学也。知识则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于多学臆中之助而已,入于后天矣。”在王畿看来,利欲、意见乃至知识等都属于后天的范畴,因为都要借助于外在的事象或形式规范而存在,只有作为本心之灵明的良知才是人先天本有的,只要主体自信自肯即能当下呈现之。王畿进一步将先后天的范畴运用于对致良知工夫种类的划分,认为致良知的工夫有先天正心之学和后天诚意之学的区别,并自认己学为先天正心之学。
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乃是借助于《周易》的“先天”和《大学》的“正心”观念来论致良知工夫,其所谓先天正心工夫有着独特内涵。其一,先天良知具有超越日常经验和语言思维的特征。面对弟子对良知秘诀的叩问,王畿这样回答:“苟能发心求悟,所谓密在汝边,凡有所说即非密也。”他认为良知秘诀并非经验描述或文字言说所能传达,只有超越于经验言诠的心之觉悟才能体证其真谛和精蕴。良知作为“先天之学”具有超越言诠的特征,凡语言文字与理论阐释如同禅宗以指见月一般,对于学人悟人心体只能起指点和启发的作用。其二,王畿先天正心工夫简易直接,可以由心体立根而径直启动良知,故无须过多地纠缠于经验情感和意识。在他心目中,颜回的“不远复”就是这种简易工夫的代表:“颜子心如明镜止水,纤尘微波,才动即觉,才觉即化,不待远而后复,所谓庶几也。”如果任由经验意识形成习惯性动作,就会产生善恶的分别与执着,这样工夫反而离良知日远。王畿以为只有经验情意的每一次发动时刻顺应本正的良知心体,这样工夫才能始终在心体上立定脚跟而自作主宰,经验情意的生起也能时时化入良知。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立根于良知本心,具有超越性和直接性的工夫特点,主张以超越世情的态度把现实社会人生善恶混杂的种种人情世态、万握丝头一起斩断或消融,这需要学人极度自信并发挥良知本心的力量才可达成。
在王畿看来,先天正心之学与后天诚意之学乃两种截然不同的致良知工夫路径,前者简易直接而后者繁难曲折。就良知践履而言,先天工夫要靠主体当下一念之自觉而返回和把握自身的良知心体,后天工夫则主要着意于经验情意的对治与澄清。依先天工夫,一悟良知则心体自然流行,如此则不必直接面对物欲俗情的牵扯和缠绕,这样的工夫没有固定的模式和刻意之作为,不需要后天外在法则的严格约束,因为即使经验情意偶尔放逸也能像颜回一样“不远而复”,很快能够回归到先天良知的本体状态,这种工夫无疑简易而省力;反之,如果主要着意于后天经验情意的对治,只是从后天的伦理问题或道德规范人手,则难以避免纠缠不清和顾此失彼的状况发生,如此则物欲俗情可能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主体难免会受到情欲生灭的牵扰。王畿认为《论语》里面的颜回和原宪就是先后天工夫的典型代表:“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便是先天易简之学。原宪克伐怨欲不行,便是后天繁难之学。”颜回因为已经见到先天本体,故其知行实践有源泉和根据,即使偶尔行为不当或习气未化,也能随时洞察和消解之;而原宪则因不见本体,只是对心中的种种物欲俗情采取强行克治的态度,因而学无根本,终究还是难免意欲的纠缠。由此论证过程,王畿在工夫论上得出先天简易而后天繁难的结论。就理而言,先天工夫确实根本而直接,但在实践中由于学人根器的不同往往难以把握。因为良知觉悟绝非易事,学人也可能未悟言悟,从而产生混情识为良知的后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