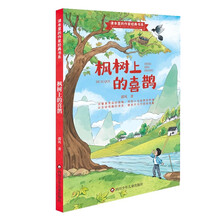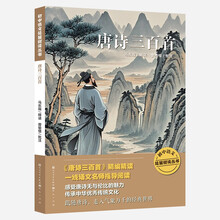《猎狐(升级版)》:
保姆蟒
我儿子生在边远蛮荒的曼广弄寨子,寨子后面是戛洛山,寨子前面是布朗山,都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寨子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大人上山干活了,比兔子还大的山老鼠从梁上翻下来,把睡在摇篮里的婴儿的鼻子和耳朵咬掉了;一头母熊推开村长家的竹篱笆,一巴掌掴死了看家的狗,把村长刚满周岁的小孙孙抱走了。村长在老林子里找了五年,才在一个臭气熏天的熊窝里把小孙孙找回来。六岁的孩子了,不会说话,也不会直立行走,只会像熊那样叫,只会四肢趴在地上像野兽似的爬行,成了个地道的熊孩……
我那时迷上了打猎,有时钻进深山老林追逐鹿群或象群,几天几夜都不回家。妻子挑水、种菜、洗衣服什么的,只好把还在吃奶的儿子独自反锁在家里。我们住的是到处有窟窿的破陋的茅草房,毒蛇、蝎子、野狗、山猫很容易钻进来,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找个保姆来带孩子,但我那时候收入微薄,养家糊口尚且不易,哪还有闲钱去请保姆。我和妻子都是插队来的知青,也不可能让远在上海的亲人万里迢迢跑到边陲来替我们照看小孩。
就在我犯愁之际,寨子里一位名叫召彰的中年猎人说可以帮我找一个不用管饭也不要开工资的保姆。除非七仙女下凡,田螺姑娘再世,上哪里去找这等便宜的事?我直摇头。召彰见我不相信,就说:“你们等着,我立马把保姆给你们带来。”
一袋烟的工夫,我家门前那条通往箐沟的荒草掩映的小路上便传来悠扬的笛声。又不是送新娘来,用得着音乐伴奏吗?我正纳闷间,召彰已吹着笛子跨进门来。我特意看他的身后,并没发现有什么人影。他朝我狡黠地眨眨眼,一甩脑袋,金竹笛里飞出一串高亢的颤音,就像云雀呜叫着飞上彩云。随着那串颤音,他身后倏地蹿立起一个“保姆”来。
我魂飞魄散,一股热热的液体顺着大腿流下来,脚下的地都湿了一块。不好意思,我吓得尿裤子了。
妻子像只母鸡似的张开手臂,把儿子罩在自己的身体底下。
召彰用笛声给我们带来的保姆,是一条大蟒蛇!
“快……快把蟒蛇弄走。召彰,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弄条蛇来害我们!”妻子嗔怒道。
“我敢用猎手的名义担保,它是一个最尽心尽职的保姆。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它帮着带大的。哦,假如它伤着你们小宝贝一根毫毛,我用我的两个儿子来赔你们。”召彰很认真地说。
“这……我一看到蛇就恶心,饭也吃不下。”
“先让它试十天吧,不合适,再退给我。”召彰说着,把蟒蛇引到摇篮前,嘴里喃喃有词,又在蟒蛇的头顶轻轻拍了三下。蟒蛇立刻像个卫兵似的伫立在摇篮边。
这时,我才看清,这是一条罕见的大蟒蛇,粗如龙竹,长约六米,淡褐色的身体上环绕着一圈圈、一条条不规则的深褐色的斑纹,这些斑纹越接近尾巴,颜色越深,是典型的西双版纳黑尾蟒;在下腹部,还有两条长约三四寸、退化了的后肢;一张国字形的小方脸,一条菱形黑纹从鼻洞贯穿额顶,伸向脊背;两只玻璃球似的蓝眼睛像井水一样清澈温柔;微微启开的大嘴里,吐出一条叉形的芯子,红得像片枫叶。整个形象并不给人一种凶恶的感觉,倒有几分温顺和慈祥。
或许,可以试十天的,我和妻子勉强答应下来。
十天下来,我算是服了召彰。我敢说,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这条蟒蛇更称职的保姆了。假如保姆这个行当也可以评职称的话,这条蟒蛇绝对是一级保姆,就像一级教授或一级作家一样。它不分昼夜、忠诚地守候在我儿子的摇篮边,夏天蚊子奇多,我们虽然给摇篮搭了个小蚊帐,但儿子睡觉不老实,抡胳膊蹬腿的,不是把蚊帐蹬开一个缺口,让蚊子乘虚而人,就是胳膊或腿贴在蚊帐上,让尖嘴蚊子穿透蚊帐叮咬。几乎每天早晨起来,我都会发现儿子嫩得像水豆腐似的身上隆起几只红色丘疱,让我心疼得恨不能自己立刻变成一只大壁虎,把天底下所有的蚊子统统消灭光。但自从这条蟒蛇来了之后,可恶的蚊子再也无法接近我儿子了,那条叉形的蛇芯子,像一台最灵敏的雷达跟踪仪,又像是效率极高的捕蚊器,摇篮周围只要一有飞蚊的嗡嗡声,它就会闪电般地朝空中蹿去,嘴里吐出火焰似的芯子,那只倒霉的蚊子就从世界上消失了。过去只要一下雨,免不了会有竹叶青或龟壳花蛇溜进我家来躲雨。有一次,我上床睡觉,脚伸进被窝,怎么凉飕飕滑腻腻的,像踩在一条冰冻鱼上,掀开被子一看,一条剧毒的眼镜蛇,盘踞在我的脚跟……这条蟒蛇住进我家的第二天,老天爷就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我亲眼看见有好几条花里胡哨的毒蛇窜到我家的房檐下,在墙洞外探头探脑,但一感觉到蟒蛇的存在,就立刻反身仓皇逃走了。至于老鼠,过去大白天都敢在我家的房梁上打架,一人夜背光的墙角就会传来吱吱的鼠叫声,但自打我们请了保姆蟒,嘿,老鼠自觉搬家了,请也请不回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