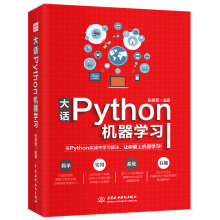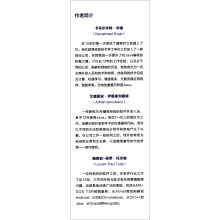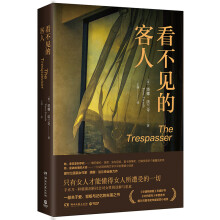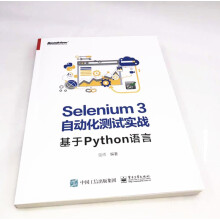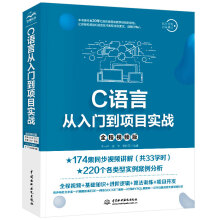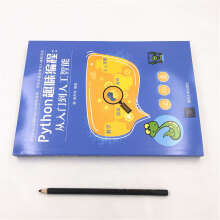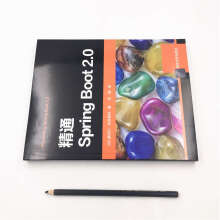上篇 基于要素视角的综合评价基本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综合评价的基本问题与认识
一、综合评价的基本问题
(一)综合评价的发展
1.综合评价思想的发展
广义地讲,一切基于多个因素来综合判断评价对象水平或状态或类型的认识过程,都可认为是综合评价活动。从这个角度讲,综合评价的思想与实践自古有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也就从哪里开始”(章士嵘,2002)。
早在商周时代,无论是知人用人,还是察事考绩,抑或是观景品物,古代的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医学家都不乏从多个因素进行综合评判的理念或做法。《庄子 杂篇 列御寇第三十二》中提出了九种知人之法,先秦时期《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以测评人才的守、僻、节、特、人、志。西汉时期的《大戴礼记 文王官人》记载,文王观察人注重六个方面,“一曰观诚,二曰考志,三曰视中,四曰观色,五曰观隐,六曰揆德”(王聘珍,1983),其中的“观诚”列出了“信”“知”“勇”“治”“宁”“轻”“常”“情”等十六条标准(杨东涛等,2004)。汉魏刘劭的《人物志》中提出了“八观五视”,诸葛亮提出了类似的“七观”。甚至在《吕氏春秋 谨听》中,详细记述了尧从娶妻、定法、总理百官、接待宾客、巡查山林等五个方面综合考察舜,以判定其是否可以继承帝位(李永鑫等,2006)。这些“法”“观”“验”正是“阅人”的维度或“指标体系”,体现了“多角度”“多方面”综合“识人知人”的观点。
古代对人的分等评价,更是全面系统。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人划分为12种,有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辨、雄杰。赵蕤在《长短经 品目》中,把人按行为举止风格划分为“庸人、士人、君子、圣、贤”五种。荀子在《荀子 不苟篇第三》把“士”划分为“通士、公士、直士、悫士、小人”等五类。刘向在《说苑 臣术》中把臣子分为“六正”(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和“六邪”(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诸葛亮在《将苑》中把将领划分为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并做了相应的描述(李永鑫等,2006)。这些则是对“综合评判”结果类型的设定。
我国古代对于官吏的考核制度历史之悠久、系统之完备,令人叹服。夏朝以前,对部落首领的考核主要是以天子巡视察访、臣下朝觐述职的方式进行的,简称为“巡狩”与“述职”。“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有职也,无非事着”(丁建军,2009)。据《礼记》载,西周就建立了考核百官的“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制度。
根据丁建军博士的介绍,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采用“上计”制度对官员进行考核,郡守每年年终通过“上计簿”(类似当今政府“统计报表”)向国君呈报当地有关“户口增减、赋税收入、钱谷出入、田亩耕作、手工生产、教育文化、城墙修筑、仓廪管理、治安司法、灾害事故等各方面情况”,“国君逐项进行考核后,决定对郡守的赏罚升降”(这是综合考量各项指标完成情况的结果),秦朝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五善五失”考核官员绩效,汉代则制定了《上计律》及与之配合的“刺史制度”,以及京官的“考功课吏”制度,以“会课”(开会)方式公开评定官员业绩,辅之以必要的当面“质询”,分出官员的“殿”(差者)与“*”(优者)。到北魏时期,形成了“考课制度”,考核结果分为“上、中、下三等”,且又再分“上、中、下”,交叉形成“九品”:“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到唐朝,考核程序更加完备,分类分级考核,四品及以下官员实施初考与校考两环节,三品及以上则由皇帝亲自主持考核,有“四善二十七*”之法。宋代对地方官员财经业绩的考核尤其重视,征税任务完成好坏有专门分段定量的考评办法(历纸、考词等,减或展“磨勘年”),并且融入宋代*著名的“磨勘考课制”之中,优秀者可以“减”若干“磨勘年”,不良者则要“展”若干“磨勘年”(一种任职年资,“展”,即相当于延后才能够转升职级),从中可以看到十分复杂的多维度综合评价的思想。
至明清时期,分别实行“三等八法”“四格八法”等考核办法(侯经川等,2006)。可以说,中国古代政府考评体系,从考核内容(指标)与形式,到组织机构设置甚至于数据质量监督体系,都非常完善(宋一和周凯,2009),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借鉴。
我国古人不仅关注人类自身的情况,而且还特别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成为人们关注与研究的对象。例如,关于人类居住环境的选择问题,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尚书》《周礼》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经典之作。《周礼》中围绕建筑选址营造活动,提出了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土地、水源、特产、动植物、土质等)、人口与土地关系等因素的规划(王其亨和张慧,2010)。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综合评判思想同样十分丰富,“望闻问切”四诊参合的诊断方法便是一种多因素综合评价,即使是其中的某一诊法,同样包含了十分丰富的诊断内容,也是一种综合评判的思想。
人类的文明史一再证明不同国度的人们在很多思想认识方面依然是相通相似的。西方国家同样不乏“综合评价”的思想与实践。虽然我们没有专门就中西方有关综合思想的文献进行研究,但源自近现代西方的许多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思想,与我国古代政府治理思想类似,也不乏综合评价的思想方式。例如,西方有关的选举或投票理论研究,从综合评价角度看,是一种选择性的“择一”评价(决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理论,引起了长期的关于选择制度公平性的讨论;有关群体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也成为群组决策或评价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有关管理组织评价的系列理论(赵丽艳和顾基发,2000),以及众多的相关科学思想,都是很好的例证。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