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设计长久以来便是人们最关心的事物之一。在《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中,甚至连上帝也在进行室内设计,他这样告诫摩西:“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十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合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室内设计的历史远较建筑学更长久。远在人类开始设计独立式建筑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曾以壁画、舒适的皮毛、陶器来装饰和布置自己的洞穴。当人们开始设计独立式建筑物时,他们的建造理念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整体:房屋的结构和空间被一同纳入考量,这个整体就逐渐成为人们所知道的建筑学。室内设计和结构设计从最开始就是建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如今室内设计已经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它自己的教育标准、课程、专业机构、出版物和法律认可。我们感到建立属于它自己的哲学是必要的。在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建筑学甚至是大众哲学、社会研究或文学写作中,总有关于室内设计的哲学性思考。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也一直为房间的布置和家具的使用费尽心思,人们还关注以上二者对人类行为、思想和情感的影响。因此,这本书所要呈现的,并不能说是室内设计哲学的新发现。它仅仅希望提醒设计者正视久已存在的室内设计哲学。
……
登堂入室
尽管当我们进入任何室内环境时,都会首先经过一个入口——是一项由外向内的运动,但事实上,在更早和最基础的经验中,我们首先经历的,却是一项由内向外的运动。在我们尚不知道有一个室外环境存在时,我们就已首先经历了受到庇护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在室内出生,婴孩时期成长于室内,并在室内环境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我。这个环境成为了我们心理上至关重要的容器。无论这个第一环境是什么,它被定义为:居所。在我们认识到还有任何其他空间以前,我们曾经生活在那里。不管日后我们对于其他场所产生了多么浓厚的兴趣,比如商贸场所、公共环境、银行、运动场或剧院,我们对于这些非居所性室内环境的感觉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首次居所性内部经验的影响。这最初的家居经验无所不在,无论是在我们的记忆或是白日梦中,甚至是在潜意识里。
正是在这样的经验中,我们逐渐了解了室内环境的各个种类与功能:我们自己舒适的房间、我们最喜爱的私人角落或是钢琴脚下的小世界、厨房里的嘈杂匆忙、客厅中的仪式感、父母亲房门紧闭的卧室……在此我显然不打算讨论“遗传和环境哪一个对人们的影响更大”,但事实上,童年生活给所有人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走进室内总是带有“回家”的经验。
我们进入室内空间之前的地点——不管那是室外、走廊,或是公共电梯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于特定室内空间的喜爱程度。那就像是一条边界线,而当我们迈入室内空间时,就打破了这条边界线。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25— ,美国建筑师)[1]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一书中指出:“由外向内地设计,同时由内向外地设计,制造必要的张力,这才是建筑学。由于内部与外部的差异,象征边界点的墙壁成为了标志性的建筑。建筑学正是发生在室内与室外使用和空间的双重力量交汇处。”
入口显然是物理上的一个转折点,但它同时也是心理上的,它将引出人们关于此处室内和室外环境的记忆,以及在此记忆基础上的心理预期。因此,入口有其在心理学上的重要意义。艾德里安·斯托克斯(Adrian Stokes,1902—1972,英国作家、画家)在1963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入迷地凝视着……室外的灯光洒在入口处,这样的主题对于17世纪的荷兰画家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可能联想起了一个昏暗又安宁的封闭空间,微光射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又离开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与死中,创痛性的挣扎始终伴随着我们。”波菲鲁斯(Porphyrus,大约公元234—公元305,古希腊新柏拉图派哲学家)也曾在3世纪时写道:“一处入口,是一件神圣的事物。”
越过这个神圣之处,从而进入一个他人统辖下的室内空间,有时是令人焦虑的经历。入口同时也是一处室内环境中令主人感到最不确定的地点,因为他将在此面对任何可能的外来者。所以当主人打开门时,常渴望微微地躲避在门后。但不可否认,这种渴望尽管对于西方社会来说非常典型,却并不是普世性的。应用环境行为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乔恩·朗(Jon Lang)曾指出:“一栋房子中主人迎接外客的地点,因文化而异。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这样的迎接就发生在临街的入口,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半公共或是半私人的领域了,过渡发生在完全的公共与完全的私人之间。”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并不总是着急进入一个室内环境的中心,比如:嘈杂的客厅(不幸的是,许多城市公寓中总有着嘈杂的客厅)或是人人各司其职的大办公室,取而代之,我们喜欢有一点儿过渡区域,处在室内的人就能将进入者打量一番,而进入者也可以为接下来的见面作些准备。美国作家梭罗(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诗人、哲学家)崇尚极简的个人生活方式,他曾住在瓦尔登湖畔自建的小木屋内声称自己喜欢“一栋一打开大门就已完全置身屋内的房子”,尽管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更赞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法国建筑师、室内设计师、雕塑家、画家,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功能主义建筑的泰斗)在《走向新建筑》(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中所表达的,希望“有一小段通廊,让你的思绪远离尘嚣”。
入口处的设计还有一项功用,那就是呈现建筑物自身的识别性,例如“从人头攒动、喧嚣嘈杂的马路上离开……你就进入了一个罗马人的家”。显然,这就是入口区域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它肩负着引介后续空间的角色,它决定了进入者对于整个内部空间的第一印象。
因此,若要适当地设计一处入口,设计者必须已经对整个内部空间的特质有所设想。他对于预期结果的设计理念不能是零零散散的,而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构想,唯有这时,设计者才谈得上真正开始了某项设计。就像一栋建筑的门厅、通廊或会客室一样,“设计理念”正是打开通往整套房屋设计之大门,而设计理念将通过画在纸上或是构想中的平面图来实现。
房间
“一张平面图就是一个由房间组成的集合。”路易·伊撒多·卡恩这样说。在考虑过设计中的物理限制和预算限制之后,在考虑过需要达到的物理和心理上的功能并满足了这些需求之后(无论在概念性的平面图中,这只是多么笼统的一种考量),接下来设计师就该去考虑这个“集合”中的独立成员——那些房间了。这是整个设计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如同整体的规划图将领导着接下来的步骤一样重要,使用者最终将会逐一地去体验这些房间。一间房将从视觉和听觉上向我们呈现出“空间限制”(limits)之所在。房间的围合可能被门和窗户所打断,并且,在最为开放式的平面规划中,可能仅依靠一些小心放置的屏障来取代围合,以暗示房间的边界。无论如何,房间是我们去感知一项设计的最基本单元。
接下来,设计师应当考虑房间风格的一致性。当然,一组房间中可以适当地包括风格变化与对比,但单一的房间是需要保持它风格上的凝聚力的。这并不是说设计中就不能藏有惊喜,但那些最好的房间总是让人一看便知它的特点所在。
我们感知到的关于房间的第一样事物,通常是它的尺寸。让·威廉·弗里兹·皮亚杰(Piaget,1896—1980,瑞士近代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曾提及,人们从幼儿时期便学会了去判断空间的体量。这是指我们走进一间房间时,在无意识中就会自动作出的判断。从理论上说,这些空间体量并没有价值,空间大小也没有好坏之分。但我们毕竟从来不在“理论上”去体验空间,而是在具体环境中去体验。设计师正是需要巧妙地处理这些环境,从而使得空间达到预想中的感知效果。
开阔的室内空间就像宽广的室外环境一样,使人情感释放,正如《(蟑螂)阿奇和(猫)梅伊塔贝尔的生活》 (Aarchy’s Life of Mehitabel) 中谈及的,“唯有在旷野中,猫才像只猫”;或者令人敬畏,一如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在他研读小说《白鲸》(Moby Dick,赫尔曼·梅尔维尔著)的手记中写道的,“我认为从史前福尔松洞穴时代直到现在,‘空间’一直在美国人心中占据中心地位。我特意以大写标出,是因为它来得很大,大而不含怜悯”。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Piranesi,1720—1778,意大利新古典主义画家)创作的“监狱”主题系列铜版画便呈现出了这样的恐怖感——在那些巨大的厅堂中,人们毫无隐私地暴露在外,并且毫无避难之所,尖叫的回声在石穹顶上滚动。正如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1903—1987,法国作家)所说:“这种完全暴露在外、毫无安全感的设计所造成的最大效果,就是将这些华美的宫殿统统变成了监狱。”在设计中加重这样的不安全感,正是建筑师欠缺考虑的结果。要知道,人们通常只能看到巨大而复杂的建筑物的一部分(我们无法知道这一部分有多大),整体的建筑更加超出了我们的视觉、超出了我们的理解。我们所看见的这一部分并不能具有逻辑秩序地引导我们去看清全景。“监狱”剥夺了我们掌控情况的能力,因为,我们如果无法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我们就不可能去掌控它。在皮拉内西不知名的空间中,我们迷失了。
同样地,较小的空间既可能使人感到幽闭,也可能使人感到舒适惬意。曾被文艺评论家瓦尔特·本杰明 (Walter Benjamin,1892—1940) 称为 “室内环境的第一位相士”的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作家,诗人)曾写道:“人类受困于狭小、险恶的空间——身陷于漩涡中、密闭的房间里、拥挤的街道上、坟墓中。人类迷失在建筑里。”不过,在弗兰兹·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地洞》(The Burrow)中,那位形似鼹鼠的生物却叙述道,“较小的房间……能将我更安宁、温暖地围护起来,比鸟儿躺在巢中更加舒适”。
在人类与空间尺寸的关系中,人们经常考虑的一个因素是自己。我们基本上有着相似的身高、体重,我们正是据此来衡量空间。同样,人类视觉的可视距离也相差不远,听见的音量大小也相似,我们以基本相同的速度走路,以相似的音量说话、唱歌、叫喊。在直觉上我们都能感知,什么样的空间尺寸适合什么样的人类活动——适合打篮球的空间尺寸、适合股票交易的场所;感受歌剧《女人心》(Così fan tutte)只需要较小空间的歌剧院,但感受另一场歌剧《阿依达》(Aida)则需要较大空间的剧院;另如八人用餐的房间、两人谈话的房间、用于独自学习的空间,均各有不同。
当然,房间也需要有灵活性和差异性。适合这个人的房间未必就适合那个人,并没有绝对理想的房间尺寸。例如梭罗就感到特别需要更大的空间用于和朋友交谈,而并不需要更多的私密空间,他说:“我有时在小房间中感受到的一大不便,就是当我和客人希望谈论些崇高伟大的话题时,彼此间无法形成充足的距离。你希望在开口之前有足够的房屋空间让你整理思绪……在我的住宅里,人们相隔太近,以至于无法不受干扰地聆听对方的表述,我们无法低声地交谈,就像你往平静的水中扔入两粒石子,如果距离太近,它们就会干扰对方溅起的涟漪……因此,当谈话变成了高谈阔论,声调也越来越高扬,我们只好将椅子逐渐拉远,直到它顶住墙脚,但通常来说,仍旧没有足够的空间。”无论如何,就像卡恩所说的,“人们在不同尺寸的房间内所说出的话,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的房屋需要各种不同尺寸的房间。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们喜欢从他们豪华的公共宫殿(palazzi)退居至更狭小的私密书房(studioli)。正如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法国哲学家)在《空间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中写道(在本书中,我们将多次引用这本著作):“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大房间才能睡个好觉,也并不需要一个小房间才能好好工作。然而,从开始构思到最终写下一首诗,我们则同时需要以上两者……因此,梦想中的住宅必须具有种种优点。无论它的空间有多大,它必须同时是一间村舍、一座鸽棚、一个鸟巢、一只蚕蛹,其间的私密空间需如同鸟巢般温暖。”
有时设计师有机会掌控房间的尺寸,有时却不能。经常地,设计师需要设法将一个较大的空间分隔成数个小空间,以便于住户了解环境。他们同样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需要将一个非常小的空间设计得令人可以接受。
在目前的实践中,容易遇见的房间尺寸问题出现在大型办公空间的设计中。受房地产开发与空间管理的经济因素影响,典型的办公楼层通常采取开放式设计,除去一些服务性设施(如电梯间、消防通道、洗手间、机械间)和高级主管的私人办公间等,其中心区域多半采取可移动的家具“系统”隔板用于分隔而不采用传统的墙壁。这就是现今办公空间的普遍情况。这也许还形成了现今设计师们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尽管这些办公装置目前看来是无法替代的实用,却众所周知地缺少了许多传统房间的好处,不是开放式的办公楼层太大了,就是独立的房间太小。设计师们应当严肃地思考办公空间的规模,例如在中等尺寸的空间中可以加入一些特色性元素,使得这种随处可见的办公环境同时满足人们物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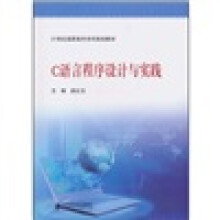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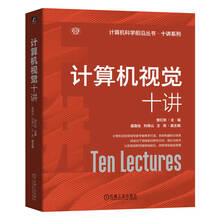





——美国《室内设计杂志》(Interior Design)
在装修我们的居室前,先装修我们的心灵。
——美国作家、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哲学并不如我们想的如此概括与抽象……相反地,它可能隐身于任何日常事物中——衣柜、混凝土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唯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生存的事实方能予以落实,场所的意味方得以揭示。这就是住宅的意义所在——日常的、不确定的、见微知著的。
——美国哲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