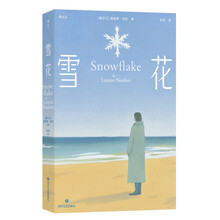时光回到了一九六六年。
一所由近百年历史的汤家祠堂改成的公社小学里,瞿盛丰的命运正在无形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年少的他却毫无察觉。
这是一座占地不下五亩的老屋,前后有两栋楼,青砖黛瓦。前栋有三四层楼高,是宽宽大大的牌楼和正门,后栋高度是前栋的一点五倍多,中间有十五米见方的天井,主体建筑用比脸盆还粗的石柱支撑而起,空旷宽敞,在天井的后栋有牌匾被拆掉的痕迹。后栋的六层已分别改作学生上课的教室。主栋两边是两层楼的厢房,在右边的厢房里,一楼主要用于老师住宿和办公场所及食堂,楼上的木板房是寄宿学生的宿舍。门口是操场,礼堂与操场两边及屋后是菜地,一棵数十米高的银杏树青翠碧绿。
祠堂右边不足百米,是一条几乎天天都清澈见底的芙蓉小河。学校工友每天早上五点不到就来到这里拂水为寄宿生和住校老师做饭。瞿盛丰这天与往日一样,给工友提灯照路。工友每天要做一百多学生和十来个老师的饭菜。这里人的习惯是学生和老师一般八点半上课,寄宿生六点起床,简单洗漱后即早操,然后早自习,大约七点五十分吃早餐。因为只有一个工友,所以工友必须天不亮就得起床担水,然后蒸饭、洗菜、烹饪,忙而不乱。
“骆凡,昨晚从我们宿舍门口到板梯,好像整晚都有人在上上下下跑个不停,出什么事了?”做早操时瞿盛丰问。
“你发烧了吧?是不是帮工友提灯起得太早碰到鬼了?我与你邻铺,一晚到大天亮,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哪有什么声音?”骆凡回答说。
“真的。我整晚都听到了,而且就是从楼梯上楼廊到我们房间这一段,没有再往里走了……”
老师的一声“集合”,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瞿盛丰的寝室在木楼板上,用稻草编织的稿荐(一种用稻草编织的垫子),两端转过来做枕头,上面再铺上草席,就成了床,一般每两人一床,骆凡说是邻床,其实就是床挨着床。
头天晚上与平时并没有任何不同。虽然外面的“文化大革命”已风起云涌。可这里远离城镇,交通极为不便,信息异常闭塞,邮递员一个月都难得来一趟。山村小学似乎被“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暂时忘却了。也难怪,这个公社原是从洪流公社分出来的新公社,这时公社又合并到洪流公社去了。而学校离原公社五六里,离洪流公社二十多里。大队和学校干部到公社开个会都要走弯弯曲曲的山间路。也好,即使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农历闰三月,这所完全小学还在正常运行。
山高皇帝远嘛。
作为家里排行老七的瞿盛丰上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前后,除了大哥之外的五兄妹在几个月内先后夭折。但“留下”的大哥,据说是母亲十七岁不满且来足月而生的,身体一直不好,比同年龄的孩子个子要小几成,七岁才会走路,十岁才送去读书。正因为如此,瞿盛丰一生下来就成了父母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
若干年后有人问瞿盛丰:“三年自然灾害中,人人都饿得要死,你那时已有五六岁了,有什么记忆吗?”
“我只有‘文化大革命’十年饿得眼睛发黑的记忆。至于三年困难期,只记得我的远房堂弟没得吃的,常吃米糠和糯米坨(一种藤类根部,一般比汤圆大不了多少,挖掘出来煨熟可以吃,有糯米粘味),经常拉不出屎,大人们用纺棉花线轴俗称车线的细铁条从屁眼里挖,挖得直流血。”
三年困难时期全民挨饿,但瞿盛丰的母亲在食堂做炊事员,每天不仅能让他基本吃饱,且还时不时有个荷包蛋吃;再说平时家里有点什么好吃的都是瞿盛丰的,他哪会有许许多多同龄人三年自然灾害挨饿的切肤之痛?
上小学后,瞿盛丰长得虎头虎脑、敦敦实实、白里透红,功课门门优秀,老师喜欢、同学敬佩,初小毕业以当年该校第一的成绩升入全公社唯一的高级完小,十岁就当班长,还当上了全校少先队大队长和旗手。管着这个山区因读书迟而比他大五六岁或与他同龄的同学和一些都记不清读了多少个一年级的留级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