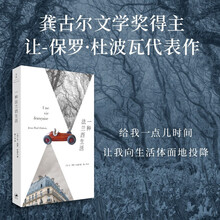1 许多年前的一个早晨,当我躺在黎村那间挂满兵器的屋子里,我突然想到了人的灵魂。这年我十六岁,是村落里的一名搏击少年。在绵绵无尽的打斗 之中,时光悄然流逝。每天,我会走到村里的大樟树下,静静地端坐 片刻,看蓝天下茂盛的树枝,看树枝上的灰雀。在我的生命里,我喜欢的自然物包括天地、草木,风、雨、雪。风在我看来,是一种神器,它能让我的肉身从麻木趋向精神;雨 是安抚五脏的家伙,可甜可苦,我愉悦时,它便是甜的,滋润我心,忧 伤时,则是苦涩滋味;雪使人宁静,但这一天早上我却感觉到浑身燥 热,我知道,雪在我心头的滋味改变了。在这个寒冷的早晨里,我从窗口看见了漫天雪花,我听到母亲 在屋外对谁说了一声,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然后,我就闻到了一股 清幽的气息。这股清香随风而来,随风而逝。母亲柔软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吃饭啦!”我便看见父亲一身短 褂从屋外走了进来,鹅毛大雪落满了他的头发,他的眼睫上也沾着 融化着的雪子,衣服上挂满了雪水。他将长剑往墙角一放,接过母亲 递去的毛巾。父亲曾是江南有名的镖师,在遇到母亲之后,他选择归隐故乡。母亲说,爱情终于让一颗漂泊的心安定下来了。黎村毗邻省城,村民世代尚武轻商。倚山而居的村民重硬气功 铁布衫、金钟罩,村子里一半的石板都是他们敲断的;临河一带的人 家则习太极与玄武拳,一个自称道长的瘦子整天在那里教他们吞吐 纳气,偶也见他将墨黑的药丸放入徒弟口中,引得这帮徒孙们哇哇 乱叫,搞不清楚这滋味是痛苦呢还是痛快;介于山与水之间的十余 家农户则推崇摔跤,他们身形健硕,一上手就黏住你,搂你腰抱你 腿。跤王黎无定身形魁伟力大无比,但他却生出一个气质如兰的女 儿,名叫苇。我家是独户,在村落的正中心。“这是一个与天狼星暗合的位 置。”母亲在观察星相之后下了定论。母亲的祖上是做大官的,她从 异乡嫁入黎村时,除了绸缎、棉被,还有笔砚与算盘。母亲浑身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她是黎村少有的能够识字、习字 的女人。她教我珠算,每晚她会高举那把小叶紫檀做成的算盘,发出 “嘁嚓”一声,我就端坐在她跟前了。“你可以不算计人,但必须懂得算计银两。”这是她的名言,然后 她纤细的手指在珠子间轻盈地撩拨起来,灵动如雀。如果是春天的早上,可以听见她兴致勃勃地对着村里的千年樟 树发出鸟语,飞雀们很快来临,憩息在枝头,与她对吟。黎村的商贾、村民视樟树为至宝,缘于树底下供奉着的一只纯银雀儿。银雀塑像 几时立身于此,传说不一。但凡恭敬祈福敬香之人,都说能够如愿。仿佛是佛。黎村最壮观的景象,奠过于如此一幕:樟树底下聚集了燃 香膜拜的村民,树顶上是从苍穹盘旋而至的飞雀。母亲还能预知孕妇生男生女,无一失手。黎子平家闺女被人肚 子搞大,成为众矢之的,这多少让人觉得伤风败俗。母亲却说:“贵人 会接走这对母子。” 几个月后,母亲的话应验了。那闺女产下男婴的那天,一支衣衫 不整的军队开进了黎村,身着长官制服的一个男人从马背上跳下 来,几个小厮就请出了黎子平闺女与家人,长官仔细审视婴儿,看到 他的鼻子鹰钩似的与己无异,便心满意足地将母子请入轿。这队人 马随即绝尘而去,马匹扬起的灰尘朦胧了村民的眼睛。黎子平一家人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这是临时大总统手下的一 支部队。攀上军队长官可遇不可求,只要不嫁给士兵,管他做第几任 姨太太。那时,父亲正研习一门武功绝技。他结识了一位给革命军头领 做保镖的武师,专门求教了一种叫“自然门”的功夫。据说这位武师 的前辈,是一个名叫徐矮子的隐世高人。父亲说,战争制造流血,与其扛着枪与人厮杀,不如用拳修炼 己心。父亲让母亲准备了几只自编的竹箩筐,因为他要练轻功,在竹 箩筐上走八卦步。“除非你是麻雀。”我跟父亲说。令人凉奇的是,父 亲在踩坏了十六只竹箩筐,摔到屁股老肿时,终于像麻雀一样轻巧 地能在竹箩筐上行拳了。这真是奇迹。父亲的瘾头不止于此,他开始钻到方桌底下习拳,他说要把架 子练到能贴到地上。这让我油然生起敬意,我相信父亲贴地而行的 武功一定是超然物外的功夫。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