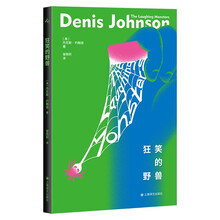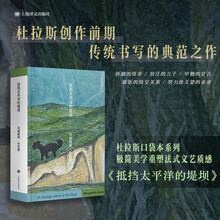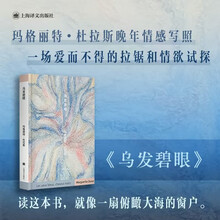我一定在夜里思考了我的作息计划。我想我可以给自己讲四个故事,每个故事的主题都不同。第一个讲一个男人,另一个讲一个女人,第三个讲一样东西,最后一个讲一个动物,也许一只鸟。我想我什么都没遗漏。这样就好。也许,我会把男人和女人放在同一个故事里,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区别是那么的小,我是说在我的人物中。也许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结束。从另一方面讲,我也许又会结束得太早。我又陷入了自己悬而未决的疑难之中。但这是逻辑疑难吗?真的吗?我不知道。
就算结束不了。也不要紧。但要是我结束得太早呢?那同样也不要紧。因为那时我将讲一讲仍占着我脑子的事,那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计划。这将是一次清仓盘货。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这个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只要我不搞错的话。再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件事我非做不可。至多,我为它留一刻钟。也就是说,假如我真的愿意,我本可以留更长的时间。不过,要是在最后一刻时间不够了,我只需短短的一刻钟来拉我的存货清单。我愿从此后我心里清清楚楚,而不古怪成癖,这是在我的计划中的。我清楚我随时随刻都有可能油尽灯灭。
那么,不等不待地讲讲脑子里的事情不是更好吗?这难道不是更谨慎可靠吗?即便在最后的一分钟,只要情况需要,不是还可以做些修改吗?这就是理性给我的建议。可是现在,理性对我的控制还不那么牢靠。一切都促使我放大胆子。要真是死了而没有留下清单,我能忍受得了这一可能性吗?这不,我又重新吹毛求疵起来了。既然我要去冒一冒险,必须假定我会忍受。我一生都忍着不去制订这一计划,我对自己说:太早,还太早。那么现在呢,现在仍然还太早。我一生都在梦想这一最终时刻的到来,赶在失掉一切之前,确定它,画出线条,求出总和。这一时刻仿佛迫在眉睫。我却不会凶此而失却冷静。就这样,我的故事得先讲,如果一切正常,那么最后的便是我的清单。我、将以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开始,只是为了以后不再见到他们。这将是第一个故事,没有材料分成两个故事讲。那么,现在总共有三个故事了;我刚说明的那个,然后是动物的那个,然后是物件的那个,或许是一块石头。这一切十分清楚。随后,我再处理脑子里的存物。假如这一切完了之后我还活着的话,就将做必需之事,只要我不搞错的话。就这么决定了。换言之,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但我知道我将到达,我知道长途的盲目跋涉终将完成。何等的差不离哟,我的天!很好。现在该玩了。我很难习惯这个想法。旧的流水账在叫唤我;现在,该说的是相反的话了。因为标得清清楚楚的这条路,我感到我也许走不到头。但是我满怀希望。我问自已我现在是不是正在失去时间或者反过来是不是正在赢得时间。我同时决定,在开始我的那几个故事之前,要简单地回顾一下我的现状。我想我是错了。这是一个弱点。不过,我会超越它。到后来,我将怀着满腔的热情来玩。再说了,这将与清单相对称。
无论如何,这样做是符合美学的,-·种确确实实的美学。因为,我还必须重新变得严肃认真,好再讲一讲我脑子里的存货。就这样,我剩下的时间分成了五份。哪五份?我不知道。
我猜想,到时候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分割的。
假如我再要考虑考虑,那我就会赶不七我的死。我必须说,这一前景还真有一些迷人之处。不过,我可是有所警惕的。几天以来,我发现什么事儿都有它的魅力。还是回过头来说说那五份吧。先是现状,再是三个故事,最后是清单,就这样。这里也不排除某些小插曲。
这是一整套编排好的节目。只有万不得已之时,我才会把话题岔开去。就这么定了。我感到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这没有任何关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