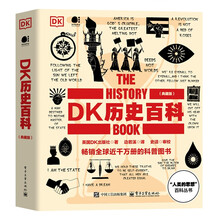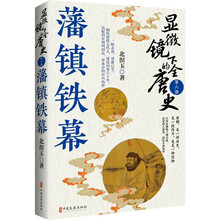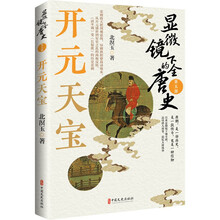忠之有道
如何才算得上是忠臣,在中国古代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定论。其实倒不是没有什么定论,而是忠的层次不一样罢了。
齐庄公荒淫无耻,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就把庄公在自己的家里杀了。蒯聩刚好出使晋国将要返回,他的仆人说:“崔杼已经在齐国杀了国君,您打算到哪里去?”蒯聩说:“你快赶车,我打算回国以死来报效国君。”他的仆人说:“国君的暴行昭着,四周相邻的诸侯没有不知道的,您却为他而死,不也太不值得了吗?”蒯聩说:“你的话很有道理,但说得太晚了。你如果早早地对我说,我就能去规劝国君。规劝不听,我还能离去。如今既没有国君又没有离去。我听说,吃谁的俸禄就要为谁的事去牺牲,我既然吃了乱君的俸禄了,又怎么能去惩治国君而杀死他呢?”于是,驱车回国而死。他的仆人说:“别人有乱君,还为乱君去死;我有这样贤明的主人,难道能不为之而死吗?”于是,系好车绳,就在车上自杀了。君子听到这件事说:“蒯聩可称得上是保住名义了。”
但当时的国相晏婴就不一样了。晏婴听说了崔杼杀了齐庄公,站在崔杼的家门外,他的仆人问:“大夫要为君王死难吗?”晏婴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王吗?我为什么要死难呢!”仆人又问道:“大夫要逃走吗?”晏婴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为什么要我逃走呢?”仆人又问:“大夫要回家吗?”晏婴说:“我的君王都死了,怎么能回家呢?治理百姓的人,岂能只为凌驾百姓之上,应该以国家的大业为根本;做国君之臣,哪能只为饭食,应该以侍奉社稷为根本。所以,国君要是为社稷而死,则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出逃;倘若国君为自己的私事而死,不是国君宠爱的亲信,谁能为君王而死难,为国君而逃亡呢?况且,有人有自己的国君而把他杀了,我为什么要为此而死,为什么要为此而逃,又怎么能回家呢?”
后来,晏婴终于帮助齐景公杀死了崔杼。但晏婴的这种忠诚似乎还不够档次,比之他的先辈管仲,应该是相形见绌了。
当初,管仲、鲍叔牙和召忽3个人受命分别辅佐国君的3个儿子。召忽觉得自己所辅佐的那个将来不可能当国君,不愿意受命,后经鲍叔牙劝说,才勉强答应了,但他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果有违反国君的命令而废弃所立并篡夺了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了。何况,参与齐国政务,受君令而不能改变,侍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却不同意他的看法,说:“我的想法不一样,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一个人而死呢?只有国家灭亡,宗庙被毁,祭祀无人这3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这3件事,我就要活着。我活着对齐国有利,我为何要死呢?”
果然,后来召忽为公子纠被杀而自刎,管仲没有为自己所辅佐的公子纠而死,而是接受了自己的“仇人”公子小白的任命,辅佐公子小白建立了霸业,使公子小白终于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霸主。
——见《晏子春秋》《管子》《说苑》
治盗之道
《庄子》上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意思是说,盗窃衣钩这样小东西的人要被诛杀,而盗窃国家的大盗却要当诸侯,仁义道德在哪里呢?仁义道德在诸侯当权者那里。
何谓强盗,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讲到深处,也许并不容易那么明白。
公元前552年,邾国人庶其背叛了他的国家投降了鲁国,并将邾国的漆和、闾丘两座城邑献给了鲁国。鲁国的当政者季武子很高兴,为了感谢庶其,把襄公的姑母嫁给他做妻,并对他的所有随从都给以优厚的赏赐。
当时,臧武仲正任鲁国的司寇,掌管国家的狱讼和治安。他对季武子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便想找个机会提出来。恰巧,鲁国的盗贼闹得很凶,臧武仲有意不治。季武子对他很有意见,便找到臧武仲,问他:“盗贼闹得这样厉害,您专负其责,为什么不去禁治?”臧武仲说:“盗贼可不能捕捉。而且,我也没有能力去治。”季武子感到极为奇怪,问他:“我国四边都有边境,可以用来禁治盗贼,如果盗贼不可以禁治,我们要边境和军队干什么?再说,您作为司寇,职责就是维护治安,惩治盗贼,怎么说没能力呢?”
臧武仲说:“不错,我的职责就是禁治盗贼。但在我禁治盗贼的同时,我们国家有人却将外面的盗贼引进来,并且给予礼遇。有人让外面的盗贼进来,却让我治国内的盗贼,我怎么能治得了?”
季武子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指责自己,就说:“谁这么大胆,敢引外面的盗贼进来?”
臧武仲说:“还有谁呀,就是您呀!”季武子听了,非常生气。臧武仲说:“听说您给了邾国人庶其很优厚的待遇,是吗?”季武子说:“这和招引盗贼有什么关系呢?”臧武仲说:“庶其在邾国,偷盗了国家的城邑,前来我国。您把国君的姑母给他为妻,还赏给他城邑。不但如此,那些随从也被赐以车马、衣服、佩剑、带子。这些大大小小的盗贼都得到了赏赐。赏赐盗贼,又要去掉他,这恐怕是太困难了吧?我听说,处于高位之人,心灵要洁净,待人要专一,其一举一动都要符合法度而使人民信任,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上面的所作所为,对百姓的影响很大。上面遵守法度,而百姓有人不遵守,上面因此加以惩治,百姓哪个敢不警戒?如果上面胡作非为,百姓也跟着仿效,这是势所必然,谁又能禁止呢?”
季武子听了,再也无话可说了。
今天看来,臧武仲所讲的道理既对又不对。如果连别的国家的人前来献城投降都认为是盗的话,岂不是太迂腐了呢?道德的适用应该是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的。那么到底盗与非盗的界限何在呢?似乎还是庄子的那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更能说明问题。当然,从理论上讲,强权并不等于真理,但确实有的时候强权和真理并不是十分容易区别的。
——见《左传》
悲壮的改革家
纵观历史,社会的变革总在进行,有时激烈有时舒缓,但是对于喜欢因循守旧的中国人来说,一个千古的命题是不变的——为天下人变法者最终都以悲剧为结局。倒不是中国人顽固不开明,只是因为所谓的“变法”没有真正根除社会弊端的根源——封建统治,只是在方法上找出路,既然这样,当然最后会失败。
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改革家之一的商鞅就是这样的。
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他听说秦国招纳人才,就跑到了秦国。
秦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远处西北边陲,本来很小,名不载诸侯之籍,但它总是从其他诸侯国招纳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使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发展是由秦国本国的人才推动实行的,秦国的这种开放的态度以及君主的进取精神,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但到秦孝公这一代,秦国还不算很强大,东邻魏国就常欺负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就发布了一道命令,招贤纳士,凡能使秦国强大的人,封高官、赏土地。
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着秦国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去见秦孝公。他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不敢一见面就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给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弄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3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变法。这下引起了秦孝公的兴趣,两人谈了3天3夜,也不觉疲劳。
秦孝公当即任命他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先耍了一点小手腕。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大木,下令说:“谁若把这根大木扛到北门去,就赏他50金。”那木头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动,而50金之赏却非常之多,时人以为有诈,不敢搬运。后有一个粗鲁人见赏金很多,就扛到了北门,结果真得到了50金的赏金。商鞅借此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
于是,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做官奴。
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大功被封于商地,领有15座城邑,号为商君。
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的利益的,所以百姓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变法之初,就有许多旧贵族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着,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他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在秦国无容身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商君之法规定,住店要有证件,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只好跑到魏国,魏国人要杀他,他又只好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旧贵族前来逮捕他的军队。由于寡不敌众,兵败被擒。
商鞅最终遭受的刑罚是“车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马车之上,让马车把他的躯体生生地撕开。其刑罚之酷,令人发指。
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一直发展起来,在百年之后统一了中国。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虽无商鞅变法之激烈,结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似乎更有意味。
先说其法反复以及新、旧两党的交替罢黜任免。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提出并推行了一些变法措施,诸如在青苗农贷、农田水利、省兵置将以及向中央集中财力等方面有所变革,这些措施确实是根据宋朝当时的社会积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动机无疑是良好的。实施的效果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毕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然而在朝廷内部,特别是一帮大臣之间,围绕新法形成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的旧党,两党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
这两党交往了好几个回合,一会儿新党上台,贬斥旧党,一会儿旧党上台,抑制新党,再加上势利小人投机钻营,使得新、旧两党斗争几乎完全变成以废、立新法为幌子来进行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事情到了这一地步,至于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里还有人去考虑。
新法时兴时废,完全成了党派权力之争的借口和由头,已无什么实际意义。最后,新法还是被完全废除。早在新法被完全废除以前,王安石就被弃隐居了。他还算是幸运的,没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尽天年。
平心而论,王安石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和一位十分有学问的文学家,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实在争议很大,《拗相公饮恨半山腰》一文就把王安石及其改革诋毁得不成样子,就是王安石以后的许多正直、有修养、有学问的大臣也没有人说他是个好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说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的一次灾难,是上天灾异的显现。
由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对于变法的特点来说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那就是中国的变法绝非坏在老百姓的手里,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才是使变法夭折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还有许多改革家的命运也是一样,这里就不一一陈述。
如此看来,历史上的改革是一个祭坛,而改革家则是这个祭坛上的祭品。这个祭坛因充满了悲剧色彩而变得异常的凄壮。变法者身为悲剧虽不自知,但是他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
——见《史记》《宋史》《资治通鉴》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