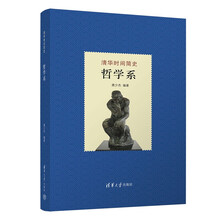监狱的浪漫
我错了,虽然并非完全错了,但确实错了。我用了十七年才发现这些错误。
我毫不怀疑,全是因为她。她一开始就在那儿,脸上有雀斑,眼神黯淡。你也许会说,一切是因为她开始的。这么说很接近,虽然事情并不像听起来那样,这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我去监狱,并不是为了给写小说寻找爱情故事、情节、对话或塑造人物;我的兴趣出于社会学:我是带着冷静客观的眼光去的,这些毫不夸张。而且,对于生性浪漫的作家来说,防范森严的监狱是理想的灵感之地,于我也不例外。要不是因为意外,一切都不会有闪失,我周游世界推销的则会是另一套智慧。很久以前,我就写过这个女犯人,以及受她启发而诞生的工作。那时我还不能说出对她的了解,或者她对我、对我将要做的工作产生的影响。
贝德福德山监狱在纽约市以北,天气好时,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可到达。监狱的历史相当久远,我初次看见它时,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夏天,下了高速,道路蜿蜒,经过高挑纤细的树木和田野,再往前开半英里,周围的景色提醒我,就要到了。一片毫无生气的荒地,散布着石块,太阳地里的黄色大巴和汽车上积满了灰土。监狱外面没什么动静,只有一些换岗的哨兵,或者搭载访客的黄色大巴来到或离开。在这片死寂的广场后面矗立着砖楼,楼间有一些老树,枝繁叶茂,给人增添了一丝耐心。这是最高戒备监狱,每个女囚的刑期至少是六年,还有很多被判了无期
徒刑。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暴力比街头还要泛滥,这是她教给我的。她即将成为我的老师,正如我是她的老师那样。
初来乍到的那个下午,在一个大房间里,我和犯人们以及两名社工坐在金属椅子上,围成一圈。这房间大概位于监狱中央,不过我也不太清楚。社工让我坐在一个短小敦实的年轻女子旁边。她和我握手,用一种我以为适宜监狱会见的正式礼仪相互做了介绍。她看我时,目光迟钝,监狱中典型的带有敌意的眼睛,而从一开始,她的嘴角就带着一丝讥笑。
我们听了关于虐待妇女的讲解,也听了她们的故事,看着她们一边讲,一边哭;还观看了在场一些人的录像,比她们现场的讲述更详细。放完录像,一个高个儿的金发女子大步走到圈子中央。她站得笔直,手垂在身体两侧,用一种平淡、不带口音的语气讲述着。她说自己参与抢劫了一家便利店,她的任务是把刀架在店员的脖子上;她说自己并不想伤着他,可是他非要挣扎,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告诉他别动,但他还在挣扎,她就割断了他的咽喉。
高个儿女人讲话时没有表情,她只做了一个动作:抬起右手比画了一个用刀割断咽喉的动作,似乎那是店员的咽喉,然后,她的手臂又垂下来。停了一会儿,她说,她马上就能回家了。她没有再提杀人这件事,也没有提到她回家以后怎样生活。她从我身边经过回到座位上时,我看到她像是哭过。
当高个儿女人说她的故事时,我并没有留意到坐在我身边的女人,我更想看到大家的反应。没有人感到震惊,没有人想回避正在坦白如何杀人的自己。也许她们以前听过这件事,也许她们听了上百遍。监狱就是不断重复,这是惩罚的本质。伟大的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说过:“重复意味着死亡。”但这种重复并不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这重复是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人们因此才把服刑称为“谋杀时间”。
在聆听暴力和观看救赎录像带的间歇,我扭过头看身边的这个女人。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也因为我没有忘记到这里来的目的,我问她:“你觉得人们为什么贫穷?”
“因为他们没有城里人那样的道德生活。”
“你说的道德生活是指什么?”我猜她指的是宗教。
她说:“你应该让孩子从小就开始。”她说得很快,不时冒出一些街头俚语。她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恢复了几乎没有停顿的语速:“你必须把城里人的道德教给孩子。怎么做到呢,厄尔?就是带他们去看戏剧、去博物馆、去听音乐会、去听讲座,这样他们才能学会城里人的道德生活。”
“你是指人文?”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世界上最傻的人:“是的,厄尔,人文。”
她叫出我的名字让我感到意外,她的名字不那么常见,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向她微笑,她误以为我是在迁就她,却没有认识到,其实正相反。我反问:“那他们就不会再受穷了?”
她读懂了我回答里的每一个字,也开始用讥讽的语气回答:“他们就不会再受穷了。”
“你的意思是——”
“我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与街头生活不同的道德选择。”
她没有提到钱或是工作。在这方面,她像我问过的其他人一样。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没有人提到钱和工作。我在美国各地看到人们生活在我眼里的压力围困之中——丑陋、暴力、饥饿、虐待、糟糕的学校、毒品、简陋的住房、歹徒、凶狠的警察,还有电视和广告的噩梦。最后这一点把贫困的屈辱说得再清楚不过,往往最糟糕,最难以忍受,尤其对孩子们来说,是通过比较而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电视和广告时刻在提醒着他们,自己是穷人。这些宣传没完没了,没有一时停歇。他们没有时间反省,没有时间喘息,只有被动的反应。我很欣赏她说的对于贫穷的解决办法,但是“城里人的道德生活”怎样才能使人摆脱周围的力量?一个博物馆又如何能驱赶贫穷?那些历史和雕像既不能吃也不能穿;还有,政治生活怎么办?摆脱贫穷需要政治,我想,而不是城里人的道德生活。但是,为了进入公共领域,实践政治生活,穷人先要学会反思。她说的“城里人的道德生活”指的是这些吗?我看了她片刻,转过头去,没有说话,轻视不需要回答。
开车回纽约的路上,我回想起自己的教育经历和她的话。如果真能让穷人有城里人的道德生活,他们也许会脱离贫困;即使不能摆脱经济上的贫困,至少,可以脱离束缚他们、让他们碌碌无为、疲于奔命的那个环境。我把疑问暂且放在一边,顺着她的思路思考。我发现,她为我的想法构建好了框架,可惜我没有细想,因为我的心思都在写作上,还以为自己找对了路子。
你是指人文?
是的,厄尔,人文。
没有人真正知道“人文”是指什么。《牛津英语词典》也不愿意为这个词写长篇的解释。《福勒现代英语用法》里说,一个人在报纸上读到“人文”这个词,可以给它下四种定义,哪一种都对。我接受了服刑于一级戒备监狱中的一个女囚给出的含义。部分是由于她下的这个定义,我花了十七年的时间开始从事这项轻微却有意义的工作。她没有提到彼特拉克[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
]或是他对人文的定义,不过我觉得,她指的就是这个,我同意她的说法。彼特拉克在文艺复兴时这样不容置疑地定义人文:人文包括道德哲学、艺术史、历史、文学和逻辑的经典著作。不多不少,就是这样。如果她不是指这个,那她等于什么都没说。她通过默许说服了我,不是争辩,甚至不是提议。她那时已是一位了不起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