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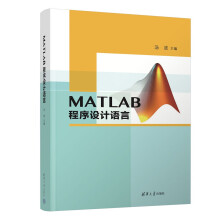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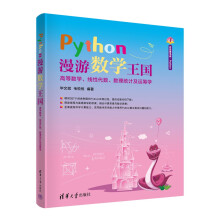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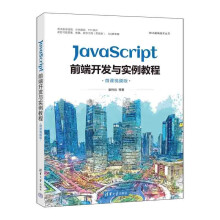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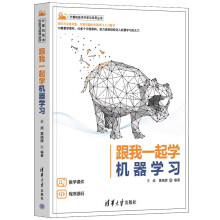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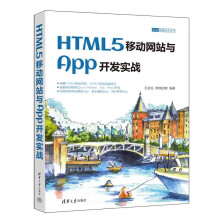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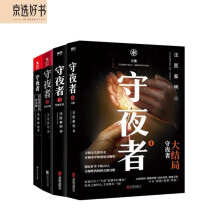

1、《大历史不会萎缩》为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文集。黄仁宇及其提倡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代表作《万历十五年》畅销20余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及于史学界之外的非专业读者。
2、此版根据台湾版本重新修订,在前版的基础上增补了《个人经验与历史》以及有关蒋介石和其他主题的数篇重要文章。
3、《大历史不会萎缩》本书中,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通过中外的历史对比,结合自身的经历,重新审视中国现代的历程,对其中的事件、人物进行了重新解释与评价,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视角。
4、本书中,黄仁宇以“大历史”的观点,对古代、近代的部分人物、事件,乃至当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等进行了重新阐释,展现了“大历史”在今时今日的意义。
《大历史不会萎缩》搜集了黄仁宇生前发表的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访谈、时论等形式。是对他所提倡的“大历史观”的进一步阐释与研究上的具体应用。在前版的基础上增补了《个人经验与历史》以及有关蒋介石和其他主题的数篇重要文章。
作者从数百年前着眼,通过与英国、荷兰等国家之间的比较,指出中国要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与其他国家所经过类似之程序大致相同:需要创造高层机构,翻转低层机构,并重新厘定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中国近现代的人物、政党、事件即在中间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作者认为,“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一百年之内将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三百年。”这全部经过,由 “公众之志愿”所促成,而非领导人物独断,而且领导人物自己往往做了执行历史发展之工具。因之,我们在看历史时,要注重事实后面的非人身因素,而非止于道德上的评断。
除此以外,作者还从“大历史”的角度,对古代、近代的部分人物、事件,乃至当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国两制等进行了重新阐释,展现了“大历史”在今时今日的意义。
个人经验与历史
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1938 年的夏天,当日军进攻武汉的时候,我工作的《抗战日报》因故停刊。我那时有意从军,所从的军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中央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委员长兼。骤看起来,这很奇怪,因为《抗战日报》的主笔为田汉,在我为田伯伯;和我在同一楼房的编辑室内以笔墨劳动的则为廖沫沙,在我为沫沙兄。虽然我在这时候还没有知道他已多年为共产党员,但是在谈吐中知道他们思想前进,而沫沙兄尤其慷慨激昂。而同我去成都的则又有田伯伯的长子。海男弟当日尚未成年,毕业之后,我们同在驻印军工作,抗战一停止,他就自动入人民解放军。我听说他对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和炮兵的训练,做有实质上的贡献,又曾在朝鲜战事期间,去过前线,此是后话。
且说我们到武汉军校复试时,看到《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希天兄也是我们在长沙见过面的,那时仍是无党无派,和他一同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陈侬非则确实为共产党员。我知道他于抗战前的20 世纪30 年代被国民党人员抓住,受过苦刑,当日仍感筋骨隐痛,获得我们的同情。
长江一见到我们,就想劝我们放弃从军的念头,要我和他一起办“青记”。自己说还不算,又请其他朋友苦口婆心地央劝。我当日刚满二十岁,擂吹唱着大丈夫投笔从戎的雄心壮志,不为所动。长江就说如果我们一定要从军,也应当到延安进抗大,不应当到成都进军校。我们就说,延安所教的为游击战,我们想学的乃是正规战。我那时确是少年气盛,我认为中国军队在长江防线守不住,乃是将领偷生怕死。假使所有的将士,统统一步不退,“撼山倒海易,撼岳家军难”,何至一退就几百里,一溃就几十个师跑得落花流水?有一个晚上我们又谈到这延安和成都分歧点的问题,在座也有潘梓年先生。旁的朋友都说希天兄对,独有潘先生偏对我们同情。他说我们既有这志向,应当去成都。希天兄乃边笑着说:“你们既有《新华日报》的社论为你们做后盾,那我不能再劝了。”因为在武汉时代,潘先生常为《新华日报》社论的执笔者。这些往事,已快有半个世纪,今日追怀,当然有不胜沧海桑田的感慨。可是这篇文章执笔的动机,又不仅是吊念亡友,而更不是夸说自家有先见,所以今日保持在海外偷安的侥幸,也不是因袭滥调,假惺惺地负荆请罪,做言不由衷的忏悔,乃是叙述在大陆时代的大动乱中,很少人能对前途做彻底的打算,常常是因时就势,也常常是遇与愿违。只有最后局势稳定中,才能将前后的来因去果,看得清楚。因之更叹赏历史的发展,有它的规律。与之相较,个人不仅力量微薄,其所观察,也难能衡量全盘局势。
现在先说1938 年,此时还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在武汉的各种集会中,通常有两党的人士和其他无党无派的人士抵掌摩肩,我们年轻人,更没有为政治问题留难,只希望抗战胜利,中国不至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已。因为国民党有“清党”的历史,抗战期间,两党已生嫌隙,内战一开,更是黑白分明。下一代的人,总以为我们这一代对党派问题,早有成见,去此舍彼,也出于早期志向,如田伯伯及海男弟他们一家与周恩来总理有旧,对于传统所谓“世交”。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不是全般现象。与之相反的则有如沫沙兄熊夫人的父亲,即沫沙的故岳父熊瑾玎先生,为武汉时代《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他的儿子熊笑三则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在昆仑关击败日军时任团长,抗战结束次年冬即荣任国军的第二百师师长。二百师是当年全国数一数二的“机械化部队”,熊笑三将军为国民党高级干部亲信可知。至于在两党中来往的人物,情形更多。我们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国军十四师当排长。按战斗序列十四师属五十四军,其前军长陈烈,即曾为共产党员。我们的团长梁铁豹,也曾为共产党员。而在驻印军任国民党党代表的盛岳,则不仅曾为共产党员,也是早期留俄学生,因为反对苏联侵华政策,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的苏联专家,以后更出席联合国会议,指摘苏联。用不着说的,由国民党去共产党的情形更多。
希天兄范长江因他的政治活动,牵涉过多,为《大公报》所不容,被胡政之开革,以后办《国新社》,入共产党,在苏北解放区工作,人民政府成立前后,曾在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做过负责人,听说于“文革”期间在河南确山身故。田汉田伯伯寿昌曾写《关汉卿》的剧本,把他满腔热忱及艺术情调熔合一炉,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只是好景不长,听说他身故的情形也极凄惨。只有他所作《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今日人民共和国国歌,使我们知道他的人,一闻聂耳的乐曲,如见寿昌其人,可谓精神不死。沫沙兄虎口余生,三年前又为我著书《万历十五年》作题签。我为他欣幸,个人也非常铭感。只有陈侬非兄,则很少为人道及,又始终为“无名英雄”。
中国人写历史的传统,以“褒贬”为前提,通常将叙述人物质量,分为至善与极恶。这种历史观,只能表现作者个人在世间的经验(概括来说,以一百年为最高限度),而不能表彰超过生命长度的历史经验;也只能代表农业社会形态简单的经验,而不能表彰工业社会组织关系复杂的经验。这办法正是我们今日应该改革的地方。可是反转来说,长期历史的经验,乃是短时间生活各种事务堆积的成果,否则写来,只能成为抽象的观念,而不足成为历史。如果我这篇文章就此搁笔,也必陷入于“褒贬”的陈套。现在我既已提议,创造新的历史观,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将自己寻觅历史的途径公开。既有些地方,好像自卑,有些地方又矜夸,
不得已也,不如此则这篇文章无法写也。
读者必须看到,我进军校时,是一个无经验的年轻人。但是从小又读过太史公司马迁的著作,满头满脑的好奇心冲动。即景慕田伯伯和希天兄等,也是读过他们的剧本及报道,内中多“传奇主义”的色彩,所以我个人主义的成分浓厚。国民党的好处,则是他们注重外表形式,纪律在行为上表彰,没有整个思想管制的体系。所谓历史观,也是传统历史,这些方面,给我有自寻门径的机会。而我真正第一次体会中国社会的实貌,为1941 年。军校训练两年后,向驻滇南第十四师报到。时抗战已入后期,由于欧战急转直下,日军占领越南,有威胁昆明模样。十四师原为国军教导第三师,为陈诚将军部下嫡系。由粤北行军经广西全境抵云南马关县,当日亦认为国防前线。我做了好几个月步兵排长之后,才知道军事失败的真原因。十四师编制有万余人,驻滇南时只有四千人,而友军邻师有的只有两千人。因为几百里行军,途中无补给站,无休养所,亦无医院及治病室,全部装备给养大部分靠官兵自己肩扛身携,即征用民间骡马,亦因此地为烟瘴区,整片大山,人口稀少,前后不继。一遇雨季,道涂泥泞,狼狈已极,而淫雨与疟疾相继并至,士兵营养不良,一病倒拖死,有的即逃亡,即补充兵员,情形亦相似。
我虽为排长,又似代理连长。因全连官兵只四十人,无连长,亦无其他排长,有特务长一人(掌书算给养),后来也由师部调往他任,所以我们驻屯民房一间内,全由我年少书生做主。这四十名士兵内有三四个上士下士,为抗战前募兵时代的“遗老”。他们体格粗粗可以过得去,也能射击及投手榴弹,看不起我军官学校出身的学生,没有战斗经验。(后来在缅甸前线,我虽为参谋常出入第一线排连,曾负伤,与此有关。)有时早操称病不起床,我不得不用威迫利诱的方式,才能保全我做排长的面子。其他士兵大部分为抗战期间征兵所得。一般为癃痹残疾,不识左右。因为国民政府无实际机构,到达各乡村。征兵全靠上面向下加压力,至此行之已四年多,所征的“壮丁”,如非顶卖作数,存心打算逃亡的投机分子,即是不知申辩、不知抗拒被抓来的白痴。教亦无益,劝亦无益,骂亦无益,打亦无益。射击不中标的,我自己军官学校所学尖兵、斥堠、侧卫、警戒、佯动等全部无法使用,后来我才知道,国军很多部队,不怕打仗,而怕“拖”。十四师至此已拖坏了,以后作战,全靠一连五个十个突击射手做中坚,其他士兵只能滥竽充数,在阵地前表现人多,冲锋时一拥上前,退却时无法掌握,溃败为当然之事。滇南丛山交通困难,即有给养补充也无法输送。我们下级军官和士兵一样,满身蚤虱。而最怕士兵病倒或逃亡。我们驻地附近的土匪,出资购买我们逃兵的枪械,步骑枪每支七千元。我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士兵月饷十二元至二十元。因之有些排连长,夜间将枪械锁在木架上以提防士兵携械逃亡。
我于1942 年初离开十四师,从此即未再做带兵官,以后在国军又近十年,总是当参谋。有一次和《新华日报》采访主任陆诒相遇,曾以“黄禾”笔名替重庆《新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也用本名替重庆《大公报》写过十几次文章,都表明我为国军下级军官的身份。(1950 年我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退伍,官仅少校,叙上尉。)
内战期间国民党常被攻击是贪污腐化,上级骄奢淫逸,下级与土匪乞丐无异。我们做下级军官的常觉得这种批评不公允。而最不能容忍的则是有些人在抗战期间置身事外,好像国军全部与他们无关,也作同一批评,难道以上这些情况,是我们的志愿和希望?或是只有我们这些自动从军的人单独应有的命运?可是事情如此,又无法分辩。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在台湾的同学,或者已经退伍,或者已为高级干部,官至上将中将,还是为这些事不平,有做孤臣孽子几十年,一意要洗刷这污名的决心。
我于1946 年来美进陆军参谋大学一年。1952 年再度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馆洗碗碟,做侍者,酒吧间做鸡尾酒,做园丁,在堆栈里当小工,银行里整理档案,建筑公司画蓝图糊口。读书从大学三年级读起,于1964 年得历史博士止,前后凡十二年。虽然涉猎欧美、日本、帝俄、苏联、印度历史,但是大部分精神仍是注重中国的问题。我自己教书之外,也在各处演讲过和参加集体研究工作,和不少欧美的汉学家曾见过面。对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极为仰佩。此公父母在中国传教,葬于通州。自己在中国青年会担任干事多年,第一次欧战期间,率领华工赴法,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多年,今年九十岁,最近尚与他夫人打网球。我在他《明代名人传》做过工作。他常常提醒我注意中国历史的伟大,不要因短时间的偃蹇,忽略了几千年的优点。还有对我历史观有极大的影响的则为剑桥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欧美汉学的奇葩。他也主张不作人云亦云,即阴阳五行等一套,不要先认为它做错了。一定要将它查看底细,方能断定是假是真。他现年八十四岁,我也和他联名发表过文章,亲临馨咳,得益至多。
我在他们影响之下,再掺和了自己读书旅行的经验,觉得中国传统历史,如不针对20 世纪末期解释,只是故纸陈篇、乱章滥调。反过来说,今日目前的事迹,也需要将它们的历史基点移后几百年,才能解释得清楚。因为中国的革命,是由于旧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闭关自守的国家,在非竞争性的条件下,依靠文化的特点而存在,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一与欧美做实质上的接触,造成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局面。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成立人民共和国到现在的“四个现代化”都是一浪未平,一波又起,这些接二连三的事迹已超过一世纪,其历史基点,也不可能在一时一事站得住脚跟,而需要将全部组织结构,和盘托出,我们才可以窥见它的真相。也不能以一种抽象的名词,含糊囫囵带过,如指旧社会为“封建主义”了事;而需要将这旧社会的特征,尽量缕列。我写的《万历十五年》即从此方针出发。亦即是研究现代史,不妨以四百年前做基点,如果我们能把当日朝廷做事形态、地方政府施政情形,以及法制、军备、税收、思想各种端倪前后印证时,则可视为信史。则虽叙述,可代论文。此书除中英文本外,已有德法文本,日译本亦将于年内成书。
……
编者说明 林载爵
个人经验与历史: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大历史不会萎缩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如何修订他的历史观
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拟“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答客问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
张择端为我书制图:历史小说《汴京残梦》写作纲要
1619 年的辽东战役
从珍珠港事变说起
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
1945 年的上海
风雨飘摇:1946 年初期的东北
如何了解历史人物蒋介石
关于蒋介石日记之二三事
接受历史的仲裁:如何纪念蒋公忌辰
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点看法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
资本主义与21 世纪
从历史的观点看东南亚金融危机
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的经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
掌握人类知识之全豹:《新世纪世界历史百科全书》中文版序
关系:从大历史观点看性、金钱、生死关系
道德与技术之间:黄仁宇答客问
摆脱旧传统,寻求新路向:访问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
附录 万历皇帝:长期荒废政事与消极对抗
我觉得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的都是对事情不满意,满纸谩骂,所以我想站在中间。
——黄仁宇
现在我用这结论作假说,倒看回去,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西洋史、日本史、个人观感、人物传记整幅重新修订……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
——黄仁宇
中国在20 世纪的长期革命是世界史里前所未有的事迹。以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工业条件未备,去拖垮一个先进国家,已是令人惊讶。而八年抗战之后又接着四年内战,更逼着放弃传统去接受西方标准,至此中国历史才与西洋文化汇合。
——黄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