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模特时光
我对第一次时装表演仍然记忆犹新:妈妈在观众席上朝我灿烂地微笑;我不知道该怎么走才像个时装模特(mannequin,那时都这样称走台模特),只是尽力观察其他女孩的走法,听着音乐的节奏,也许她们同样对专业模特知之甚少。妈妈称赞道:“琼,你太出色了。你是做得最好的!”我知道我不是,但下定决心成为最好的——为了她。从一开始,妈妈就是我事业上升的推动力。我只得到了在法摩尔商场店内表演的工作,她还不确定他们是否会信守承诺联系我做其他的工作。随着下一时装表演季的临近,她又找到他们。她望女成凤的决心影响了我对待模特工作的方式,使我把它当成一份严肃的全职事业,即便在我认为自己已经达到巅峰时也毫不懈怠。它激励我努力“成名”以洗雪我们两个过去的耻辱。同样强大的动力是经济需求,我们要挣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对于一些女孩来说,从事模特行业只是遇到真命天子之前的跳板,但是母亲的经历告诉我,我不能依靠男人。
那时还没有个人精修学校和模特经纪公司,都是妈妈待在家里料理我的演出契约。当时也没有模特照片集之类的东西来招揽工作,所以我只是在家里等着别人来联系我。悉尼的模特屈指可数,所以百货商场的经理们和广告人很快都认识了我,但是大约 6个月以后模特才成为我的全职工作。与此同时,我母亲的收入补贴了我买耳环的费用,我也在一家电影广告公司——查尔斯·E.布兰克斯公司(Charles E. Blanks)找到一份兼职化妆师的工作。我只是刚刚学会给自己化妆,不过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要知道,我在观察着周围环境中我所感到新鲜的一切事物的细节,这样我可以很快获取最多的信息,在大脑里过滤,然后在自己上身上呈现出最好的一面,我很喜欢这样做,哪怕是现在。我很喜欢见到那些广告里的电影女演员。
查尔斯·E.布兰克斯也资助我参加了 1945年的澳大利亚小姐选美比赛。作为比赛的募捐活动之一,参赛选手将带有她们头像的价值一先令的徽章卖掉来为战争中的遗孀筹款。我白天忙于工作,又没有足够的人脉出售这些徽章,所以我没有别的选手卖的多。我相信自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在淘汰轮之前就退出了。真是如释重负!那个阶段,我缺乏自信,受不了被陌生人评头论足。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却成了那个赛事的主办者和许多大型比赛的评委。
时装目录册的工作解决了我最初的生计问题。我最早的一些模特工作不是以照片形式呈现,而是画家的速写。这些多数都是白描画,也有一些用了不同的色调和颜色,跟我本人还是很像的。渐渐地,报纸和杂志广告的预定也多起来。后者包括为各种出版物拍摄色彩非常艳丽的封面照片,其中有《澳大利亚女性周刊》和《女性挚友》。其中一期的《周刊》封面是我穿着红白相间的格子围裙正在一个配备着最新家电的蓝色厨房里开心地做一个蓝色蛋糕的特写。我想这个形象记录了消费主义的新时代、家用电器的出现和战后社会希望妇女成为迷人的全职太太的观念。尽管厨房是我在家里最得心应手的地方,我也渴望着有一天能为家人营造美好的家居生活,但是在拍那张照片时我还不知道我的每一次事业抉择都与那个家庭主妇的形象背道而驰。
在早期的一些工作中我只化很淡的妆。我学会快速把凡士林抹在一支浅色口红上,然后涂在嘴唇和睫毛上使其具有光泽。睫毛膏是块状的,需要加水来用。因为摄影室不总是有水,我就在睫毛刷上抹点唾沫,这使睫毛膏黏黏的,但比掺水能更好地粘在我的睫毛上。如果今天还有那种睫毛膏,我还愿意用,它真的好极了,只是哭的时候脸上会淌下棕色的涓涓细流!后来我逐渐开始用腮红、粉底和眼影。我们的手提包里没有什么模特“戏法”。假睫毛和假发到 60年代才开始流行。胸罩也许会被垫高,但美容外科手术还闻所未闻。模特们需要天生丽质。也没有造型师、美发师和化妆师负责我们的妆容。我们自带化妆品、头饰、长筒袜、鞋子和其他配饰,并自己化妆,我们每次有工作时都把这些东西塞在手提包和帽箱里随身携带。丝巾是这套装备里的必需品。在表演过程中匆匆换衣服时,我们把丝巾戴在头上,两端系在颌下,这样不管衣服多么紧身,我们都不用担心妆容和头发,也不会弄脏衣服。我家里还有一个在用。
要保证我们的手提包里储备充足,我们的衣服、鞋子上档次,需要用去收入的一大部分。如果是拍商业广告,无论是销售冰箱还是某个牌子的芝士,我们都需要自备衣服。如果是卖衣服或帽子的时装广告,我们需要自带配饰。因此,我必须学会用少量的钱买到最合适我的衣服和配饰,而我的穿着打扮引起其他女性的兴趣。她们纷纷向我们寻求建议,因为全职模特很少,我们的脸尽人皆知,我们的名字家喻户晓。当时还没有太多对名人的追捧和宣传,因此我们是真正不拿腔作势的明星,同时,在澳大利亚人眼中我们也非常真实。
渐渐地,客户们开始在拍照时雇用造型师来保障模特形象符合要求,百货商场时装表演时也有服装师在一旁帮忙——有一次却害苦了我。一次,柯曾百货商场(Curzon ’s department store)的时装表演中,一个服装师在给我拉连衣裙的侧拉链时挤破了一颗痣。在我走向 T台时,血渗出了裙子。当然,那不是走秀中的唯一一次出错。法摩尔商场建造了一个大楼梯,穿着泳衣的模特要从那里走下来。我把尖底高跟鞋踩到了最高一级台阶的边上,一下子就滑倒了。我一直滑到楼梯的底部,我戴的一只贝壳手镯摔碎了,细小的贝壳随着我一级级地蹦落下来。我无可奈何,只能自己爬起来,微笑,继续,感谢观众们给了我同情的掌声。一次,我火红头发的莽撞朋友贝蒂·格林(Betty Girling)没有看到 T台的边缘,竟直接走了下去,跌到了观众席中。
为厂家的展销表演试衣服是我工作中最无聊的部分,修改衣服尺寸时需要我长久站立,还得在衣服架子间进进出出地换衣服。相反,我很期待百货商场的表演。这些激动人心、回报颇丰、时尚豪华、历时一小时的表演成为重大社会活动。我的全转身、半转身、入场、退场随着每次表演而日臻完善,后来竟然成为人人皆知的达领风格(Dally Pose)。后来在女儿的坚持下,她为其进行了注册,这一风格也成了后来学生们争相仿效的仪态之一。我注重精益求精。我携一把长柄伞,一手在上一手在下持着伞柄,展现一个优美的角度。当我在 T台尽头驻足时,我用伞尖抵地,手腕做出一个弧度拿着伞柄。我潜心研究怎样在边走边向观众微笑时优雅地摘掉手套,怎样提着短裙能让它像鼓起的风帆。我训练自己在脱掉外套时不露出衬里,将它飘然拖曳身后,继而搭在臂弯上稍微向身后弯曲,这样就不会抢了我身上衣服的风头。运动衣要轻松活泼地搭在一肩上,并要轻触衣领和口袋以引人注意。时时刻刻都要优雅娇柔:走路时只有大腿以下移动,身体要保持挺拔不动,以肩为轴摆动双臂,而不能晃动肩膀。为了显得脖子长,我想象自己的头从耳朵以上都被提起,而头顶则竭力去够天花板。表情也很重要,但我尽量不做得太夸张。尽管我比其他模特笑得多,但我对自己的表情很敏感。它不是表演技巧,而仅仅是我享受这份工作的快乐流露。很多时候母亲都在观众席中,所以我会给她一个微笑,然后将这致意推及在场的每位女士,就像每个人都是我的母亲。在戴维·琼斯(David Jones)城区店七楼举行的时装表演算得上秀场雅事。女人们戴着帽子和手套,斯文地吃着黄瓜三明治,小口品着香茗,时装模特们绕着半圆形的秀场款步而来。现场演奏的浪漫背景音乐给这样的沙龙集会更增添了几分优雅。我走秀时总是请求乐队或钢琴师演奏查尔斯·德内(Charles Trenet)的《小姐》(Mamselle)或《大海》(La Mer)。那音乐使我感觉自己似乎可以自由翱翔。另一首经常演奏的曲子是《漂亮女孩就像一首歌》(A Pretty Girl is Like a Melody)。柯曾商场总是请我参加它在布里斯班和悉尼的表演。它的老板 ,艾希礼·伯金翰(Ashley Buckingham),对我说我是他最喜欢的模特,他像父亲一样对我的事业发展提出建议。他的调情无伤大雅,我很享受他把我当成一个女人对待。女权主义已经彻底摧毁了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何益之有?我对女权主义者带来的很多东西不敢苟同。
马克·福伊百货商场(Mark Foy ’s department store)(在伊丽莎白和利物浦街拐角处仍可见其雄伟的外观)拥有最别出心裁的表演和光怪陆离的布景。但是它们与现代时装表演中的耸人听闻之举相比还望尘莫及——最近的一次表演竟然将老鼠放到台道上,让它们在衣衫单薄的模特的大腿间来往穿梭。马克·福伊的创意最多不过是当滑冰者在冰上正常滑动时,让模特们绕着滑冰场走秀。福伊的服装在当时也惊世骇俗。穿着长睡裙和薄纱睡裙表演时,我听到观众发出惊愕之声。我当时不知这骚动所为何故。后来才如梦初醒。我穿的奶油色纱网紧身上衣上的手型黑缎贴花就像在抚摸我的乳房。媒体将那件睡裙称为“惊魂”(The Gasper),而且有人向报纸抱怨说,我穿着那件衣服令人生厌。
天真是很多模特的大敌。在我从业的早年,曾有一个比我大很多的摄影师在拍照时让我脱掉衣服,还要我吻他一下。我拒绝了他,并马上离开了他的摄影室。身为模特,我可以为了摄影作品付出一切辛劳,但是我不会为了工作讨好任何一名有歹念的摄影师。我跟任何人都没提起这件事,连妈妈也没说。我想这是我的错,肯定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才勾起他的歹意。我明白低俗的请求不同于一位摄影师让你想象一些浪漫的事情,比如被一个英俊的男人揽在怀中,那是为了激发出某些情感以通过你的表情和眼神投射到照片中。对于那些表示你心有所属的照片来说,表情至关重要。我本来就没有同年龄的女孩子那么放松、随便,这件事使我在摄影师面前更加拘谨。有些人甚至认为我很高傲,以致一个模特为我辩解说:“琼并非自命不凡,她只是害羞而已。 ”
我开始从事模特行业的时候还没有模特经纪公司扮演保护模特利益的角色。所有时尚摄影师都是男性,他们可以左右客户用或不用某个模特。这使摄影师对模特有很大的控制权。当今模特经纪公司和超级名模的出现有助于打破这种权利平衡,当然还会有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人隐匿在这个行业的边缘,随时准备占那些天真女孩的便宜。谢天谢地,我有幸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和正派、有职业道德的摄影师合作,他们很多都成了我终生的朋友。在别人眼中我是可望不可及的人,因为很多人或者机构都想收藏他们拍摄的人物作品。
其中包括魅力四射、才华横溢的马克斯·杜培(Max Dupain)1,一位真正天才的摄影师。马克斯在 1949年对《周日先驱报杂志》(The Sunday Herald Magazine)替我善为说辞,称我具备一个模特应有的特质:“面部对称,皮肤细腻,眉目疏朗,牙齿整齐——还有表情自然。 ”他为我拍的照片至今仍然收藏在澳大利亚国家肖像展览馆,向专业人士和公众展出。热尔韦斯·珀塞尔(Gervaise Purcell)是另一位我喜欢的摄影师。
他给我拍了很多半身像,大多都是帽子广告。热尔韦斯曾经是早期的摄影大师之一约翰·李(John Lee)的助手,李的妻子桑德拉(Sandra)是悉尼最早的私人造型师,她帮助模特整理头发、化妆,或用一枚白铁胸针或一对耳环来烘托衣服,使照片光彩大增。热尔韦斯后来投奔位于卡斯尔雷大街(Castlereagh Street)的蒙特·卢克(Monte Luke)摄影室,那个摄影室最终被约翰·赫尔德(John Hearder)接手,成为寻常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拍家庭照或婚纱照的地方,就像每个人走过一条城市街道都可以得到一张身份摄影室(Identity Studio)给他们拍的照片那样。身份摄影室经常在市场街派驻一位摄影师,他抓拍路人的照片并给他们一张可以打印照片的票据。诺埃尔·西克(Noel Hickey)性情平和,每个模特都把他当成朋友。我还有一些早期照片是巴里·路登(Barry Louden)拍摄的。
古灵精怪的雷吉·约翰逊(Reg Johnson)周旋于他的詹特森(Jantzen)泳装主顾和为阿尔弗雷德皇子医院(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的阿兰·利雷医生(Dr Alan Lilley)拍摄癌症患者的手术之间。利雷医生对摄影非常感兴趣,我们的多次拍摄都有他和艾瑞克·龙利陪伴,艾瑞克偶尔当模特以资助他的医学学业。艾瑞克的一位教授在一本出版物上看到他和我的合影时,艾瑞克立即收到了最后通牒:模特或医学二选其一。表面看来,二者毫不相干。雷吉最终离开了时尚界去从事全职的医疗摄影,不过他受雇于詹特森时有机会沉迷于他最热爱的消遣方式:滑水。雷吉总是选霍克斯布里河(Hawkesbury River)进行外景拍摄绝非巧合。雷吉穿着泳裤站在水里,肌肉发达的身体湿淋淋的,他拍完需要的照片就逆流而上,到下一节拍摄和野餐前一直不见踪影。与雷吉和管理他摄影室的妻子珍妮(Jeannie)一起工作的日子总是非常美好。雷吉试图教我滑水,但是我并不擅长,而且,正如他喜欢的其他泳装模特——多恩·弗雷泽(Dorn Fraser)和费尔丽·福克斯(Fairy Folkes)——我不想把头发弄湿再重新梳理,也不想破坏我的妆,到下一组拍摄时还得重新化妆。外景拍摄时,如果没有公共厕所,模特们就在摄影师的汽车后座上或一棵树、一块大石头后面换衣服,有时由另一个模特拿条毛巾挡着。
和今天一样,时尚行业的工作总是提前一个季节,所以我们就得忍受在冬天穿泳装而在夏天穿皮衣的情况。和其他摄影师拍泳装照,我最远只到过邦迪(Bondi)和塔玛拉玛(Tamarama)海滩,那里耸立的岩石营造出迷人的背景。我的其他外景拍摄曾到过海德公园(Hyde Park)和禁苑(the Domain)。那时根本没有跨州或海外拍摄这回事!
淘气包(Scamp)是我代言的另一泳装品牌。它的厂主本·特纳(Ben Turner)曾是最早的伞兵,他的工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澳大利亚士兵供应降落伞,后来他把生产线改为制作泳装。每当本拜访我妈妈时,如果我们任他信马由缰,他就会数小时不停地大谈生产完美泳衣所需的技术妙招。尽管淘气包泳装被认为有点儿大胆,其两件套的泳裤总能盖住肚脐,而且前面带有一个半裙。我从来没有给比基尼做模特代言。才只几年以后,我的一些模特就被检察官奥布·莱德劳(Aub Laidlaw)赶出悉尼海滩,他测量比基尼上下装之间的距离来评价其是否体面。
前《女性周刊》的摄影师鲍勃·克莱兰德(Bob Cleland)给我拍过很多专业照片。在“二战”期间,他和厄尼·纳特(Ernie Nutt)为《周刊》拍摄了最早的彩色照片。在卡斯尔雷大街联合大楼(the Grand United Building)地下一层的《周刊》摄影室中,鲍勃和我合作愉快——我命中注定有一天会在那里开办自己的个人精修学校和模特经纪公司。“你肯定是悉尼最不性感的模特,”他会开玩笑地说,“我不明白怎么别的模特更漂亮而你却能够成功。”他说的很对。我怀疑那个据我妈妈说教她讲新的骂人话的、言语不羁的著名摄影师瑞·雷登(Ray Leighton)对我也有同感。在对《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提起我作为模特的可塑性时,瑞评论说我“既适合牙膏也适合长裙”。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像恭维。他曾在给我拍摄的一张专业照片上写道:“送给我最喜爱的模特。”——但是我敢打赌他对所有的女孩都这样说。
劳里·勒瓜伊享有很高的艺术声誉,但是我发现和他合作并非易事。他性格怪戾,而且我相信他并不喜欢我。有些模特会跟他顶嘴,但是我对他的生硬态度很敏感。他的妻子,安妮·普莱斯 -琼斯(Anne Price-Jones),当然知道怎么跟他顶嘴。作为法摩尔时装摄影的主管,当安妮在劳里的摄影室中监督法摩尔的照片拍摄时,她会直抒己见。他们把摄影室转变成了唇枪舌剑的战场。他们不稳定的婚姻没有像他们共同拍摄的照片那样历时久远。
得益于新闻有限公司(News Limited)一群退休摄影师成立的社交圈——塔茨塔拉俱乐部(Tutsitala Club),使我与很多摄影师的友谊得以保持。这些老男孩邀请我成为两名女会员之一[另一位是阿黛尔 ·赫尔利(Adele Hurley),著名南极摄影师弗兰克 ·赫尔利(Frank Hurley)的女儿]。俱乐部的前主席罗恩·艾尔代尔(Ron Iredale)和合伙人梅尔瓦(Melva)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罗恩曾经给我经纪公司的很多模特拍照,做《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三版女郎”,她们在他手上所托得人。他和各位绅士一样深情地称我为“小姐”,我也乐而受之。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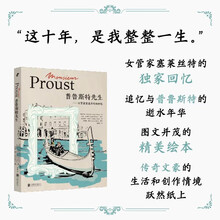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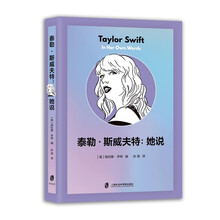


我会以她为榜样,做好自己,爱护环境,影响和造福于行业和社会。
——诺亚财富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汪静波
真正的美丽不会随岁月而流逝,充满探索未知的激情,保持温柔美好的内心,享
受工作的乐趣,感恩家庭的温暖。
——中国银行江苏分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 张怡
每一个走近她的人,才会真正明白什么是优雅,什么是魅力,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心底里流淌出的爱!那是岁月无法磨去的痕迹,那是从人性里绽放出来的光彩!
——沪江首席教育官 吴虹
微笑是一种力量,礼仪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修养。有了自信的微笑和优雅的礼仪,你的美丽从此就会插上翅膀。
——新丝路娱乐机构总裁 宁佐勤
Miss Dally 用自已传奇的一生,带给中国女性的不仅是外表、举止的优雅,更多是
爱和感恩,勇敢和自信,这是我们在中国共同的梦想。
——国际知名设计师、法国Cherry Chau 创始人 Cherry 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