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基因是固有的。我们不能只选择偏向于遗传父母一方的完美视力,而不遗传另一方的散光,或者选择比我们现在更高的身高。这并不是说相同的基因总会有完全相同的表示方式:营养的改善会影响孩子的身高,教育的改进会影响她在智商测试中的表现;同卵双胞胎也不是完全相同——他们可以选择改变他们的外貌或培养不同的技能、学习不同的科目、实践不同的宗教,但通过这些方式他们也不能选择改变他们的基因。关于文化我们可以进行选择,但关于自然我们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简单地进行选择。例如,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基因的遗传。我们不能选择天生没有视力缺陷,然而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很多选择的国家里,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是戴有架眼镜还是戴隐形眼镜来纠正我们的视力,或者甚至选择做手术。我们也可以选择如何应对文化的传承。我们不能选择不出生在有特殊宗教信仰、讲特殊语言或有特殊教育理念的家庭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是否也接受那个宗教,是否要去学习讲一种不同的语言、是否也认同那种教育理念。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对于文化传承的反应也会传递给我们的子孙,而我们对基因遗传的反应却不会以同样的方式传递给子孙。眼科手术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基因:无论她是在做手术之前还是在做手术之后怀孕,她的孩子们都同样有可能遗传她的弱视力。然而,如果她反对她父母的无神论,而成为基督徒,那么她的孩子将可能被培养成基督徒而非无神论者。她的父母不重视教育,以致她还没有学会识字和计算就离开了学校。如果她对此感到遗憾的话,那么她可能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也会向她的孩子传递一种与她父母给她的、完全不同的教育态度。
这种文化是人类独有的。非人类物种,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用语言或工具,能够学习彼此并形成一种所谓的文化,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仍在继续,但毫无争议的是其他物种都不能形成像人类文化那样博大精深的东西。很多物种的遗传倾向是由接触环境刺激所决定的:例如,刚孵化的小鹅或小鸭有一种遗传倾向,即与它们遇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建立社交性联系,而这种倾向取决于任何可以提供适当环境刺激的移动物体。基因引起了这些遗传倾向,就像物种在它们的基因中所携带的信息一样,很多物种在它们的大脑中也携带着信息:它们能过形成并记住事件之间的联系,随后它们的行为会受到这些联系以及环境和生物学的影响,就像巴甫洛夫(Pavlov)著名实验中的狗一听到铃声就流口水一样,因为它们已经知道把铃声和食物的到来联系起来。除了像这些它们自己学会的信息之外,一些物种成员还能够模仿同种个体的行为:这些生物的行为受其基因和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它们大脑中的信息和其他生物行为的影响。目前据我们所知,仅有一种物种成员携带着周围的外在信息以及在它们大脑和基因中的信息。人类的行为受其基因和环境的影响,也受到我们自己大脑中的信息和其他人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同种个体大脑中信息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言语和书面符号接触那些信息。在使信息免受基因和大脑的限制方面,我们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才有了人类文化。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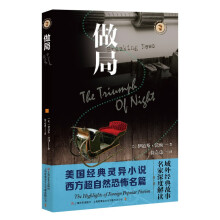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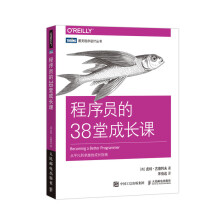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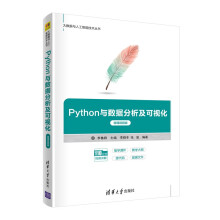



——Robert Aunger, 生物人类学家,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学院
★作者将她的观点和证据在本书和她的上一部著作《自私的模因》中清晰地罗列出来。本书的章节分布清晰,很多引文都引自最近的语言学、模因论、生物学和文化进化理论研究,对我们理解人类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Rebecca Wells-Jopling,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发展与应用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