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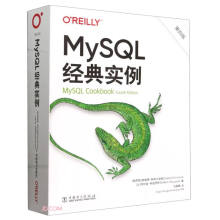
1.作者是北大在任时间很长的校长,亲历了近代七十年每一件大事,他的人生本就是一部微观的近代史。书中对很多民国名人轶事有精彩的侧面描写。
2.他是那个动荡时代立志报国的年轻留学生的典型,与现在的海外留学大军有所共鸣。
3.作者在清末的乡村经历,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文笔十分生动有趣。
4.本书曾被视作台湾青年人手一册的人生教科书。
蒋梦麟以饱含风趣和人生智慧的笔触,娓娓道来他成长的故事,同时也映照出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从传统浓厚的余姚到开放繁华的上海,眼见社会的种种变化;再到留学海外,感受文化的差异,思考国族的未来;最后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他始终秉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掌握着北大之舵。在抗战时期,他站在历史台前,用温和有力的双手保护学生;在和平时代,又把五四精神成功推广于农村建设。他是那时青年人的启蒙者,影响一直到现在。
1.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康之家。兄弟姊妹五人,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位哥哥,一位姊姊。我出生的前夕,我父亲梦到一只熊到家里来,据说那是生男孩的征兆。第二天,这个吉兆应验了,托庇祖先在天之灵,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儿子。我大哥出生时,父亲曾经梦到收到一束兰花,因此我大哥就取名梦兰。我二哥也以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不用说,我自然取名为梦熊了。姊姊和三哥诞生时,父亲却没有梦到什么。后来在我进浙江高等学堂时,为了先前的学校里闹了事,梦熊这个名字入了黑名单,于是就改为梦麟了。
我出生在战乱频仍的时代里。我出生的那一年,英国从中国拿走了对缅甸的宗主权;出生的前一年恰恰是中法战争结束的一年,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那一年让渡给法国。中国把宗主权一再割让,正是外国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本土的序幕,因为中国之保有属国,完全
是拿它们当缓冲地带,而不是为了剥削它们。中国从来不干涉这些边缘国家的内政。
这情形很像一只橘子,橘皮被剥去以后,微生物就开始往橘子内部侵蚀了。但是中国百姓却懵然不觉,西南边疆的战争隔得太远了,它们不过是浩瀚的海洋上的一阵泡沫。乡村里的人更毫不关心,他们一向与外界隔绝,谈狐说鬼的故事比这些军国大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但是中国的国防军力的一部却就是从这些对战争不感兴趣的乡村征募而来的。
慢慢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之后,我注意到村里的人讲起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时,却比谈当前国家大事起劲多了。我们乡间呼太平军为长毛,因为他们蓄发不剃头。凡听到有变乱的事,一概称之为长毛造反。大约在我出生的三十年前,我们村庄的一角曾经被太平军破坏。一位
木匠出身的蒋氏族长就参加过太平军。人们说他当过长毛的,他自己也直认不讳。他告诉我们许多太平军掳掠杀戮煮吃人肉的故事,许多还是他自己亲身参加的。我看他的双目发出一种怪光,我父亲说,这是因为吃了人肉的缘故。我听了这些恐怖的故事,常常为之毛骨悚然。
这位族长说,太平军里每天要做祷告感谢天父天兄(上帝和耶稣)。
有一天做祷告以后,想要讨好一位老长毛,就说了几句“天父夹天兄,长毛夺咸丰”一套吉利话。老长毛点头称许他。他抖了,就继续念道:“天下打不通,仍旧还咸丰。”“妈”的一声,刀光一闪,从他头上掠过。从此以后,他不敢再和老长毛开玩笑了。
这样关于长毛的故事,大家都欢喜讲,欢喜听。但是村里的人只有偶然才提到近年来的国际战争,而且漠不关心。其间还有些怪诞不经的胜利,后来想起来可怜亦复可笑。事实上,中国军队固然在某些战役上有过良好的表现,结果却总是一败涂地的。
2. 我在六岁时进家塾,一般小孩子差不多都在这个年岁“启蒙”的。事实上我那时才五岁零一个月的样子,因为照我家乡的算法,一个人生下来就算一岁了。家塾里的书桌太高,我的椅子下面必须垫上一个木架子之后我才够得上书桌,因此我坐到椅子上时,两只脚总是悬
空的。
我最先念的书叫《三字经》,每句三个字,而且是押韵的,因此小孩子记起来比较容易。事隔六十多年,我现在还能背出一大半,开头几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性善论是儒家人生哲学和教育原理的出发点,这种看法曾对十八世纪的大光明时代的法国学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虽然我现在已经懂得甚么叫“性本善”,在当时却真莫名其妙。
我恨透了家塾里的生活。有一天,我乘先生不注意我的时候,偷偷地爬下椅子,像一只挣脱锁链的小狗,一溜烟逃回家中,躲到母亲的怀里。
母亲自然很感意外,但是她只是很慈祥地问我:“你怎么跑回家来了,孩子?”
我答道:“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
“你不怕先生吗?他也许会到家里来找你呢!”母亲笑着说。
“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我急着说。
母亲并没有把我送回家塾,那位先生也没有找上门来。
第二天早上,奶妈喊醒了我,对我说了许多好话,总算把我劝回家塾。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吃软不吃硬。好好劝我,要我干什么都行,高压手段可没有用。经过奶妈一阵委婉的劝谏,我终于自动地重新去上学了。
3. 上海在一八九九年前后还是个小城, 居留的外国人也不过三四千,但是这些洋人却都趾高气扬,自视甚高。市政倒办得不错,街道宽大清洁,有电灯,也有煤气灯。我觉得洋人真了不起,他们居然懂得电的秘密。他们发明了蒸汽机,又能建造轮船。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新的神,原先心目中的神佛在我接受科学知识之后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有时候他们又像是魔鬼,因为他们不可一世的神气以及巡捕手中的木棒使我害怕,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犬居华人之上,这就很够人受的了。在我的心目中,外国人是半神半鬼的怪物,很像三头六臂的千手观音,三只手分别拿着电灯、轮船、洋娃娃,另外三只手分别拿着巡棍、手枪、鸦片。从某一边看,他是天使;从另一边看,他却是魔鬼。
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总不出这两个极端,印象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李鸿章看到西方文明丑恶狰狞的一面,因此决定建立海军,以魔鬼之矛攻魔鬼之盾。光绪帝看到西方文明光明和善的一面,因此想建立新式的学校制度。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看到可憎的一面,想用中
国的陈旧武器驱逐魔鬼。
我们在上海住了将近两年。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慈禧太后已经命令各省总督把所有的外国人一齐杀光。于是我们连夜举家迁离上海,那是一九〇〇年的事,也就是义和团战争的开始。义和团的人自称能用符咒对付刀枪子弹,拳术也是训练节目之一。因此,义和团有拳匪之称。他们预备破坏一切外国制造的东西,同时杀死所有使用外国货的人。他们要把运进这些可恶的外国货而阻绝他们生路的洋人统统杀光。把这些害人的外国货介绍到中国来的教会、学校、传教士、基督徒都罪无可逭。用刀剑、法术把这些人杀光吧!放把火把外国人的财产统统烧光!
朝廷本身也想把康有为、梁启超介绍进来的外国思想一扫而光,免得有人再搞什么维新运动。义和团要消灭物质的外国货,慈禧太后则想消灭精神上的外国货。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反正都是外国货,都是外国人造的孽。杀呀!杀光外国人!工业革命开始时,
英国人曾经捣毁了威胁他们生活的机器。义和团做得更彻底,他们要同时破坏血肉构成的“机器”。
南方的人对外国人的看法稍有不同,他们欢迎外国货,他们不觉得外国货是盗匪的起因,他们认为毛病在于清室的苛捐杂税以及官吏
4. 我们离开那所教会学校以后,我们的学生会自行筹办了一个学校,取名“改进学社”。这个名称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章炳麟给我们起的。这位一代大儒,穿了和服木屐,履声郭橐,溢于堂外。他说,改进的意思是改良进步。这当然是我们愿意听的。我们的妄想是,希望把这个学校办得和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一样,真是稚气十足。但是不久我们就尝到幻灭的滋味。不到半年学生就渐渐散了。结果只剩下几个被选担任职务的学生。当这几位职员发现再没有选举他们的群众时,他们也就另觅求学之所去了。我自己进了浙江高等学堂。我原来的名字“梦熊”已经入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因此就改用“梦麟”注册。我参加入学考试,幸被录取。
5. 初到美国时,就英文而论,我简直是半盲、半聋、半哑。如果我希望能在学校里跟得上功课,这些障碍必须先行克服。头一重障碍,经过四个月的不断努力,总算大致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第二重障碍要靠多听人家谈话和教授讲课才能慢慢克服。
教授讲课还算比较容易懂,因为教授们的演讲,思想有系统,语调比较慢,发音也清晰。普通谈话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包括一连串互不衔接而且五花八门的观念,要抓住谈话的线索颇不容易。到剧院去听话剧对白,其难易则介于演讲与谈话之间。
最困难的是克服开不得口的难关。主要的原因是我在中国时一开始就走错了路。错误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矫正过来。其次是我根本不懂语音学的方法,单凭模仿,不一定能得到准确的发音。因为口中发出的声音与耳朵所听到的声音之间,以及耳
朵与口舌之间,究竟还有很大的差别。耳朵不一定能够抓住正确的音调,口舌也不一定能够遵照耳朵的指示发出正确的声音。此外,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对中国人并不太亲热,难得使人不生身处异地、万事小心的感觉。我更特别敏感,不敢贸然与美国人厮混,别人想接近我
时,我也很怕羞。许多可贵的社会关系都因此断绝了。语言只有多与人接触才能进步,我既然这样固步自封,这方面的进步自然慢之又慢。后来我进了加大,这种口语上的缺陷,严重地影响了我在课内课外参加讨论的机会。有人问我问题时,我常常是脸一红,头一低,不知如何回答。教授们总算特别客气,从来不勉强我回答任何问题。也许他们了解我处境的窘困,也许是他们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特别加以原谅。无论如何,他们知道,我虽然噤若寒蝉,对功课仍旧很用心,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多半列在乙等以上。
6.初次晋谒孙先生。他住在唐人街附近的史多克顿街的一家旅馆里。我进门的时候,因为
心情紧张,一颗心怦怦直跳,孙先生在他的房间里很客气地接见我们。房间很小,一张床,几张椅子,还有一张小书桌。靠窗的地方有个小小的洗脸盆,窗帘是拉上的。
刘麻哥把我介绍给这位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孙先生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引力,任何人如果有机会和他谈话,马上会完全信赖他。他的天庭饱满,眉毛浓黑,一望而知是位智慧极高,意念坚强的人物。他的澄澈而和善的眼睛显示了他的坦率和热情。他的紧闭的嘴唇和坚
定的下巴,则显示出他是个勇敢果断的人。他的肌肉坚实,身体强壮,予人镇定沉着的印象。谈话时他的论据清楚而有力,即使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也会觉得他的观点无可批驳。除非你有意打断话头,他总是娓娓不倦地向你发挥他的理论。他说话很慢,但是句句清楚,使人觉
得他的话无不出于至诚。他也能很安详地听别人讲话,但是很快就抓住人家的谈话要点。
后来我发现他对各种书都有浓厚的兴趣,不论是中文书,或者英文书。他把可能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书。他读书不快,但是记忆力却非常惊人。孙先生博览群书,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
他喜欢听笑话,虽然他自己很少说,每次听到有趣的笑话时总是大笑不止。他喜欢鱼类和蔬菜,很少吃肉类食物。喜欢中菜,不大喜欢西菜。他常说:“中国菜是全世界最好的菜。”
在开始讲话以前,他总先估量一下他的听众,然后选择适当的题目,临时决定适当的讲话的方式,然后再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意见。他能自始至终把握听众的注意力。他也随时愿意发表演说,因为他有惊人的演说天才。
孙中山先生对人性有深切的了解,对于祖国和人民有热烈的爱,对于建立新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有深邃的见解。这一切的一切,使他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无可置辩的领袖。他常常到南部各州、东部各州去旅行,有时又到欧洲,但是经常要回到旧金山来,每次回到旧
金山,我和刘麻哥就去看他。
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大概晚上八点钟左右,孙先生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和一顶常礼帽,到了《大同日报》的编辑部。他似乎很快乐,但是很镇静。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据他从某方面得到的消息,一切似乎很顺利,计划在武汉起义的一群人已经完成部署,随时可以采取行
动。两天以后,消息传至旧金山,武昌已经爆发革命了。这就是辛亥年十月十日的武汉革命,接着清朝政府被推翻,这一天也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7. 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经政府授意把“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泄漏了,那时我正在纽约读书。这消息使西方各国首都大为震惊。抵制日货运动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以示抗议,但是日本军舰已经结集在中国的重要口岸,同时日本在南满和山东的军队也已经动员。
民国四年即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也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四个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袁世凯终于在两天之后接受“二十一条”要求。
后来情势演变,这些要求终于化为乌有,但是中国对日本的钦慕和感激却由此转变为恐惧和猜疑。从此以后,不论日本说什么,中国总是满腹怀疑,不敢置信;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加以警戒。日本越表示亲善,中国越觉得她居心叵测。
我们的东邻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爱你们一样地爱我们?”我们回答说:“你们正在用刺刀谈恋爱,我们又怎么能爱你们?”“九一八”事变前几年,一位日本将官有一天问我:“中国为什么要挑拨西方列强与日本作对?”
“为保持均势,以免中国被你们并吞。”我很坦白地回答。
“日本并吞中国!我们怎么会呢?这简直是笑话。”
“一点也不笑话,将军。上次大战时列强自顾不暇,日本不是曾经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吗?如果这些要求条条实现。日本不是就可以鲸吞中国吗?”
“哦,哦——?”这位将军像是吃惊不小
“一点不错。”我直截了当的回答。
8. 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以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
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处就在著名的西湖旁边,临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隐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他最后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我因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起这副重担,我于是在七月间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乘了火车,前赴北京。到了北京大学,初次遇见了当时北大学生,以后任台大校长的傅孟真(斯年),现在台湾任馆长的罗志希(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他们约好了好多同学,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出版了一种杂志,叫做《新潮》,向旧思想进攻。
我现在写《西潮》,实在自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然而“五四”之起因,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主义之崩溃,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所以毕竟还是与西潮有关。
我到校以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当时的演说中,有如下一段:“……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暴风雨过去以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九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9.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早晨,行辕顾问马素打电话来通知我,孙先生已入弥留状态。我连忙赶到他的临时寓所。我进他卧室时,孙先生已经不能说话。在我到达前不久,他曾经说过:“和平、奋斗、救中国。……”这就是他的最后遗嘱了。大家退到客厅里,面面相觑。
“先生还有复原的希望吗?”一个国民党元老轻轻地问。大家都摇摇头,欲言又止。
沉默愈来愈使人感到窒息,几乎彼此的呼吸都清晰可闻。时间一分一秒无声地过去,有些人倚在墙上,茫然望着天花板。有些人躺在沙发上,闭起眼睛沉思。也有几个人蹑手蹑脚跑进孙先生卧室,然后又一声不响地回到客厅。
忽然客厅里的人都尖起耳朵,谛听卧室内隐约传来的一阵啜泣声,隐约的哭声接着转为号啕痛哭——这位伟大的领袖已经撒手逝世了。我们进入卧室时,我发现孙先生的容颜澄澈宁静,像是在安睡。他的公子哲生先生坐在床旁的一张小凳上,呆呆地瞪着两只眼,像是一个石头人。孙夫人伏身床上,埋头在盖被里饮泣,哭声悽楚,使人心碎。汪精卫站在床头号啕痛哭,同时拿着一条手帕擦眼泪。吴稚晖老先生背着双手站在一边,含泪而立。覆盖着国旗的中山先生的遗体舁出大厅时,鲍罗廷很感慨地对我说:如果孙先生能够多活几年,甚至几个月,中国的局势也许会完全改观的。
协和医院检验结果,发现中山先生系死于肝癌。
孙先生的灵柩停放在中央公园的社稷坛,任人瞻仰遗容。一星期里,每天至少有两三万人前来向他们的领袖致最后的敬意。出殡行列长达四五里,执绋在十万人以上,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生、教员、政府官员、商人、工人和农人。
10. 西安事变的消息广播全国之后,老百姓无不忧心如焚,妇女小孩甚至泣不成声。全国各方纷电西安,劝谏张学良三思而行。蒋夫人和宋子文先生不顾身入虎穴的危险,径行飞往西安。张学良在全国舆情压迫下,终于改变初衷,最后护送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安返洛阳。
蒋委员长在西安未有脱险消息以前,美国大使馆的美军陆战队营房里曾举行一次舞会,参加的有各使领馆人员,我也是来宾之一,一位塔斯社的记者斯拉配克问我为什么不跳舞。我告诉他正为蒋委员长的安全担忧,所以无心跳舞,他很平静地对我说:“你放心好了,他马上就会出来。他决不会有什么意外。”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说:“但愿你的预言能成事实。”
第二天晚上快吃饭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喂,这里是中央社。蒋委员长已经安抵洛阳,并已转飞南京。”这消息太好了,简直不像真的,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打电话给胡适之,他正在请客。我把消息告诉他以后,客人的欢呼声从电话筒里都清晰可闻。号外最先送到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观众之间马上掀起一片欢呼声,弄得戏台上唱戏的人们莫名其妙。大约半小时之后,北平严冬夜晚的静寂忽然被震耳的鞭炮声冲破了,漆黑的夜空中到处飞舞着爆竹焰火的火星。
我有一位朋友当时正搭乘火车从南京到上海,火车驶近苏州时,车中乘客被苏州城内的一片爆竹声弄得莫名其妙。到达车站时他们才得到这个好消息,乘客也都想放几个鞭炮以发泄抑积已久的情绪,但是车站上买不到爆竹,于是车上的女学生们就放开喉咙高唱起来了。
11.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前往上海车站,准备搭火车回北平。进车站后,发现情势迥异平常,整个车站像个荒凉的村落。一位车站警卫是认识我的,他告诉我,已经没有往外开的车子。“看样子,日本人马上要发动攻击了。”他说,“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恐怕这里随时要出事呢!”
那天夜里,我突然被一阵炮声惊醒,接着是一阵轧轧的机枪声。我从床跳起来,随着旅馆里的人跑到屋顶观望。天空被车站附近射出来的炮火映得通红。日本侵略似乎已经追在我脚跟后面,从北方到了南方,我所住的十余层高楼的旅馆在租界以内,日本炮火不会打过来
的。我同一班旅客都作隔岸观火。隆隆的大炮声,拍拍的机枪声终宵不断。第二天早晨,我再度爬上屋顶,发现商务印书馆正在起火燃烧,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好几架日本轰炸机在轮番轰炸商务印书馆的房子。黑烟冲天,纸片漫天飞舞,有些碎纸片上还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字样。
日本已经展开对上海的攻击。结果引起一场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以前最激烈的战事,但是中国终于被迫接受条件,准许日本在上海驻兵。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
12.一两个月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日本宪兵到北大来找我。“日本在东交民巷的驻防军请你去一趟,谈谈他们希望了解并且需要你加以解释的事情。”他这样告诉我。我答应在一小时之内就去,这位日本宪兵也就告辞回去了。
我把这件事通知家里的几位朋友之后,在天黑以前单独往东交民巷日本兵营。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以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请坐。”我坐下时,用眼角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电话又响了,他再度转身对我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
西 潮
序 言
英文版序
丹麦文译者序
前言 边城昆明
第一部 清朝末年
第一章 西风东渐
第二章 乡村生活
第三章 童年教育
第四章 家庭影响
第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六章 继续就学
第七章 参加郡试
第八章 西化运动
第二部 留美时期
第九章 负笈西行
第十章 美国华埠
第十一章 纽约生活
第三部 民国初年
第十二章 急剧变化
第十三章 军阀割据
第十四章 知识分子的觉醒
第十五章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第十六章 扰攘不安的岁月
第四部 国家统一
第十七章 宪政的试验
第十八章 中山先生之逝世
第十九章 反军阀运动
第二十章 国民党之出掌政权
第五部 中国生活面面观
第二十一章 陋规制度
第二十二章 社会组织和社会进步
第二十三章 迷人的北京
第二十四章 杭州、南京、上海、北京
第六部 抗战时期
第二十五章 东北与朝鲜
第二十六章 战云密布
第二十七章 抗战初期
第二十八章 战时的长沙
第二十九章 日军入侵前夕之越南与缅甸
第三十章 大学逃难
第三十一章 战时之昆明
第七部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第三十二章 中国与日本——谈敌我之短长
第三十三章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
第三十四章 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
新 潮
引 言
第一章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第二章 改革方案的施行
第三章 土地问题
第四章 大后方的民众生活
第五章 中国文化
外 篇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蔡先生不朽
追忆中山先生
一个富有意义的人生
忆孟真
谈中国新文艺运动
一、北京大学与学术自由
二、鲁迅兄弟
三、绍兴师爷与《阿Q 正传》
四、胡适之先生与白话文运动
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六、陈独秀的最后主张
七、西欧个性主义思想的引进
八、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九、台湾文艺界继承了西欧思想的遗产
十、台湾中国文艺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附 录
《西潮》与《新潮》(刘绍唐)
评介《西潮》(王德昭)
推荐人的话(沈君山)
蒋梦麟生平
他(蒋梦麟)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去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胡 适(著名学者、思想家、文学家)
我何敢序孟邻先生的大著,只能引王安石两句诗以形容他的写作和生平。诗云:“看似平常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
——罗家伦( 教育家、思想家)
蒋梦麟先生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行政的长才。三十出头就代理蔡元培先生为北大校长,后来真除,又在政府担任过教育部长等职。茫茫中国,何去何从?他是有相当的感慨的。
——沈君山 (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五十年间的史事,作者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见证,有价值的见证,莫过于与教育有关、作者所亲历的三件事:一是辛亥革命时期学生革命思想的来源,二是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革命及爱国运动,三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的组织与发展。
——张玉法 (著名历史学家)
本书是一位饱经世故的中国智者的自述。他叙述他的不平凡的时代和他自己的不平凡的阅历,而以极其平易近人的口吻道出。书中的每一页都闪耀着他的晶莹的智慧,缀以隽永的妙语和幽默的讽刺,佳趣洋溢,而且发人深省。
——王德昭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蒋先生时常提起被许多读他书的年轻人所感动的故事。可是,正当万千读者期待读他那“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几十年的经验之书时,他却不幸逝世了。这无论对中国知识界以及他所念念不忘的青年一代,都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刘绍唐 (台湾《传记文学》创办人、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