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冲绳岛被逼出的残忍
一条弯弯曲曲的村路,尽头处,小山起伏葱笼,掩映着他相相帮起来的那所房子。这里是蒙太瓦拉大学校园。从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到这里,车行45分钟。
我是被他1981年出版的那本引人注目的回忆录《帛琉②冲绳旧事》招来的。
他是这所大学的生物学教授,骨细身长,举止文雅。“我的主要兴趣是鸟类学。我从小在莫贝尔③就喜欢看鸟儿。你不觉得好笑吗?一个在前线当过海军陆战队的人,居然对鸟类,对大自然感兴趣,人们总觉得玩鸟不是男子汉的行当。”
关于那场战争,实在说不上有什么英雄气概可言。我们简直像一群吓坏了的孩子,不得不干就是了。都说我一举一动不像海军陆战队的老兵。那么,陆战队老兵究竟应该什么样呢?人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好莱坞模式。不用说,我根本不像约翰·韦恩④!我们打仗,无非想熬过去,活着回家干自己爱干的事罢了。
我那年才19岁,是1944年6月入伍的新兵。参加瓜达尔卡纳
②帛琉,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在日本关岛西南。
③莫贝尔,美国阿拉巴马州西南部的一个海港。
④约翰,韦恩,好莱坞演“硬汉”的著名男影星,主演过多部西部片。
尔岛①战役的这个师,80%的兵都在21岁以下,比一般部队士兵的年龄小得多。
我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战争。一种是前线斗兵的战争,你得一直打下去,打到受伤或者送命算完。要不就是走运,被人替换下来。另一种是后勤人员的战争。在太平洋战场,前线有一个步兵,后边就有十九个后勤。当后勤的对战争的理解跟我们不同。前线的兵一天又一天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死而后已。
你能坚持下去,唯一可以凭借的东西只是对战友的信任。那不仅仅是一种友谊。我在战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事情。从别的部队回来的人说,在欧洲战场见过这种事。唉,那时候,我也不止一次希望能花上哪怕100万元给自己买一处枪伤。(淡笑)比方说,打掉一个脚趾。但是,比死更可伯的是战友的那种激愤。你怎么能辜负他们呢?哪一种比军旗比祖国还要有力量的感情啊!
跟日本人打,尽是在夜里。他们穿过防线,悄悄摸进来扔手榴弹,要不就端着刺刀,舞着马刀,冲进来,整夜折腾。弟兄们想打个盹,你就得呆在那儿站岗。然后就轮到你打盹了。就这么白天黑夜打了歇,歇了打,无非就是想法子活下来。唯一的办法是不等他们消灭你,先把他们消灭掉。我所了解的战争是绝对野蛮的。
日本人依照他们自认为正确的准则——武士道——打仗,这就是:绝不投降。如果不身临其境,跟那些面临绝境但绝不投降的人搏斗,你是没法理解这一点的。你想去搭救一个日本兵,他多半会拉响一颗手榴弹,跟你同归于尽。在他们心目中,当俘虏是耻辱。对于我们来说,当然也是不堪的。巴丹半岛?发生的事,
①瓜达尔卡纳尔岛,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中的一个岛。
?巴丹半岛,在马尼拉湾的一个半岛,属菲律宾。1942年9月日军玫攻占该岛,在岛上虐待美军俘虏,害死了好几千人。
我们都很清楚。
冲绳战役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先前大概是野战医院的地方,发现了一张铺上躺着一个衰弱不堪的日本兵。我们在巡逻,大雨下了整整两星期,掩体里面都是水。有一个日本兵身上只穿一块兜裆布。他大概只剩下90磅了,让人挺可冷。我的同伴把这个人扶起背出来放在泥地上,当时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安顿他。
我们坐在自已的钢盔上,等卫生兵来给这个日本兵检查。他看起来挺温顺。我们还以为他起不来了。谁知他突然从兜裆里掏出一颗日本手榴弹,猛地拉出导火线,在拳头上狠砸,想把盖子打开。他想把我们跟他一起炸成肉酱。我大喊:“当心!”于是只听得我那位战友骂道:“你个狗娘养的!你想找死……”,说着,抽出0.45口径手枪,对准日本兵的眉心开了一枪。
这就是我们要对付的事情。我不喜欢暴力,可是有时候又无法不使用暴力。我不愿意看那种宣扬暴力的电视片。我讨厌一切可怕的东西。而那时候,我天天在恐惧当中,以至于连害怕都厌倦了。我见过一些当兵的,经过三次战役都安然无恙,但是到了最后一天还是在冲绳难逃一死。你就知道,人人朝不保夕,只有眼前这会儿是活着的。
我们渐渐形成了一种对别人毫无怜悯的态度,因为他们对我们从不怜悯。战争,那是一桩毫不宽恕的、十足野蛮的书。在帛琉,我第一次在近处看清一张日本兵的脸。那人被打死了,我的一个伙伴像拆卸枪炮似的把他翻过来掉过去,撕开衣服搜寻“纪念品”。我得承认,这件事确实使我很不自在。弟兄们把他拖来拖去,就像对牲口似的,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那个日本人也是个人呀,但是没过多久,我也就克服了这种感情。我的许多战友被打死了,加上疲劳、压力,没多久,那一层文明的外壳就磨得相当薄了。
我还见过人们无缘无故开枪打死日本伤兵,然后从他们嘴里敲下金牙来,日本兵多数都镶金牙,我记得有一次在帛琉,我也动过念头,想要搞点儿金牙。我的一位战友在一只袜子里就装有一大把金牙。你只要拿出你的“卡把”刀,一种拼杀用的匕首,就成。(他拿出一把七寸长的刀子给我看)我们每人都有一把这种匕首,因为敌人有时候会在黑夜摸到掩体里面打你。我们在冲绳岛半月山大约呆了十天,每天夜里都发生这种事情。
取金牙的方法是把刀尖顶到死者的牙齿上——我见过有的弟兄对受伤的日本兵也这么干——然后捶打刀柄,使牙齿松动。你会说,我们美国的小伙子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可是如果你在环境影响之下变残酷野蛮了,那是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的。林白(1942—1974)美国飞行家,于1927年首次完成横渡大西洋不着陆飞行。)在菲律宾旅行的时候,对于美国兵谈论日本兵时的态度大吃一惊,当时确实就是这么野蛮,我们当时确实是野蛮人。
我弯下腰正要去做摘除手术(大兵们经常这么叫),一位名叫“卡斯威尔大夫”的海军卫生兵(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安息!)说:“‘大锤’,你在干什么?”我说:“大夫,我也想给自己弄几个金牙。”他很轻很轻地说:“你没有必要干这种事。”我说:“别人都在这么干。”他说:“你家里人知道了该怎么想呢?”“哟,我爸爸是莫贝尔的医生。他也许会觉得这怪有趣儿呢!”他又说:“得啦,你弄不好会沾上什么细菌的。”我说:“这我倒没想过,大夫。”后来一回想,我才明自,卡斯威尔何尝是担心细菌,他是不想让我朝着那条丧尽人性的道路再迈出一步啊。
我见过一个蹲着的日本机枪手,被我们的勃朗宁自动步枪手打死了,连天灵盖儿也给揭了。那天下了整整一夜的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竟然没有倒下去,直挺挺地坐在那挺机关枪前,两只胳膊耷拉在两边,眼睛瞪得老大。下了一夜雨,他的脑壳里面积满了雨水。当时,我们正好垫着钢盔在四下坐着,等来人换班。我看见我的一个伙伴从三英尺开外往那脑壳里扔珊瑚石碎块,扔进一块,就溅起一片水花,这使我想起小男孩往水坑里扔石子的情形。这简直让人没法相信。他这样做,并没有丝毫恶意。他是个很文静的小伙子,现在成了一个20世纪的野蛮人。
我们攻破日军在冲绳的防线的时候,我端着一支汤姆生式冲锋枪,走进一间小茅屋去。一个老太婆坐在一进门的地方,她伸出一双手,上面刺着古代计时用的沙漏的图案。这说明她是冲绳人。她说:“不是日本人。”她解开身上的和服,指着下腹部一处大伤口,已经感染化脓,肯定活不了了,显然极其痛苦。她很可能是双方打炮或者空袭的时候受伤的。
她颤巍巍地把手转过来,抓住我的冲锋枪枪口,拉着对准自己的脑门,另一只手比划着,让我扣扳机。我把枪猛地甩开,对卫生兵喊道:“这儿有个重伤的土人老太婆。喂,大夫,你来看看。”那时候,我们管太平洋地区的当地居民都叫土人。
他给老太婆包扎了伤口,又吩咐后头的人让她撤离。我们正要离开那儿,忽听得步枪响了一声。卫生兵跟我赶忙蹲下,“这是M-1式步枪的枪声,对吧?”那是美国枪。我们回头看那茅屋,心里想,也许屋子里藏着一个日本狙击手,那老婆子是在给他打掩护呢。
可是屋里走出来的是连里的一个弟兄,正在扣好枪上的保险。我问:“屋里有日本兵吗?”他说:“没有,只有一个土人老太婆。我猜她是吃不了这个苦,想到老祖宗那儿去了。我成全了她。”
我火冒三丈:“你这个婊子养的!人家派我们到这儿可不是来杀老太婆的!”他找了一大堆理由替自己辩解。这时候,一个中士走了过来,我们向他报告了这件事。我们离开了,不知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其实,那小伙子也是好人,就跟街坊上一般小伙子一样,他也不是个头脑发热好冲动的人。他也想做一个好样儿的。可是为什么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会和另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大不相同呢?我就是弄不明白。
大家的心肠都变硬了。人类,地球上生命发展的最高形式,在那里像野兽一样互相厮杀。我们经常处在炮火之下,必须走两里地的泥路去送伤员。死的可就没法运走了,到处是日本兵的尸体。我们用稀泥把他们盖住,可是炮弹过来又把泥巴炸飞了,死尸也炸散了。蛆虫在稀泥里乱爬,就像在腐烂的东西或者粪堆里一样。
人都有自己特别受不了的事儿。在我,最可怕的莫过于炮火。那简直让你毫无办法。鬼东西就像货车呼啸而来,夹着可怕的爆炸,地动山摇,血肉横飞。
我还记得在半月山的那个下午。当时我旁边掩体里有两个小伙子。再过去的一个里有三个。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突然,炮声响了,像打枪一样向我们开炮。炮弹在离我头顶一英尺的空中掠过。跟我隔两个掩体的地方,有一个小伙子正坐在钢盔上,喝C种配给里的那份巧克力热饮。炮弹在他的掩体里爆炸。我亲眼看见这个小伙子比尔·莱顿炸到半空中。另外两个小伙子都被炸得仰面朝天,当然是死了。我旁边那个掩体里的两个人也当场牺牲。
莱顿是唯一的幸存者,你信吗?他只是局部有些伤残,弹片炸的。他的病历上一点儿也没有提脑震荡,但是以后他的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作。他是被炸到半空中的呀!如果你不把这叫做脑震荡,那……卫生兵忙着救命,哪儿顾得上给人填写病历啊!
还有一个小伙子炸掉了一条腿。他原先是个伐木工人,大约21岁。他经常对我说,用云杉做的圣诞树散发出来的气味好闻极了,又说:“‘大锤’,你看我的腿能丢了吗?”唉,想起来就让人伤心……担架上放着他的一只行军鞋,那截脚脖子露在外面,就像砍断的树桩。抬担架的人相互看了一眼,用他的雨披把他盖了起来。他死了。
雨没完没了地下,泥水没过我们的两膝。我心里想,他妈的,我们呆在这个臭气熏天、泥泞不堪的山脊上到底为啥?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我是说,我们在泥泞的山坡上浪费我们的生命!
人们说,硫磺岛(西太平洋上的一个火山岛,二次大战中是日木的一个空军基地,1945年2月至3月,美军以极大代价攻克。)之战是历史上两栖作战最为辉煌的战例。但是从硫磺岛回来的退伍军人对我说,那次战斗比他们读到过的任何一次战斗都更与帛琉之战相似。这他妈的有什么辉煌可言呢?
(“大锤”①斯莱吉 注:叙述者在部队里的绰号,在英文中,大锤的读音有一部分与叙述者的姓“斯莱吉”是谐音,拼法也相同。)
在菲律宾和日本的遭遇
此君人到中年,依然精干,却不无发福,一眼看去,很像身经百战的轻量级拳坛老将,或是棒球手。
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兰吐尔镇靠近查纽特空军基地的地方,经营一座温室和一间花店。“我只跟花儿打交道,花儿是不顶嘴的。”
“二次大战以前,我是个积极进取的人。如今,我住在镇上唯一的山岗上,很少出门。我天亮起床,照管花木,晚上回家睡觉。到晚上喝一通白干、啤酒,跟别人不来往。”
“我很想再回菲律宾看看。那儿有许多事情叫我牵肠挂肚。那儿有我们弟兄们的墓地,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墓地。”
我在战争中失掉了好多好多朋友。刚打起来的时候,我们中队有185个人,三年半之后,我们被救出日本战俘营,这时候就只剩39个了。我心里最搁不下的就是他们。我跟他们一道打球,一道干活,一道生活过;我想他们。
1940年,我到了菲律宾,服役期是两年。我1939年入伍,当时19周岁。那时找工作是很困难的。我原来一直对制造业感兴趣,尤其是飞机,很想在这方面深造一下,但硬是没钱上学。我看到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参加空军,学门手艺”。我就报了名,来到查纽特空军基地,进了金属薄板技校。毕业后,他们把我派到菲律宾群岛,径直来到克拉克空军基地,地点在马尼拉正北,离城60里。
他给我看过一幅克拉克机场的照片,是1939年拍的:茫茫平原,空无一物。
当时基地大约有250人,只有一个轰炸机中队,这就是第28航空队。我的工作是修理破旧的B-10轰炸机。那时候办点事真叫慢。直到1941年夏天,他们才开始往这儿调部队来。
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日本会进攻美利坚合众国。这根本不可能嘛!所以我们没有放在心上。1941年11月起,我们进入了戒备状态。我是老阿莫斯上士的副机枪手。这是一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式路易斯机关枪,靠空气冷却的家伙。
12月8日——当地时间是12月7日——上午9点左右,空袭警报拉响了,所有的战斗机和B-17轰炸机全部出动。我们想,嗨,麦克阿瑟将军看望我们来了,我们要露一手给他瞧瞧。不一会儿。飞机全部返回了基地,时间大约是11点30分。我吃完午饭,来到机场娱乐室,拿起一本体育杂志翻着看。这时电台正在播音。忽然,马尼拉的新闻广播中断了音乐节目,说:“克拉克机场遭到轰炸,”又大声喊叫,“日本人攻击克拉克机场啦!”
我站起来,朝窗外望,连轰炸机的影子也没有,一切平静极了。我坐了下来,问旁边的一位弟兄:“你听见了吗?”他说:“噢,上帝,胡扯淡!”这时,说什么的都有。我想,何不把这些谣言的内容和日期记下来,过一两个月好拿来当笑话讲。于是我回到自己的铺位,翻出一本小黑皮日记,记下了珍珠港清晨挨炸的谣传。我们才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可是现在,我们又听说克拉克机场也吃了炸弹!我好好儿的坐在这里,头顶上啥也没掉下来嘛。(笑)
正在这个时候,上士跑进来,大叫:“是真的!来了!”我顺手抄起我的一枝一次大战时期造的春田式步枪,把钢盔朝头上一盖,还有防毒面具,跑出兵营。
我刚到我们那个小小的机枪掩体,炸弹就下来了。我站起身来,说:“噢,炸弹的声音原来是这样的。”阿莫斯一把就抓住我的后裤腰,把我拖了回来。我在新闻纪录片上看到的轰炸场面可多了,波兰,欧洲,啥都见过。但是真家伙下来,倒是有些不大一样呢。
整个机场都炸平了,轰隆轰隆一顿乱炸,什么目标都没有放过。我们所有的飞机这时刚刚返航不久,正停在外边加油呢。
那天早晨,我们飞机起飞的时候,日本人确实是来了,袭击了吕宋岛北部的碧瑶,然后飞回台湾。我们找不着它们,这才返航加油的。他们没有看见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他们正在两万英尺的高空呢。所以,飞行员们都去吃午饭了。而正在这时,日本飞机却又飞到了克拉克机场上空,把我们炸平了就跑。阿莫斯跟我从堑壕里爬了出来,都懵了。
我们四下里一瞧,只见飞机在烧,机库在烧,油车在烧,人在嚎叫,一片死伤。日本战斗机紧跟在后边进来了,大约有80架,见到什么就扫射什么。阿莫斯便竖起我们的那挺小机关枪朝他们开火。(笑)我站在旁边,手里捧着弹夹,轰炸过后,我们两个还站在那儿直发愣。
这一切都是不该发生的。我们是美国人,他们是日本人,谁想到他们竟会把炸弹扔到我们头上来呢。过去我们都是这么说的。(笑)我们老是听说,日本人全都戴风镜,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投弹瞄准器。他们没有什么像样的海军,用的尽是我们扔掉的废铜烂铁,还烧我们的石油。大家一直是这样想的。天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日本飞机轰炸以后的一个月,我们没有什么活儿可干,只帮着修理飞机,从三四架炸坏的飞机里拼凑出一架来用。后来,他们把人员调到外边去了,我们什么也没剩下,明白吗?我们死了好多啊。
我们把轰炸机开到了明大诺岛的德尔蒙特菠萝园。好家伙,往南飞了七八百里。菲律宾再也找不到别的机场来停放B-17型轰炸机了。我们的35架B-17只剩下16架左右。至于说到P-40呢,只剩下一半了。手无寸铁,怎么跟日本人干呢?我们尽力巧用手里的飞机,无奈,日本零式飞机的性能比P-40要强。
我们在那儿一直呆到1941年圣诞节前夕。我们在想,我们快要调部队来了,要用飞机运给养、材料来了。我们听说,有五十四架A-24俯冲式轰炸机正在朝这儿飞来。我们手头连一架俯冲式轰炸机都没有。还听说要运来大炮。这是作战计划,明白吗?还有军舰呢。真是应有尽有。海军还要护送一支船队开到菲律宾。然而,我们的海军如今却躺在珍珠港的泥底上睡大觉了。我们不知道珍珠港受到了多大程度的破坏。
圣诞节前夕,我们接到命令:退守巴丹半岛。巴丹离这里大约100里。上士说:“我要五名志愿兵。你,你,你——,”他用手点到的五个人就都成了自愿的了。(笑)“你们留守克拉克机场,其余的人统统转移。”
12月22日,日本保间将军的部队在吕宋岛北部的仁牙因湾登陆,另一支在拉蒙湾登陆,对马尼拉形成了一股钳形攻势。麦克阿瑟手下有7万左右的菲律宾部队,但装备不足。温赖特将军驻守仁牙因湾,但他只有小小一团美国步兵和一些菲律宾士兵。他一架飞机都没有,更没有俯冲轰炸机。日本军队登陆没有遇到抵抗。
我们五个人仍一直守在克拉克空军基地。我们那位新任命的头儿是少尉,刚入伍的大学生,是个瘦猴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留下来。第二天早晨是圣诞节,约翰逊少校开着一辆军车停在门口,吩咐说:“少尉,你就是基地的头儿,这五名列兵就是你的人马。你有一辆装着汽油的卡车,一辆装着柴油的卡车。”汽油车上满满地载着三千加仑高辛烷汽油,“有P-40——在这儿强迫着陆,你就给它加油。什么时候撤离克拉克机场合适,完全由你决定。”少校说完,就出发去巴丹了。
我们在那儿呆了四天,可以听到塔莱克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战场就在我们正北21里的地方。我们在机场上打了地铺过夜,时刻准备P-40降落。我们看得见炮弹发射的火光,听得到隆隆的炮声。我轻轻地推了推少尉,说:“你不觉得咱们该走了吗?”(笑)枪炮声越来越近了,而我们这儿却堆着三千加仑的汽油呢。这家伙本身就是一颗巨型炸弹。只要打进一颗曳光弹就统统报销了。非把这家伙弄到巴丹去不可。
他说:“明天一早出发!”我们吃了最后一顿早餐,肉蛋一扫而光。以后三年半,我们就再也不曾尝过咸肉煎鸡蛋的味道了。
少尉说:“别莱克,你把机枪架在汽油车上。”另外两名弟兄跳上了柴油车。他自己坐一辆指挥车,跟在后面。车与车之间隔着一二里地。万一来了日本飞机,就不会全完。(笑)这几车货色一着火准得炸个天翻地覆——轰!
我们的车头和拖车很不配套,要拉着这玩意儿穿过各式各样的车马人流,开上百里多地,谈何容易。只要轻轻一踩刹车,拖斗准会往前冲,把车头顶横过来,三千加仑汽油可不算轻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算交待了。路上也碰到了一些险情,但我们总算挨到了巴丹。
上士通知我,调我到第28军需运输机队,跟那儿的一些办事人员、卡车司机、机械师、技工一样,各发一枝春田式步枪,送到前线当步兵。可是有些人从出娘胎起就没有开过一枪。我们的机关枪都是美造的,是打坏了的P-40飞机上拆下来的。我们的任务是把剩下的最后四架P-40维修好。
美国军队仍然守在马尼拉湾的柯里吉多岛。他们有重炮,可以阻止船舰闯进海湾。1942年3月,日本人攻不破我们的防线,就调来了满船满船的军队。我们直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我们有老大老大的火炮,而菲律宾侦察兵也是好样的。小日本被我们揍得三个月不能前进一步。
在最后一个月里,就是说,从3月3日到4月9日,我们打得只剩下一架P-40了。我们就把它修了又修,补了又补。这架唯一的驱逐机看起来就好像得了麻疹似内满身都是斑点。我们继续等待运输船队到来。麦克阿瑟老是跟我们说,船队已经出发。美国总统罗斯福亲口告诉菲律宾总统奎松,美国要全力支援。可是,他们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很清楚,啥也办不到。我们眼巴巴一直盼望船队早日到来,但是连个影子也没有见到。
有一位弟兄拿着一封写给美国总统的信走了进来。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总统:请给我们再派一架P-40飞机来吧。我们眼前的这一架满身都是透明窟隆。”(笑)就这样,我们开心地大笑起来。
日本人终于攻破了我们的防线。我们开始朝巴丹半岛北头撤退了。上面有令,必须把一切物资统统烧光、毁掉。我们把所有的工具都扔摔了。器材在燃烧,到处都乱成了一团。(他好久一言不发,轻声地抽泣。)真他妈的!你眼睁睁地看着弟兄们从前线退下来,一个个蓬头垢面,全身是伤,居然还在找自己的工具袋呢。——(声音很轻地)活见鬼!到处都是大堆大堆的军火在爆炸。好像进了地狱。
我们撤退的时候,巴丹半岛发生了一次地震。当时我们正在行军。霎时间地动山摇,我们全都慌了神。这是世界末日吗?这就是对上帝耶和华的赞美诗吗?我们别是在做梦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放下一切武器,等日本人来。金将军已经放弃了巴丹半岛,日本人开了进来。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列队搜身,谁戴着戒指、手表、金边眼镜,都统统拿走,把眼镜扔在地上,用脚踩烂,把金框子装进自己口袋。如果你有戒指,还是主动交出为妙。要是你舍不得摘下来,那家伙就会把刺刀顶着你的脖子。幸好我从来不戴戒指,买不起啊!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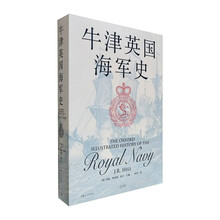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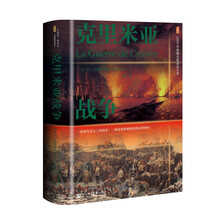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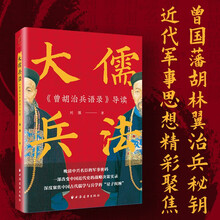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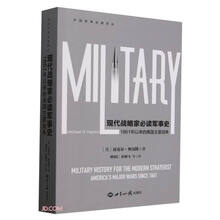



——华盛顿邮报
★“这确实是一本伟大的书,它撼动了人们的心灵,并为这段影响历史的过程留下了忠实记录。”
——《西部电讯》
★“迄今为止关于二战的最重要的书之一。”
——《Look》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