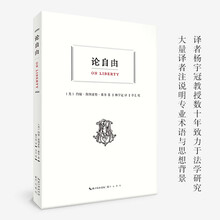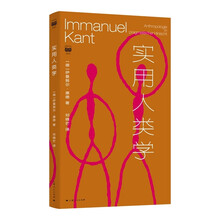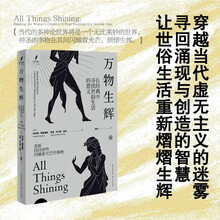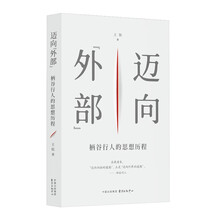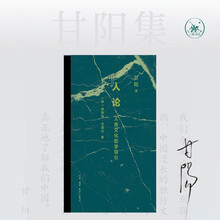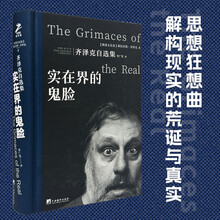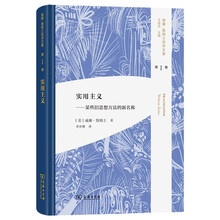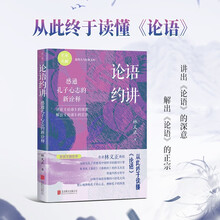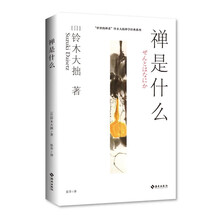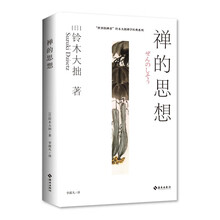(一)以“仁”释礼——儒学核心思想在礼学中的呈现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提炼出一个包括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乃至宇宙伦理的成熟而完备的伦理道德体系,而“仁”即是中华道德体系之核心。“仁”既指“仁者,爱人”这一德目,还是中华美德之总和;如果将中华道德体系比喻为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仁”即是树之根系与主干,而“孝”、“悌”、“忠”、“义”、“信”、“恭”、“敬”、“慎”、“忍”、“谦”、“勤”、“俭”、“让”等德目则是“仁德”之树的枝叶和花朵。
“仁”既是儒家伦理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核心,也是儒家构建礼学体系之理论基石。儒家将“仁”作为最高道德准则,而“礼”则是引领人实现“仁德”境界之路径;儒家将“仁”作为“礼”之精神,赋予“礼”全新的含义。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在贵族中已蜕变为庸俗、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与内在的道德情感相脱离。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记》以“仁”释礼,在对礼的阐释中倾注了丰富的道德情感;在“仁者,爱人”之人性光辉照耀下,对原本显得刻板凝滞的礼仪条文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解读;将以“仁”为核心的美善之德看作是礼之精神,而礼则是人内心“仁德”的外在文饰。
儒家认为,礼应该与人内心的道德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和水乳交融。《礼器》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并用贴切的比喻来说明“忠信”之德对于礼是多么重要:“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忠信”之德是礼的灵魂和礼的生命之所在。
儒家以“仁”释礼,将“不下庶人”的“礼”扩展到社会各阶层;认为“礼”不应仅为贵族所有,而应该下及庶人,成为普及于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曲礼上》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人的价值不是由地位高下和财富多寡决定的,一个人即使身为“贫贱”、为“负贩者”,但他“知而好礼”,就可以“志不慑”,从而拥有人性之尊严。
儒家论葬礼,针对当时用活人殉葬的丑恶习俗和用俑人殉葬之风气,站立于“仁者,爱人”之立场对丧葬礼俗进行了严厉的拷问。《檀弓下》记载:“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陈子亢是孔门弟子,儒家仁学思想的文化洗礼使他能够在丧礼中力排众议,以“非礼也”否定用活人殉葬之陋习。
人的生命在儒家的文化诉求中获得了极高的价值,儒家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甚至反对用俑人殉葬。《檀弓下》记孔子曰:“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孟子·梁惠王上》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用俑人殉葬与“人殉”相比,是丧葬礼俗的发展和历史的文明进步,但儒家以“仁”观照之,用中国语境中最激烈的措辞诅咒“始作俑者”,认为这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
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孔子对当时的礼,独有许多精邃细密的研究”,他能够发明出礼之“内心”,探寻出礼之“真意”①。孔子及其后学释礼,从中发明出的礼之“内心”与“真意”之一,即是礼所蕴涵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精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