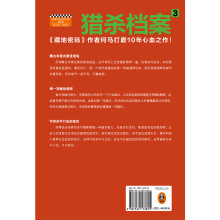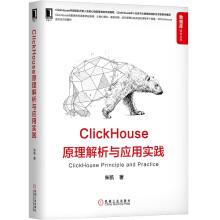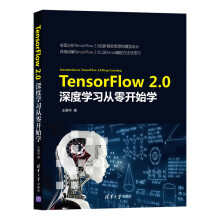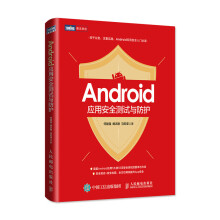丝绸与皮肤:两仪之间的身体
作为天子,皇帝需要主持每年冬至的祭天仪式——这时的北京寒冷而萧索。祭天场所设在京城南郊,那里有一座巨型的三层汉白玉石坛。祭天所在的“郊”,在英语译作“suburban”(郊区),但是它的实际含义为“boundary”(边界)。因此,祭祀地点被安排在城市与乡村的交界,正如祭祀活动调和“在上的天”和“在下的地”。
每年的大多数时候,圜丘素颜以待,毫无陈设。只有在仪式期间,人们才铺上地毯,点起火把,布置好帐篷、香案和供牲用的器皿。但是与宏伟永恒的祭坛和周遭的空旷相比,这些器物显得如此渺小。祭坛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身着龙袍的皇帝和头戴貂皮镶宝官帽的百官。
为了从绘画过渡到礼仪表演,我想首先讨论另一种丝制的平面,即印有花纹的服饰平面。然后,我将探讨典礼中盛装以待的身体为何可以比作祭祀用的“器”。
满族服饰的设计充分考虑了马背民族的灵活性,它由几个组件构成:上衣是齐裤的短款袍褂、下裳是前后开襟的下摆。礼仪用的朝服(图11)遵循这一形制。每逢科举考试,进士们会由皇帝亲自授予朝服(宫崎市定,1981:87)。朝服由丝绸制成,印有或绣有各种纹饰。朝服纹饰与更为常见的旗服和龙袍相似,它们不易损坏的特点有利于我们研究清代服饰的象征主义。
袍服表面绣满了宇宙符号,比如大地、海洋和天空。衣服的下摆是水脚,绣有波涛翻滚的水纹。袍服的四条轴线(即东、南、西、北四个主要方向)是高耸的山峰,它们的上方是云空纹,内藏升起的龙纹和其他象征帝王和宇宙的符号(坎曼,1952:81)。在穿戴袍服时,穿戴者的头部从镶有祥云的衣领探出,这个动作从动态的微观层面呈现了18世纪中国人眼里的宇宙。毫无意外,帝国官员全都身着此种袍服。
在上述基本型制之外,皇帝的龙袍绣有古代的“十二章纹”(恽敬,1883),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象征裁断的权力)、黻(惩罚的力量)、宗彝、藻、火、粉米(坎曼,1952:87—88)。在清朝,只有在1759年乾隆皇帝颁布《皇朝礼器图式》后,十二章纹才得到使用。它们与祭礼关系密切。在18世纪,人们认为这些符号不但能够指代人世之上的宇宙(四种主要祭祀、生动的自然、五行),而且可以指代君主的品质(包括临照、镇、变、孝、洁等)(坎曼,1952:90—91)。这一对外在宇宙和内在人格的双重指涉,显示出承载这些纹饰的皇帝是礼仪表演的核心。
l759年的《皇朝礼器图式》规定,上朝时的服饰需要另有一层区分皇帝和百官的装饰。官员们需要用一种黑色短褂罩住袍服,在胸前、背后和肩部缝上体现官员品级的长方形补子,按照文禽武兽的方式标定九个品级。只有皇帝能够露出袍服上的符号。这样,乾隆皇帝肯定了君主在宇宙层面表述意义和恢复这种力量的能力。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