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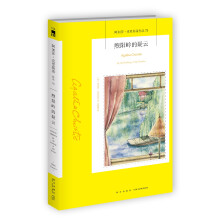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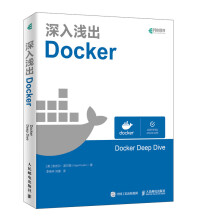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多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
周作人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弟子,而周作人与其弟子的文学思想、创作和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成就:周作人的人生道路,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现象。《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丛书:周作人与周门弟子》逐章论述了周作人与弟子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江绍原和任访秋等人在文学思想,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影响关系,并且同时也论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趣味和选择的影响关系;最后几章直接轮速周作人在“五四”之后,“七七”事变之后和1939年这几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思想、创作和人生抉择,是对前文涉及的问题的集中讨论。
第一章
俞平伯乳名“僧宝”,幼年时家人曾送他入寺挂名为僧;1932年,其《戒坛琐记》云:“四五岁就入寺挂名为僧,对于菩萨天王有一种亲切而兼怖畏之感,甚至于眠里梦里都被这些偶像所缠扰,至今未已。这个童年的印像,留下一种对于寺庙的期待。”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云,关于他的出生,家人有一个传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1934年,其《五秩自寿诗》因之而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之说。
虽然不尽相同,但难得两人都有这样的“僧缘”,这是否也是他们师生情谊之外的某种“缘分”?虽然肇因远在他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与他们本人无关,但人到中年却都又借题发挥,抒发其人生感慨,不约而同地将“迷信”表述为一种关于自我人生叙事的信念。
——周作人与俞平伯的关系,似乎比其他弟子多了一点“传奇”色彩?
一
关于周作人和俞平伯的最初的交往,钱理群《周作人论》中《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一章,有清楚、准确的叙述;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收到俞平伯的信,而在此之前,1919年12月17日出席“新潮”社的会议时,他们见过一面;他们真正的“相识”,是在1922年初讨论新诗问题的时候。
1922年1月,俞平伯在《诗》创刊号发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认为“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并且“平民性是诗底主要质素,贵族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应该说这个观点并无新见:“效用”说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就是托尔斯泰——这是文章中承认了的;“平民性”的说法,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著名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7],周作人有著名的《平民文学》,也是胡适“五四”时期文学观和进化论文学史观的一贯论点,后来甚至提出这样一个文学史的“公式”:“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俞平伯的这篇文章的思想明显反映了“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
周作人在同年2月26日发表了《诗的效用》一文,从三个方面对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了疑问。周作人认为:
真的艺术家本了他的本性与外缘的总合,诚实的表现他的情思,自然的成为有价值的文艺,便是他的效用。功利的批评也有一面的理由,但是过于重视艺术的社会的意义,忽略原来的文艺的性质,他虽声言叫文学家做指导社会的先驱者,实际上容易驱使他们去做侍奉民众的乐人,这是较量文学在人生上的效用的人所最应注意的地方了。
周作人敏锐地注意到俞平伯论点中所包含的文学“功利的批评”之思想的危险性,这是他的深刻之处,并且恐怕也是他这样郑重其事地撰文批评一篇出自自己学生之手的文章的原因之所在吧。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这是较量文学在人生上的效用的人所最应注意的地方了”,隐含了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文学观的深刻反省———他同年1月22日发表的《自己的园地》一文中说:
“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
很显然,在周作人看来,将诗乃至文学定义为“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就是“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的“功利的批评”。
至于俞平伯所谓的“平民性是诗底主要质素,贵族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周作人在此之前发表的《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已经论述过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也就没有质疑俞平伯的这个论点,但他的《诗的效用》最后说:
文学家虽希望民众能了解自己的艺术,却不必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因为据我的意见,文艺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现,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现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
这里还是就俞平伯所谓的“诗的效用”而言的,但也可以看作是对俞平伯“平民性”说法的一个侧击。
钱理群《周作人论》中《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一章在概述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和周作人《诗的效用》不同论点之后指出:“正如后来废名所说,这时候俞平伯正是‘年青的时候有大欢喜,逞异想’,受着启蒙主义思潮的薰染,作着‘时代’的‘梦’;而周作人此时已步入中年,对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发生或一程度的怀疑了。”这个判断是十分准确而深刻的。
下文,且就这一问题,依据学术界新出的学术成果和史料,作进一步的梳理。
俞平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思想确实曾经是比较激进的。他的“平民性”文学思想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的表述,并不是偶然的。这里有几条材料值得注意:
1919年3月,邓中夏等人发起并领导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该组织“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俞平伯加入了这个讲演团,为第四讲演所之讲演员,积极参加活动;同年11月,作了题为“打破空想”的讲演。由此可见俞平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思想之深。直到1922年7月,俞平伯在赴美途中,目睹“作工者状如鬼魅,筋力疲惫,仍复力作;而船上员司及旅客,则凭阑闲眺,既恶其扰,又嫌其迟缓”的情景,不禁感慨万端:“始信现代文明,一言以蔽之,罪恶而已,掠夺而已。吾辈身列头等舱,尚复嗟怨行役之苦,可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亦可谓毫无心肝。苟稍有人心者,睹近代罪恶底源泉在于掠夺,则应当以全心力去从事社会运动,即懦弱的人,至少亦须去从事民间运动。高谭学术,安富尊荣,此等学者(?)人间何贵?换言之,不从制度上着手,不把根本上的罪孽铲除了,一切光明皆等于昙花一现。”正是这种激烈的社会革命的思想,使得邓中夏这样的俞平伯北京大学同学最后走上政治革命之路,俞平伯有此思想,所以有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那样的“民间运动”,只不过最终没有迈上“以全心力去从事社会运动”的政治革命之路而已。
……
绪言 京派中的京派
——一个文学史的命题,一种阐释周作人的方式
第一章 “出家”还是“在家”?
——周作人与俞平伯的人生选择
第二章 晚明小品:周作人和俞平伯的“低徊趣味”
第三章 《窗》:“人生之艺术化”与“梦的真实与美”
——废名与周作人的人生与艺术的深刻思想共鸣
第四章 阐释周作人:“南朝人物晚唐诗”
——周作人和废名对“六朝文章”“晚唐诗”的特殊情怀
第五章 “梦想的幻境”和“文章之美”
——周作人对废名小说的阐释
第六章 “怀废名”与叹知堂
——周作人与废名1937年之后的师生情谊之分析
第七章 谢本师:“你也须要安静”
——沈启无与周作人文学关系的历史考察
第八章 书信中的故事
——周作人与江绍原往来书札笺疏
第九章 一种别有意味的对话关系
——任访秋古典文学研究与周作人影响之关系
第十章 哪里来? 何处去?
——周作人的“五四”文学观及其与俞平伯、废名之关系
第十一章 “言志”的苦心与文心
——周作人1937年至1939年北平“苦住”期间创作之
分析
第十二章 话里话外:1939年的周作人言论解读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