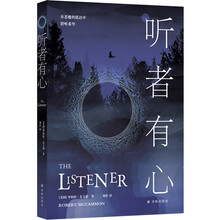现在我可以结束了。
我沿着墓地而行。那是在夜里。也许是午夜。小巷是上坡路,我行走艰难。小风刮过微微放晴的天空,把云都吹散了。有一块永久出让的墓地真好。这真是件美好的事情。如果有的只是这一永久的话。我来到了栅栏门前。它锁着,,非常正确。但我不能打开它。钥匙进到锁洞里,但是转不动。时间长了失效了?换了新锁?我朝它撞去。我一直退到小巷的另一侧,然后冲上去。我回到了家,正如尤迪指示我的那样。我最终爬了起来。是什么这么香?丁香吗?也许是报春花。我朝我的蜂箱走去。
它们都在那里,像我害怕的那样。我揭开其中一个的盖子,把它放在地上。它是个小屋顶,脊部高耸,两侧是陡然下降伸展而出的斜面。
我把手伸进蜂箱,穿过空荡荡的板层,摸到底部。在一个角落里,我的手碰到一个干燥多孔的圆球。它在触及之下立刻化为细屑了。它们集成一团团一串串,为了能热一点儿,为了能试着睡觉。我抓出一把。天太黑看不见,我把它揣进兜里。它没有一丝重量。整个一冬人们都让它们呆在外面,人们取走了它们的蜂蜜,却没给它们喂糖。是的,现在我可以结束了。
我不去我的鸡棚。我的那些母鸡也死了,我知道。只是它们,人们是用另一种方式处死的,也许除了那只灰的。我的蜜蜂,母鸡,我抛弃了它们。我朝房子走去。它在黑暗之中。门锁着。我撞开它。也许我可以用我那些钥匙中的一把打开它。我转动着开关。灯不亮。我进到厨房里去,进到玛尔特的房间里去。一个人也没有。房子被弃。电气公司切断了电源。他们后来想重新给我送电。只是我不要。我正是变成这样了。我重新回到花园里。第二天我看了那把蜜蜂。一团翅膀与圆环的灰尘。在楼梯下面,在信箱里,我发现了一些信件。一封是萨沃利的。我儿子很好。当然了。别提这一位了。他回来了。他在睡觉。一封是尤迪的,用的是第三人称,要一份报告。又是夏天了。我走了有一年了。我要走了。有一天我接待了加贝尔的来访。他要那份报告。瞧吧,我以为已经了结了,这些会面,言谈。下次再来,我说。有一天我接待了昂普瓦兹神甫的拜会。这是可能的吗!他望着我说。我相信他真的爱我,以他的方式。我告诉他不要再信任我了。
他开始高谈阔论。他有道理。谁又没有道理呢?我离开他。我要走了。也许我会遇到莫洛伊。我的膝盖不见好。我现在有了一副拐。这样将会快些。光阴甚好。我可以学。所有可以卖的东西我都卖掉了。但我曾负债累累。我不再能忍受做一个人,我不会再尝试了。我不会再点亮这盏灯。我要吹灭它走到花园里去。我想到五月、六月里那些漫长的白日,我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有一天我跟哈娜说话。她带给了我祖鲁、艾尔丝娜姐妹的消息。她知道我足谁,她不怕我。她从来也不出门,她不喜欢出门。她从她的窗口跟我说话。那些消息不好,但不完全是这样。里面也有好的。那足些美好的白天。冬天曾经出奇地严峻,所有的人都这么说。那么我们有权利拥有如此美妙的夏天。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权利。我的小鸟,人们没有杀死它们。那是些野鸟。但是挺亲人的。我认出了它们,它们也像是认出了我。但准知道呢。有的鸟不见了,也有的鸟是新的。我试图更好地了解它们的语言。毫不借助于我的语言。那是一年中最长、最美的白昼。我生活在花园里。我提到过一个告诉我这个那个的声音。就是在这一时期里,我开始使自己与之相协调,开始理解它所要的。它用的不是人们教给小莫朗,轮到他时他又教给他的孩子的言词。所以开始时我不知道它要什么。但我终究明白了这一语言。我懂了,我了解,也许是以相反的方式。问题不在这儿。是它告诉我做出报告的。那么说我现在更自由了吗?我不知道。我会学到。于是我回到房子里,我写,是午夜。雨水抽打着玻璃。那不是午夜。天没有下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