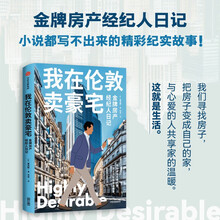毕飞宇:不洁的上帝<br><br>第一次见毕飞宇是两年前的四月,那时候他刚来过香港参加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颁奖礼,同时入围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他没想过自己会拿奖,提早买了次日回程的机票,结果旧作《玉米》获得年度文学奖,他很是意外。而后来香港参加中文大学的作家邀请活动。眼前的毕飞宇依旧是平头,留着青葱的发际线,面目轮廓分明,像极了萤幕中的正派小生。他找了可以抽烟的露台,又挑了一个可以吹散烟尘的风向位置坐下,点燃一支烟,到访问结束,烟缸里齐齐整整插了五只烟蒂。他的风格是清谈式的,就着一杯茶,天上地下好像能说到天荒地老。说到底,天生是说故事的人。<br>毕飞宇不用手机,他的理由是“实在用不着”。每天安坐家中写作,电话就在手边,打家里电话基本都能找到他。找他访问,得先找在中大的黄念欣老师。七月来书展演讲,跑前跑后不方便,主办方只好专门给他配了手机。两年过去了,他微博粉丝已经8万,墙里墙外又拿了几个奖,还在大学教起了书,手机还是没有。<br><br>没有故乡的人<br>毕飞宇在苏北兴化的乡下长大,兴化是水乡,也是施耐庵及郑板桥的故里。他小时候住过一条竹巷,铺着长长的青石板路,他常看着那些手工业者在巷里劈竹子,劈里啪啦砍下去,很是欢腾。长大后才知道,擅于描竹的郑板桥,旧居就在他家附近,文化的传承远非想像中神秘,只是耳濡目染的渗透。毕飞宇的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下乡,同母亲一起做了乡村教师。父亲是一个无根的人,从前姓陆,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那个姓陆的爷爷也不是生父,毕家只有两代人。<br>年少的毕飞宇经常看着同学去给祖先磕头、上香,而他面对着茫茫土地,却没有一块可以跪拜。他的小说大多以苏北乡村作背景,却说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他也问过父亲自己的家族史,问不出结果,这种缺憾感和对生命源头的追溯欲望却成为了最初写作的动力。他写哺乳,写血淋淋的生育场景,全然出自对血亲关系的寻觅,直到拿鲁迅文学奖的小说《玉米》,女主角玉秀未婚先孕,他第一稿安排的结局是惨烈的死亡:孩子死了,文革期间怀孕无疑身败名裂,玉秀破罐子破摔,淹死在放满菜籽的粮库里,尸体第二年春天才发现。然而死亡只是悲剧的结束,却非开始。他想起了父亲,埋头写第二稿:玉秀所生的孩子不见了,无影无踪。在小说里,玉秀就是他的奶奶,那个消失的婴儿就是他的父亲,这样的结局更加伤痛,仿佛寻着了生命的脉络,他满足了。<br>有五六年的时间,毕飞宇与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紧张到不说一句话。父亲很寡言,他的黄金岁月葬送于政治,深谙人生凶险,对“因言获罪”的恐惧驱使他极力反对儿子的写作。何况那个年代,讲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他升大学以及大学之后,父亲一直不能答应他写作这条路。长大后他觉得,父亲像康德笔下的浮士德。“这是个标准的出作家的家庭,因为神秘、波折,有冲突、有戏剧性,当然也有压抑。站定,仿佛一场仪式,也仿佛一个暗示。这幅画面令他莫名兴奋,此后将其写进了一篇短篇小说——《写字》。后来他去扬州的大学读中文系,寒暑假回家,父亲很沉默地站在门口,看到他,身子往后退一步,让他进门。他知道父亲在等他。<br>与“石头一样”的父亲相反,母亲却是一个“生动”的人,长得漂亮,嗓子也好,很有表现欲望,人也活络,父母截然相反的性格在毕飞宇身上时隐时现,这种微妙的碰撞也在他的笔下跳动,他自认自己的小说偏压抑,但到过分沉重时会夹杂一些俏皮,添一丝华美,快飘起来的时候又会把调子往下压,“所以我的小说不会让人笑出来,就在心里笑一笑。”<br>父子二人开始和解是在毕飞宇结婚以后,真正如好友般相待却是自己儿子的出生,新生命的降临重新串起了三代人的血脉,“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爱儿子的方式与父亲对我差不多,表达得不多,做得很多,对儿子的爱甚至超过对父母的爱。”出版《毕飞宇文集》的时候他特地为父亲写序,告诉他生命是漫长的河流,爱是一代代传递,却非相互的过程。<br>剥洋葱<br>毕飞宇说自己是个成熟很晚的人,刚结婚那几年在南京教书,每天惦记的就是下午要踢的那场球,傍晚进家门,太太就知道今天的球是输了还是赢了,若是赢了,临睡前还要回味一番,“那个时候苏童已经成名了。”<br>从写《青衣》开始,2年以后毕飞宇的小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开始写实,《玉米》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时,距离这部小说的创作已有十年,四十多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时期,这一点上毕飞宇绝对算不得“晚熟”。“玉米”成熟时,在毕飞宇心头也是自己的小说道路成熟之时。早年的毕飞宇写了很多诗歌,对语言的锤炼下了一番功夫,阅读体系也完善,初出文坛即给人起点较高的印象,“这些只是技术的熟练,与个人的脾性气质无关”,《青衣》之后的《玉米》与《平原》终于有了他“自己的嗓音”,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有批评家说:“《玉米》的发表,让整个中国文坛松了一口气,我们的小说终于瓜熟蒂落了。”长久以来中国作家都是吃洋面包长大,毕飞宇也吃,然而吃的过程也是把某些异质从自己的血液中一点点挤掉的过程,再拿起笔,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气力。《玉米》呈现的是2世纪7年代的场景,但彼时2岁的毕飞宇断然写不出这样的作品,这不是顿悟,而是一场漫长的修炼,他要感谢时间。<br>他常反复说自己的小说只写了一个主题:“疼痛”,他描绘个体的疼痛,出自于对人性之美的迷恋,无论怎样的痛楚,都夹杂着美好、尊严与希望。“玛丽皇后被押上了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这个时候人性的美到了极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人性的尊严更美。”所以他的小说甚少描绘风景以及外部环境,“那都是大家能看到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目之所及绝非真实,撇开海啸与风暴,他更专注于人物眼中的惶恐与心中的涌动,“我想写的是人力不可猜的那种可能性”,在他眼里,最大的悲剧是在人性的参与下经过自我选择走向悲剧,那才是切肤的实感。<br>这种过程写作者本身也是痛苦的,我们说起君特•格拉斯“剥洋葱”的比喻:“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他笑了,他说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像是自己说的,只是没来得及说而已。“小说家有时候真的是上帝”,他顿了一会,又说:“是不洁的上帝”。上帝可以肆意安排人的命运,掌控调配一切的权力,“没有一个人是该死的,也没有一个人是该受罪的”,他在写《玉秀》的时候才意识到这种不洁,他是如此爱这个姑娘,想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给她,她不该被奸污,不该背负命运沉重的枷锁,何以至此,都是自己一字一句把她推到那个境地的。这样的写作过程很是折磨,“对小说家来说,把所有的不幸放在你最爱的人身上,这就是悲剧。”<br>这种对内的探射,最后的着力点却是外部,拨开浓雾,他想照亮的仍是时代,这是他刻意为之的笔法。成长于上世纪7年代的人无可避免还带着较重的意识形态情结,极权之手抹杀了一切个性与感觉,造成人的异化。“当一种力量超出人的忍受范围,人都会被异化。爱会让人异化,宗教也会,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人缘何疼痛,缘何被束缚,又缘何残忍,都出自外部世界的规训,他渴望将极权政治的残酷野蛮呈现给年青一代。问起他的“野心”,他摇摇头,文学永远无法改变世界,只能给人静悄悄地抚慰,他的心愿在于能用小说将自己一生完成得更丰满,“我希望一生就是一部一部的作品,每个阶段很完整,写到最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标本,也许放在黑暗的仓库里,不要紧,我是个很完整的小说家。”<br>小说家的世界<br>他只说自己是个小说家,散文也极少写;他不爱旅行,旅行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工作地点就是书房,书房以外的部分就是家,他的世界很小,却又宽广无际。托尔斯泰说村庄即世界,在毕飞宇看来,两人就是一个世界。道家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世界。所有的幸与不幸都是从两人世界开始的,笔下的人物也不例外,“你塑造了这样一个人,再慢慢跟她相处,会知道很多”。写作正是这样一种逻辑性的梳理,也是一种幸福的领悟,个中的辨析、复杂与爱,在现实中无法找到。他写《青衣》里的筱燕秋,仿佛身旁有位顾盼垂首的梨园情人,然而他有的只是案头的一本《京剧知识一百问》,他为张艺谋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写剧本,所有资料就是老谋子给的一本《上海滩秘闻》。写作的过程不是电脑机械的输出,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他将其看作一种修炼,“我的人情世故大多是从写作中悟出来的。”<br>有批评家曾说,当代先锋作家从马原、莫言开始,以及后来的余华、苏童、叶兆言,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一位国外的大师。“我背后没有”,他答得很肯定,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是曹雪芹。和很多同辈一样,毕飞宇年轻的时候受西方影响很大,然后到了上世纪9年代中期几乎全部放弃。在小说技能上,对其有影响的只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同乡施耐庵,一个是曹雪芹。“施耐庵最了不起的能力是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一个人”,所以,毕飞宇小说中的次要人物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彩,而曹雪芹,则是“剥洋葱的高手”,他写风月、服饰、食谱,一步步退到最后却什么也没有。繁华落尽,万籟俱静,仿佛结尾出家的宝玉在落雪的江岸消失,了无痕迹,“多么高明”,他惊叹。父母都是“红迷”,他读《红楼梦》的时候却已经三十好几,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文坛有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擅长描写女性的作家,都会被与张爱玲拉上关系,仿佛无一例外是承了祖师奶奶的衣钵,满口“张腔”,毕飞宇倒是一直幸免于此,“张爱玲是一个技术一流的普通作家,夏志清把她提高的很高,把鲁迅压的很厉害,张爱玲是一个技术主义作家,不太有信念;钱钟书对自己小说的人物是刻薄的,完全没有爱;而红楼梦里面,一个坏人都没有”那是曹雪芹的仁慈,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抢先一步读了曹雪芹,得了“祖师太爷爷”的真传。<br>要说小说的温度,在他的作品里,《推拿》算是温度较高的一部,他曾在南京特殊教育学校执教,后来写盲人推拿师,去推拿诊所和他们聊天。他很了解自己的写作特征,凡事刨地三尺挖到底,却不忍挖他们的内心,“用一种春秋笔法进入残疾人的内心,对我来说是一种不能干的事情,但我后来恰恰觉得这是一种尊重,你不把他们当初异样的人,这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有的,心里跨过了这个坎。”所以后来就有了推拿的结尾,所有盲人手拉手,从抢救室走去手术室,那一幕,他写得特别感动。<br>至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区别,他举例,小说就是一个管道,一个人物要从管道里面爬出来,通俗小说的管道式圆的,起点在哪,从哪爬出来;严肃文学从一头进去,从另外一个出口爬出来。“通俗小说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让人物成型。西方文学中有‘机械的上帝’,任何事情马上就能解决掉,情感很简单,人性很简单。”<br>拿了太多奖的中国作家,难免会被人问及是否觊觎诺奖,他自己的方式是不听不看不想,在脑子里永远将其回避,“那个和我没关系”。他是爱小说的,一如他狂热的迷恋运动,并为此一身是伤。两天前我发邮件问他是否在闭关写新作,他回信道:“我的写作从不闭关,写作是我一生的事,快乐的事,一闭关就成终身监禁了,那样的傻瓜我不做。”恍如二十年前那个在球场上掷洒汗水的一员悍将,他大概又在书房了开始了一个人的驰骋,畅快淋漓,没有目的。<br><br>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