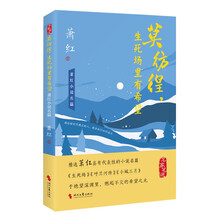写在前面的话
董良翚
书,简单一点说,就是一扇窗户。打开这扇窗户不仅仅可以看到无穷无尽的各种人文景观,还能看到未曾经历的或者不曾深入了解过的故事,或者感知将要发生的事情,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群活跃的思想。这是书给我们的。
家书出版了,其实是把一种私密的思想交流公开化了:同辈人的交流、长辈对后代的关爱和教育。读者可以看到在历史进程中一个家族里的一段思想动态,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一支
思想脉络。
父亲给我母亲的信里除了通报自己的近况、交代一些事情外,总会把随他外出的每位工作人员的情况告诉母亲,也一定会问候留守寓中的所有工作人员。父亲从来都视他们如家人一般,是一种全新的同志关系。记得母亲讲过一个关于父亲的逸事。在抗战时期,父亲太忙,因为忙,连看表的时间也常常被挤得没有了,偶尔险些误事。父亲索性把手表交给当时的警卫员,由他来掌握时间。结果没多久,那人“跑路”了。害得父亲还检讨:客观上“资助”了这个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的逃跑。
在这本集子里有一封父亲写给我的信。还记得那是我上中学,有一年,我有补考的学科,已经记不得是哪门课程。放暑假时我向父母隐瞒我有补考的事,也跟着去了外地;暑假没结束,补考时间到了,就偷偷溜回北京参加补考,临行前也没有向父亲解释,或者说没有补一个“报告”。补考完妈妈打电话告诉我:父亲非常生气,要我写信说明情况。我只得写信,简单地对自己补考的事敷衍了事地说了说,然后,反而主要责怪父亲脾气大(幸亏这封信没有留下来,不然,对我的幼稚无理自己会长久地自责)。刊出来的这封回信告诉我:他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是我的朋友,对朋友要以诚相待;我没有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他是为此生气;他还承诺以后改正自己的脾气。这本是我和父亲一次私密的交流,是父亲教我做人、做事和学习。
我常常回味这封信,体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真正在做我的老师、朋友;多少年后我入了党,还成为父亲的同志。
他用自己的思想历程和他的坚守教育我;他说母亲的慈惠是告诉我妇女的社会承担。他的爱是矗立在我眼前实实在在的榜样。无论什么时候想到父亲,想到他不经意的话语,想到他深思熟虑的文字,总让我感到十分温暖、贴心。这与旧时代比较就是全新的父女关系。
我又想起我上中学时,父亲要我们在暑假里抄写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他说他也抄,他就真的用毛笔小楷,一个假期抄完这篇文章。父亲从来都十分注重家人的思想教育,并且以身作则。
需要特别说一说的是,在这本集子里收录了我母亲写出的一些信。
我母亲出生在四川省万源县(今万源市)偏僻山区的穷人家,贫穷家的妇女没有地位,在那里,人们都称女孩子为“客娃娃”。女孩子从出生到出嫁,只是娘家的客。贫穷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让“客娃娃”上蒙馆或私塾。甚至连女孩子的出生年月也没有人记得清。母亲参加革命前认字不多,也没有写字的机会。母亲参加革命后打仗、行军是常事,直至长征胜利。在延安,大约1937年经李坚贞阿姨介绍和父亲结婚,父亲母亲在延安共同生活时间不多,父亲又被派到国统区。母亲留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之后曾追随父亲到武汉、西安、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方,参加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繁杂琐碎的事情,真正是我父亲最强有力的后勤工作支持者。进京以后我们家生活才逐渐稳定下来,1957年前后我们家搬进中南海,母亲已经四十六七岁了,她才刚刚拥有坐下来学习文化的条件。
本书集中我母亲落款的给家乡亲人们的信,前期——以我父亲谢世为界限——写的信大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我父亲的身影,因为大多数是父亲起草的,还有些信可能失落了:有我母亲抄的,也有我或者哥哥抄的;还有的是工作人员抄的(这是父亲教身边工作人员学习文化的方法)。虽然我母亲抄写不多,但每封信她都要代执笔的人给她读读。她的记性很好,什么时候给谁写过信、大致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忘。
家书的形式,大概已经变成历史了。尽管我非常留恋那文字间溢满的真情、关爱和亲情,留恋文字给人长久不衰的美感,留恋文字可以传承的精神享受;但新的通信手段,文字的、视频的、会话的方式现在使用起来都很快捷、通畅、直观,新的通信手段入门要求又不高;亲人、朋友、同志的交流更随意、更方便,也更频繁了;人际关系似乎更近了。科技的进步带来对文字记录的冲击难以估量。新潮的通信联络方式汹涌澎湃地迅速扑过来,旧有的表现形式不得不戛然而止。这一改变让我很纠结,也很无奈。
也许这只是九斤老太式的哀叹。
我其实不够写序的资格,也不敢写序。只是应编选人、我的侄儿董绍壬的请求,暂借一两页篇幅介绍一点情况。
衷心地希望读者通过本书了解一点我的父亲,亲近一些我的父亲;读者在读本书时,也是您的心灵和历史在道别,衷心地希望您能取得最大收获。
2016年元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