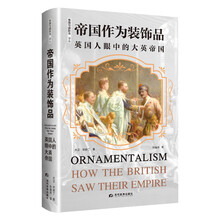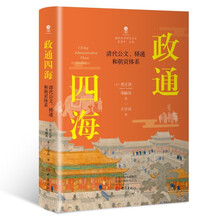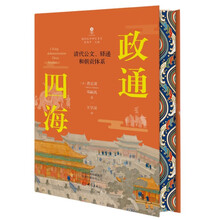一 革命暴动中的政治认同
(一)革命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
作为社会运动的革命暴动,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运动基础。这种基础,一方面体现为暴动领导者对起义前政治形势,特别是政治机遇的分析,同时还隐含着暴动领导者对革命暴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未来前景的预期。“社会运动基础由一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累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组成,这些因素均有助于社会运动活动的开始。”②对于1927年革命暴动而言,社会运动基础意味着革命形势,“包括某一特定政权内部发生的明显分裂,与之相伴的每一个政党都分别控制着该国某些重要地区或某些统治工具”。③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拥有各自的政治资源。前者拥有作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成果的合法政权,以及相对成熟的政治经验,特别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正规军事力量;后者则自认为可以把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理所当然地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甚至因此乐观地认为革命仍然处于高涨的阶段。南昌起义和“八七”政治局紧急会议后,中共中央对形势的评估相对乐观,认为革命形势有利于暴动和使革命重新走向高潮。如“八七”会议后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就认为:“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稳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④
尽管中央认为南昌起义的条件是成熟的,但事后证明:“就时间说,未能暴动于长沙事变,工农群众激昂有力,又逢河南有事,而武汉尚多同志武装之时,而暴动于国民党三派联合成熟的工农及军事力量削减与消沉之时;就空间说,不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①所以,南昌起义时机的选择其实并不理想。但考虑到起义所依赖的正规军事力量仅有贺龙和叶挺二部的尴尬现实,以及张发奎欲借九江会议之机扣押叶、贺的危急情势,选择此时起义仍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南下广东的进军方向,不能充分利用既有的社会运动基础。南昌起义拥有1927—1928年共产党领导的各次武装暴动中人数最多也最正规化的军事力量,但是即使以如此正规的军事力量作为主要动力,若无工农群众运动的呼应,也很难有所作为。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由于“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甚至“因受AB团的宣传,对我们更加仇视,数日不见一人”。②
而秋收起义则充分证明,农民的革命情绪并没有如中央设想的那样高涨,能够天然成为暴动的社会运动基础。起义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③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省政府、省党部对于铲除暴徒,排除共产,遏制工农运动完全秉承唐、何意旨,正在进行,省城公安局之厉行清乡查户口颇为可怕。”④
白色恐怖高压之下的农民运动,显然很难复制北伐战争后受到广东革命政府鼓励的合法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辉煌。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虽然畏惧白色恐怖,可是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农民运动昔日辉煌的怀念,使他们仍然有可能支持共产党的暴动鼓动。“佃农的二五减租也没有了,租金利息也没有了,地主的帐又要还了,说话也无从前自由了,土豪的屋子仍旧进去不得了,手工业工人的工价也减低了,因此农民渐渐感觉,土豪劣绅到底是欺骗他们的,暴徒专政的时候,实在要好一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