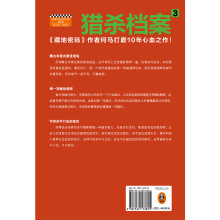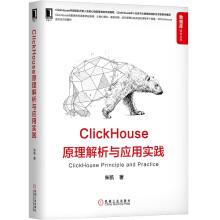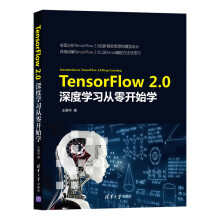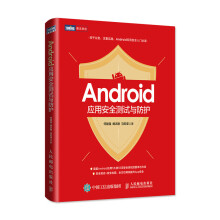这本简短的小书中,我所讨论的都是从前讨论过的问题。我将回溯一些文章(尤其在我反复记录巴格尔神话之后),因为有个问题让我反对许多关于“神话”、“口述文学”及其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充满一种神秘性质,我的证据很难证实其观点。由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用大量时间记录、转述与转译各种版本的罗德佳“神话”或记诵文。recital,有独唱会、独奏会、小型音乐会、舞蹈表演会等意思。recitation,指朗诵表演。这二者都带有记住某种文本,然后背出来、表演出来的含义。为了与action,play等词区分开,在翻译时尽量避免将其译作“表演”,“独唱”,并会把recital,recite与recitation三个词按照语境译作记诵文、记诵、记诵表演等。——译者
(同我的朋友昆姆·甘达一起),现在看来,似乎有必要尝试把一些总体观察结果综合一下。
神话与仪式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学家的主要兴趣点,人类学认为二者就像动物崇拜(自然崇拜)与英雄崇拜(死人崇拜)一样,是“原始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二者作为“他者文化”的特征,被排斥在“现代”理性之外,遵循其他逻辑体系,或者在我们的词汇中将其称作“前逻辑”、“非理性”。一定程度上出于对交流方式,尤其是口语与文字交流的兴趣,我想采用一种更偏重认知学的方法,而不是用结构—功能方法(或后结构主义)研究这些活动。此外,我比较认可埃文思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在阿赞德(Azande)研究中使用的、站在行动者角度观察社会的逻辑,不把各个文体形式看做固定不变、程式化的产物,而是认为这些形式反映了人类的创造力,把人看做一种因为要应对世界而使用语言的动物,人类既不会脱离传统,也不会完全被传统束缚。
我并不敢自认是唯一采用不同方法之人。因为确实已有很多学者一直在关注诗歌与语言学,他们记录过很多不同种类的变体,当然,我不认为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在揭示所谓“原始心态”(primitivementalities)问题上产生过多大影响。还有人强调叙述的社会语境,叙述者与听众之间的对话,但在录音设备出现之前,与此有关的证据相当稀少。正因为这样,我们既要论述那些遵循一定“结构”的变体,又得引出那些难以预测、变化多端的变体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确实很有创造力。
展开